高考向来都以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激烈竞争闻名,是很多人难以忘怀的人生经历。而今年的高考因为疫情的缘故,或许对很多考生来说这份记忆更为特别。今天已经是高考的第三日,再有两天考生们就能暂时“解放”。我们以下面这样一份和考试及高等教育有关的书单,试图对这一话题进行发散性的思考。
日本京都学派代表人物宫崎市定在《科举》一书中,梳理了中国科举制的历史和特点,指出改变命运的考试从来都有许多艰难。
撇开古代的考试不谈,今天的大学里又藏着怎样的奥秘?《象牙塔的变迁》一书展示出理性化与“世界之祛魅”如何让传统大学发生转型,成为今天我们熟悉的大学。
如果说大学尚存在着种种不足,那么进入大学的学生们能够获得什么?在学历不断贬值的今天,苦苦追求大学梦的学生们又在追求什么?寒门贵子在“鲤鱼跃龙门”之后能否获得他们期盼已久的美好明天呢?或许《文凭社会》和《出身》能够给读者带来一些思考。
中国产生“考试地狱”并不意外?

《科举:中国的考试地狱》
[日] 宫崎市定 著 宋宇航 译
启真馆 | 浙江大学出版社2019-1
考试不是当代人独有的,古代人也有他们的“高考”,也就是著名的科举考试。宫崎市定看到,中国土地辽阔、人口众多,在这里,最具才能和资源背景的人们聚在一起展开你死我活的竞争,这只会让考试变得越来越难。因此,在中国如果没有产生“考试地狱”,反而会让人觉得不可思议。
宫崎市定的《科举》一书分析认为,科举在诞生之初是皇帝用来对付贵族政治的武器;到了唐代,科举的发展帮助王朝实现了从贵族政治向官僚政治的转变;在宋代,科举帮助天子确立独裁体制,发挥出了它最大限度的效能。但是,随着中试者不断增加,应当分派的职位相对减少,科举对于政府来说开始成为沉重的负担,渐渐地,来应考的举子对于可以猎取的官职来说如同“聚集在砂糖上的蚂蚁一般”;到了清朝末年,朝廷就不得不使出各种繁琐形式淘汰更多的人,并以此最终抹杀了科举的真正精神。
随着竞争越发激烈,相比于单纯的个人才能,考生所处的环境对考中科举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在宫崎市定的研究当中,科举制度之下存在着“寒门难出贵子”的问题。这是因为教育原本就是耗费金钱的事业,朝廷不愿意给这种无法立竿见影的事业投入资金,所以把教育责任全部移交给了民间。朝廷只通过举行考试,就能够让那些在民间自行受到培养的有为之人为政府效劳,而高昂的教育投入对于普通家庭来说可望不可即。此处的教育成本问题对我们今天的思考仍有启示。
今天的大学是如何形成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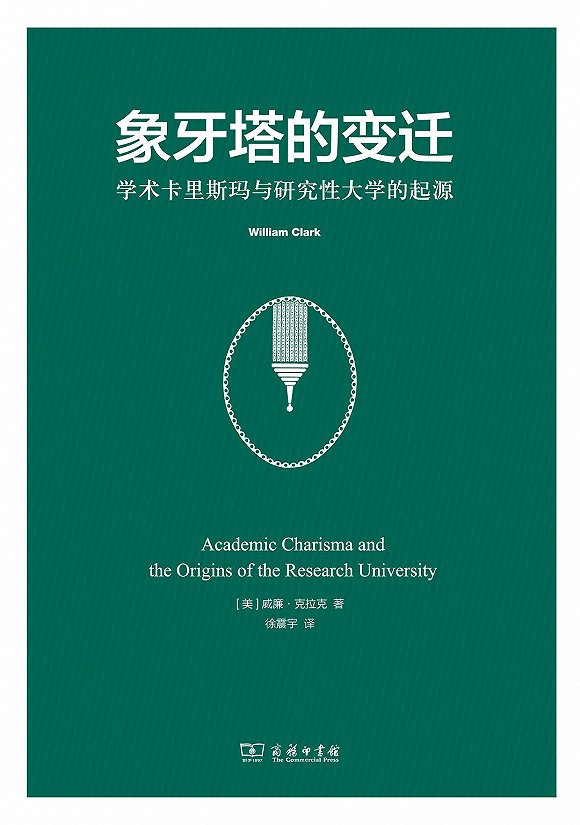
《象牙塔的变迁 : 学术卡里斯玛与研究性大学的起源》
[美]威廉·克拉克(William Clark)著 徐震宇 译
三辉图书·商务印书馆 2013-11
这本书考察了和今天许多国家大学体制均有渊源的近代德国大学体制。书中首先阐明,传统性大学蕴含了怎样的卡里斯玛(神秘魅力或巫术性质)。卡里斯玛起到的作用是巩固传统,在课程设置上变化非常小,具有正典一样的神圣性,也就是说,这些老师用着自己老师用的课本,而他们的老师用的也是自己老师的课本,代代相传。其他方面诸如教师穿着、办公室布置等等,也都有日常化、结晶化的卡里斯玛在其中。学位、学术称号、学术职位如同教阶体系那样,向持有者传递卡里斯玛,并以此维持学者的权威。这时候,人们不欢迎卡里斯玛的个人进入大学,如此方能巩固集体性的卡里斯玛。
官僚化和商品化共同驱动了理性化与“世界之祛魅”的进程,但其中的一些内容——例如学位、学术称号、学术职位等——在今天被延续下来。而且,研究性的大学开始在更广的理性化界限当中培养卡里斯玛式的人物。如徐震宇在《象牙塔的变迁》译后记中所言,今天,在象牙塔中的人们要面临官僚体制和市场经济形态的双重压力。各式各样的考核和计量手段、著作论文发表指标“量化”着学者的成果,学者们还要受到行政权力的管理。这种情况下,体制里的学者要通过不同的途径来博取自己的“学术卡里斯玛”。最终,和其他领域一样,象牙塔里也出现了马克思所言的“劳动的异化”。
进入大学是为学习技能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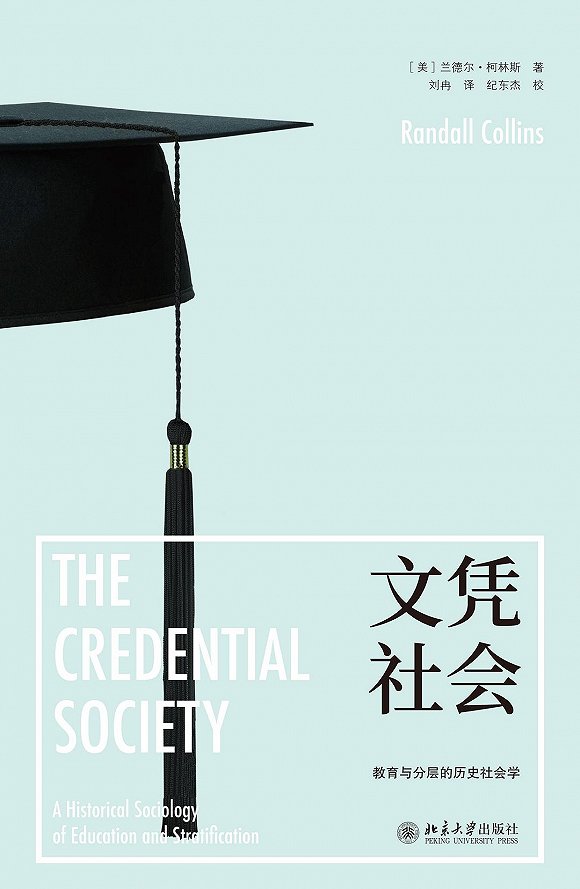
《文凭社会 : 教育与分层的历史社会学》
[美]兰德尔·柯林斯 著 刘冉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8-6-1
今天的我们处在文凭的通货膨胀中,学历贬值意味着获得高学位的人越来越多,工作岗位对教育水平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一个常见的解释就是,因为社会需要更多有技能的人,所以才需要教育的扩张。但事实上真的是这样吗?作者发现,虽然初级教育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很大,但是高等教育的普及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其实并不明显。人们常常把大学视为帮助学生准备好工作所需技能的场所,并且认为技能将会决定事业的成功,但通过数据分析就可以发现,其实大多数实际技能是在职场中获得的,在学校里学习技能的效率其实很低。
社会学家兰德尔·柯林斯指出,学历贬值实际上和“文凭凯恩斯主义”有关,也就是说,如果年轻人太早进入社会,政府就需要创造很多的就业机会,这给政府带来很大的负担。如果高校扩招,越来越多的人有一层一层的文凭要拿,就给政府提供了越来越多的缓冲时间。而人们对这种行为也并不反感,甚至乐于获得这些文凭。
之所以人人都想要高等教育文凭,是因为大家都想要进入与生产劳动相对的政治劳动当中,这就是说,大学的重要之处不在于培养技能,而在于其发放文凭的权力。人们渴望获得文凭的符号价值,凭借文凭所带来的地位做“脑力劳动”的闲职,通过统治结构而非生产结构来获得物质产品。
进了大学就会有好前程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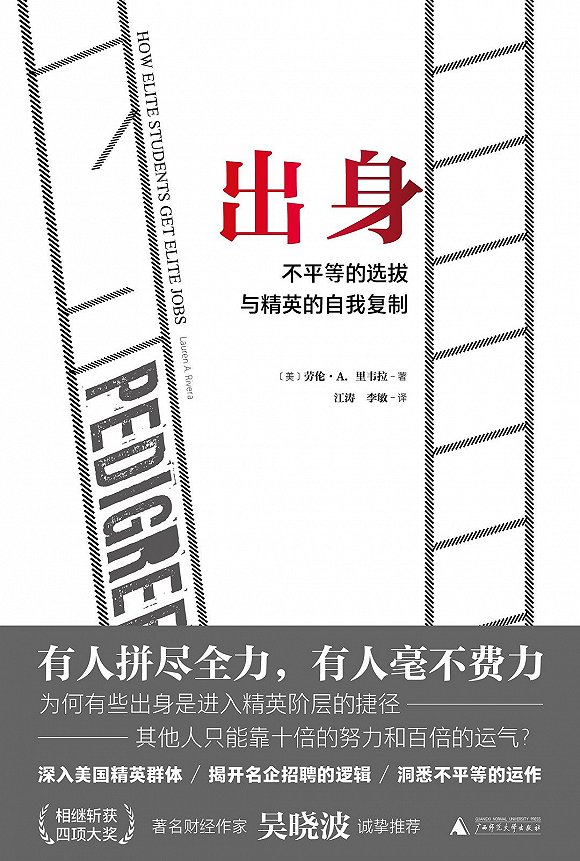
《出身:不平等的选拔与精英的自我复制》
[美]劳伦·A·里韦拉 著 江涛、李敏 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9-6
《文凭社会》一书指出,在美国,教育并没有促进社会公平,反而给社会的流动造成了更多的困难。虽然接受更高教育的孩子比例已经大幅增加,可社会的阶层分化并没有改变。
寒门难出贵子,当来一个自贫寒家庭中的学生千辛万苦拿到一个学位之后,接下来的处境会如何呢?《出身》的作者劳伦·A·里韦拉发现,在今天的美国社会,往往是富裕家庭的孩子获得高薪的职位。这与布尔迪厄说的文化资本、惯习等概念密切相关,即使进入了好的大学,一个人在找工作时不能够正确展现文化技巧,也很难谋求到理想的职位。
本书作者还看到这样一种现象:在美国名校的校园文化当中,非正式社交圈中的派对、聚餐、国外度假与正式的课堂学习一样重要。人们甚至认为本科教育的目的更侧重社交,而非学术。在大学里,家庭所处阶层更高的孩子更注重社交,普通家庭更注重学习。兰德尔·柯林斯也认为大学的社交功能也加剧了阶层固化——大学的社交就是把中上层阶级的孩子聚到一起,产生感情,成为朋友,最后走向门当户对的婚姻。
对此,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教授刘云杉
在接受界面文化采访时
称,其实,对学习来说,考高分对一个人的背景要求没有那么高。但是,一个人如何打入一个圈子,如何在其中应付自如,和所有人得体地相处并且成为核心,是困难的。在她看来,这不是社交问题,而是一种身份文化。这套身份文化和学生未来走进的专业群体、社会圈子是高度同质的。那些圈子往往也是学生未来职业想要进入的圈子。而来自某些阶层的孩子更能深谙那些圈子的规则、如鱼得水地习得一些习性。正如里韦拉所言,“对一些人来说,学到精英文化是用很大代价换来的成功;但对另一些人来讲,这只是一种继承。”
 简体中文
简体中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