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这里是一个怀旧剧场。
有人曾评价,看了《媳妇的美好时代》就会知道“老公怎么疼老婆、媳妇怎么孝顺公婆、公婆如何体谅晚辈、亲家之间的相处之道”。这样理想化的温馨固然与生活的烦恼不那么对等,但这又何尝不是以“80后”为代表的新年轻人看似“玩世不恭”的生活态度的一种折射?
婆媳剧的新“套路”从这里开始
当代中国电视剧的类型化发展,以古装、都市、青春最为成熟。其中,都市剧又以过半的比重长年占据中国电视荧屏的主流。细细想来,都市剧在中国的“霸屏”不无道理,这跟国人多年养成的观剧文化紧密相关。都市剧不外乎聚焦生存、生活两层维度,亲情、爱情、友情又括入其中一以贯之。都是当代人的现实迷思,又指涉着群体性的社会症候,其现实主义的定调和浪漫主义的气质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更丰富的想象空间,供以对现实中正经历的焦虑有所抚慰。

《媳妇的美好时代》剧照
在数目众多的当代都市剧中,家庭剧又是最受欢迎的一类。这跟电视剧过去在“客厅”场景下的家庭式观看有关,“合家欢”式的家庭娱乐通常更受中国千家万户喜爱,而家庭剧通常以社会学视角上的“核心家庭”为基础,围绕普通家庭生活铺展,似乎更切中这种家庭趣味的肯綮。严格意义上来说,既有的对于家庭剧的概念界定较为宽泛,从时间上古代、现代皆可,从空间上亦同时可发生在城市与乡村。但随着社会转型时期的矛盾进一步加剧,人们大范围地向“都市”这一新社会空间流动,其所承载的压力乃至阵痛也更趋复杂、深刻。因而,新世纪以来,都市家庭题材的剧集大量涌现,观剧群体表现出的旺盛的消费力也在事实上不断“倒逼”都市家庭剧进一步分化,以对准更具体的社会矛盾。

《媳妇的美好时代》剧照
在都市家庭剧诞生的初期,它显然是“女性化”的。电视文化学者约翰·菲斯克就曾提出西方国家与中国的家庭剧类型十分相似的“肥皂剧”(soap opera)是一种“女性叙事形式”的观点。随着社会文化的变迁、流行性别观念的转变以及家庭剧叙事策略和人物设定的调整,“即便男人们常常抵触肥皂剧,但它着实不再仅仅属于女人们了”。在很多情况下,我们会发现家庭男性是作为当代都市家庭剧隐性叙事视角存在的,诸种现实困惑促使诸如婆媳关系这样的围绕一个或多个男性建构起来的新家庭“矛盾”体正在逐步构成某种普遍性的焦虑。婆媳剧遂成为一种新的传统,在2000年前后盛行起来。
以婆媳关系为切入口的电视剧《媳妇的美好时代》,可以说是这类作品中最有代表性的了。它在很大程度上开启了中国电视荧屏中有关婆媳叙事的“蓝本”,此后的作品实际上未能表现出更具颠覆性的创新。从积极的一面来看,首播于2009年的《媳妇的美好时代》抓准了最具时代性的家庭结构变化,至少在大面上,之后几年间的中国家庭图景似乎始终面临着相似的问题;从消极的一面加以反观,《媳妇的美好时代》令人看到了那一阶段家庭剧的新变化,而此后的同类作品至少在很共性的层面上陷入“复刻”的窠臼。《媳妇的美好时代》描写了两家人之间的故事,探讨着当代都市家庭的婆媳关系,以及拥有新式婚恋观的“80后”适婚青年步入婚姻殿堂过程中所直面的种种问题。然而它的调性又是轻松而易于被接受的,以毛豆豆和余味为代表的人物角色,带着特定的喜感和人格魅力,在并不怨艾的基调里令观众来思考这些生活难题。可以认为,它也是“‘80后’步入社会”系列剧中的代表作品之一。

《婆婆媳妇小姑》剧照
在婆媳剧成为国剧小潮流的这些年里,真正能令观众记住的作品不多。1998年的《婆婆媳妇小姑》开了先河,也塑造了最戏剧化的婆媳“对立”形象。婆婆和小姑联手“欺负”就是不愿意当家庭主妇的于小娇,家长里短的小桥段现在看来也不过时;2007年的《双面胶》拔升了一些,婆媳“战争”落实到了观念层面,通过带入“凤凰男”和“孔雀女”组合下的社会阶层差异探讨,将失衡的家庭权力关系这一社会议题摆到桌面上认真剖析了一番。《媳妇的美好时代》更进一步,虽然是站在上述两部作品的“肩膀”上起跳,但这部剧的跨越是十分显著的。一是介入外部矛盾打破单一的婆媳关系建构,两个“婆婆”的势不两立也为全剧矛盾带来更复杂的角力;二是直面现实不等于总是残酷,相比其他婆媳剧,它显得更亲民——家应当是温馨的地方嘛,何必总是苦大仇深的。
有观众曾评价,看了《媳妇的美好时代》就会知道“老公怎么疼老婆、媳妇怎么孝顺公婆、公婆如何体谅晚辈、亲家之间的相处之道”。这种理想化的温馨固然与生活的烦恼不那么对等,但这又何尝不是以“80后”为代表的新年轻人看似“玩世不恭”的生活态度的一种折射?
有多“现实”才能令人念念不忘?
在中国的文化传统里,结婚从来不是两个人的事,而是两家人的事。如果能理解这一逻辑,就能理解婆媳剧的“火热”何以可能——这是现实镜像的结果。因此,都市家庭剧得以观众移情的重要基础,便是它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达成了“现实主义”。

《媳妇的美好时代》剧照
颇受观众好评的前半段故事
一个简单的例证:毛豆豆和余味从相识到相知再到相恋的戏码,用三次“莫名其妙”的约会贯穿起来。这样的叙事表面上看是出于立人物的需要,在我们传统的想象里也更偏向奇观一些。但据编剧王丽萍自述,这是她在参与一档老牌相亲节目时的真实所见。一次,她陪同女方去相亲,双方一见不合适就要一拍而散。谁知男方买了自己咖啡的单转身离开,这种AA制的相亲令人大跌眼镜、啼笑皆非。
这便是《媳妇的美好时代》里毛豆豆和余味三次相亲遇上同一人的现实源头,并不那么“戏剧”,几乎是真实生活的一次写照。且不论这是多大程度的“真实”,但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个正经历的时代或许已经分不清“狗血”的究竟是电视剧还是生活本身了。

《媳妇的美好时代》剧照
毛豆豆嫁入余家以后,真正的“婆媳”戏码登场了。在各式各样的“斗争”背后,《媳妇的美好时代》还是在冷静地讲述家庭沟通的现实问题。毛豆豆和余味都不属于特别扁平的人设,没有太过棱角分明的个性,但“纠结”似乎是他俩共同具有的特质。余味的父母离了婚又各自成了家,婚后毛豆豆的“婆婆”忧虑平白多了一倍,加之弟弟毛锋状况连连,麻烦接踵而至。然而,婆媳相处之道又不仅仅停留在婆婆与媳妇之间,在“夹缝中求生存”的余味,既要充当女人之间的调和剂,还面临着妹妹余好的不时搅局,家庭的战争总是一触即发。
仔细想来,这组群像的面貌努力裹进各式各样的现实缩影。虽然处处皆是烦忧,可生活总要热情前行,这大概就是《媳妇的美好时代》中的“现实主义”吧,有那么点恼人,也有那么点迷人。
“创作要与生活的相似度松绑”
在北京电影学院88级表演系的某张毕业合影里,十多张青涩的面庞中有后来的影后蒋雯丽和许晴,而另外的同学当中,有一位男生也于2003年在电视荧屏上推出了自己的处女作。不同的是,这位表演系毕业的同学,名字却出现在了导演一栏中。
刘江,曾获得过飞天奖、白玉兰奖和金鹰奖等国内诸多电视剧领域的重要奖项,已经成为中国当代电视生态中的重要人物之一。《媳妇的美好时代》也出自他手。他说“希望自己扎根在中国当代社会之中来呈现源自生活并高于生活的作品”,这也成为他最为关切的创作心路。
作为一个善于讲述都市故事的导演,刘江执导作品的类型化创新不仅停留在最终的作品呈现之上,更反映在他整个创作过程之中。2016年播出的《咱们相爱吧》,在他看来便与此前的同类作品形成了显著差异。这是一种“特意”的转变:要从《媳妇的美好时代》跳出来,重新去观察这个不断在变化的时代。

《媳妇的美好时代》剧照
对于都市题材而言,生活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国产都市剧若要展开进一步的深耕,最重要的便是“贴近生活”。在刘江看来,“这跟古装剧看‘传奇’的传统不同,都市剧一定要更深层次地贴近生活,这种贴近是需要与生活的相似度松绑才能实现的”,刘江继续补充,“不能因为没有经历就不相信,有时候神似比形似更重要,这就意味着我们的类型化创作还是要在一定程度上高于生活的”。在某种程度上,都市剧就是当代生活的一面镜子,它应当令人看到一些“看不到”的形态,但内核却是始终植根于现实的。《媳妇的美好时代》也有不少细节能对此加以印证。刘江说:“这部作品当时在北京取景,但我首先就拒绝用胡同去代表它的空间。所以我有意识地用了现代化的小区,不想让它局限在北京这单一的地貌上,这才能实现这部剧的‘南北通吃’。”在刘江看来,看戏就是在看故事,对生活形态进行白描并非电视剧艺术的终极目标,“不管在形式或内容上,我们都需要站在更宽广的视角和舞台来审视自己的创作,不能被某种简单的形似所绑架”。
这样似乎能够更进一步地理解《媳妇的美好时代》——我们正经历的时代,外在的生活体验或许各有不同,但内里的生活态度总是具有一致性的。
婆媳故事讲了那么多年,新意越来越少,能够映射的现实也愈发显得捉襟见肘起来。《媳妇的美好时代》给出的婆媳剧样本,能带来的思索或许还有更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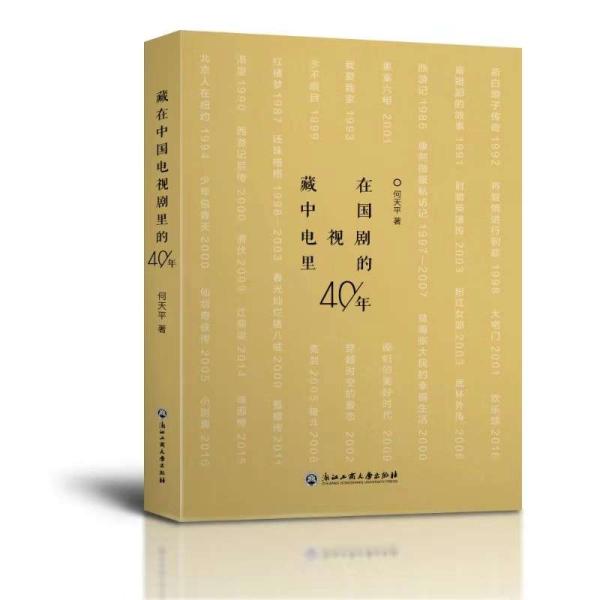
本文摘自《藏在中国电视剧里的40年》(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2018.7),作者何天平(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简体中文
简体中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