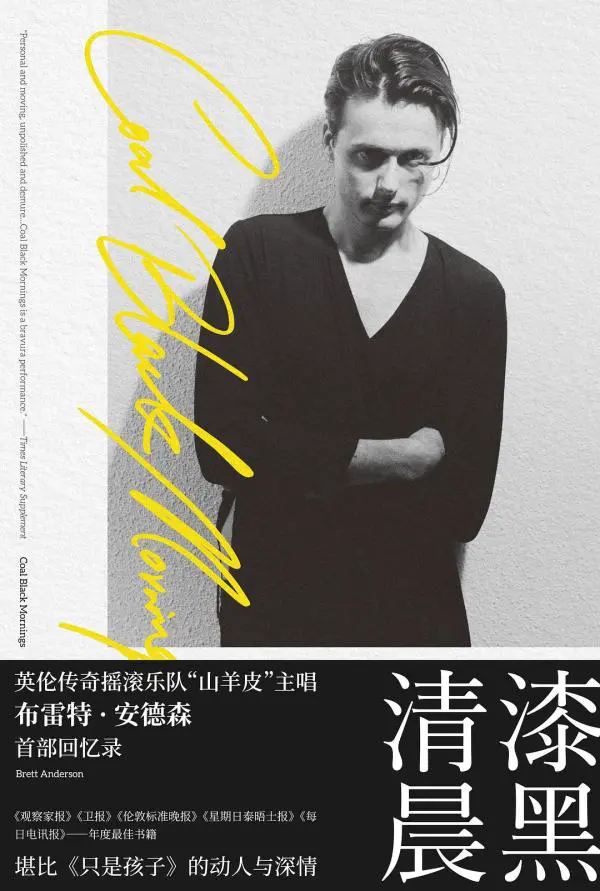“山羊皮”(Suede)主唱布雷特·安德森(Brett Anderson)在自传《漆黑清晨》(Coal Black Mornings)的前言里告知读者:“我最不想写的,就是通常的那种‘可卡因和金唱片’的回忆录。”幸好,因为最难看的回忆录通常就是这一型。人一旦成功,就会失去部分真实的力量,哪怕仅仅是回忆它。安德森的这部“史前史”,结束在“仍盲目乐观、胸无城府的年头”。他从出生写起,至乐队起飞前戛然而止。这本小书可以一口气读完,但一定会读第二和第三遍。可以给它取一个副标题:在失败、贬值的英国寻找诗意和高贵。在狂热古典乐迷的父亲的廉价城堡中,安德森一去不复返地离开单纯乖顺的童年。阴暗粗暴的朋克和父亲的浮华古典乐,在他们家那栋纸盒子般小得惊人的房子里交织。两种音乐一起播放时,“假如站在楼梯上,就能体验一种布莱恩·伊诺(Brian Eno)风格的混合音乐”。
离家以后,家乡远郊小镇的愁苦又和曼彻斯特的刚硬湿冷、伦敦庞大的力量与美丽混杂在一起。各种景象和声音扑面而来,安德森去往各地,把目之所及拼贴成一幅污秽的画面,与父亲所沉溺的大英帝国余晖截然不同,也与画家母亲笔下连绵不绝的乡村丘陵绝无相似处。安德森所绘的英国贬值、失败、冷漠,人行道上布满白色狗屎,电话亭伤痕累累、尿渍斑斑,贫穷无处不在,区别只在于栖身的方正小盒子大一点,还是小一点。

安德森父母的老照片
安德森和他所处的阶层,当时仍深信穷人不可能成功,阶级无法被跨越。他们一家甘心被贫穷包裹。父亲是个神经紧张,脾气暴躁的底层劳动者,没什么物质欲,竭尽全力养家时带有无私奉献的神圣光辉,刻薄和专制时令人胆寒。他的母亲是上过艺术学校的业余画家,最好的时光是就着六十年代民谣缝纫、画画,在厨房郑重打开一罐黏稠的炼乳,把配给时代稀有的童年甜味一勺一勺送入口中。
安德森用了不少笔墨描述父母间紧张的关系。他后悔自己曾经毫无洞察力,只知沉浸在自我的世界里。父母的关系最终分崩离析后,他将花费更多痛苦的精力探寻他们的婚姻与人生。
“我只是我父亲通往我儿子路径上的一点。”潜入记忆的深入,安德森和父亲间的复杂关系渐露全貌。他未能免俗地发现,“我对爸爸的记录与描述也有一部分是在写自己。所有的儿子都曾照着镜子,看见与自己对望的镜中人是他们的父亲”。
他很清楚,如果不加约束,自己会变成什么样——成为父亲一样的人,希望落空,好战、狭隘而残忍。但他的确记得父亲美好的一面。在父亲对建立父子关系仍有美好憧憬时,父亲对他的关爱恍如他在怜爱年幼时的自己。父子间面孔的相似带来的奇妙效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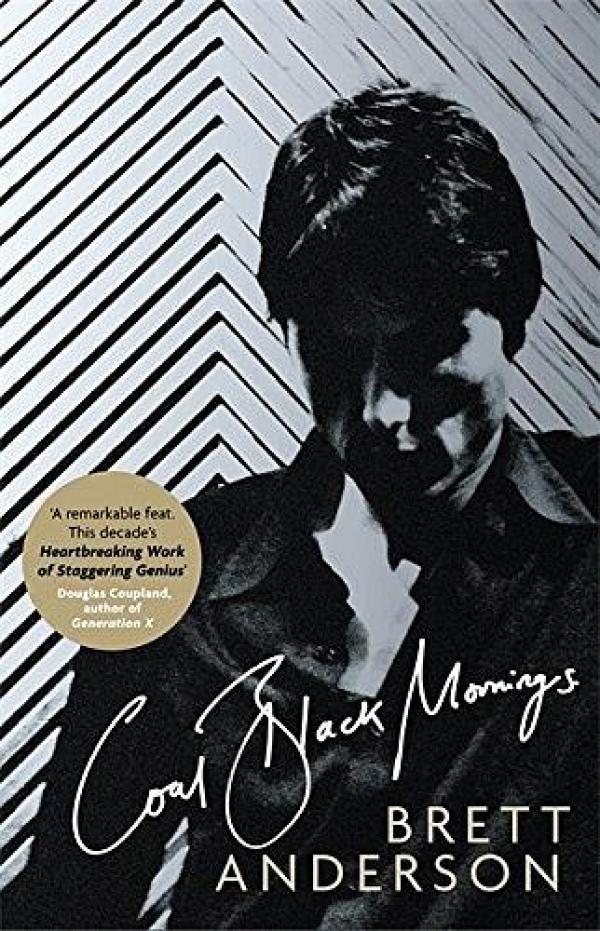
《Coal Black Mornings》书影
这个因艺术和手工而具有上层中产阶级知识分子气息的贫陋之家,却与所在村落格格不入,且一直未能融入。安德森的父母也从未真正“融入社会”,找到安身立命的舒适位置。在贫穷和它必然带来的耻辱中,他父母的艺术感觉和对美的追求脆弱不堪。他记得一个时刻,他们的车在骑士桥哈罗德百货公司门口抛锚。身后烦躁的汽笛声鸣奏仿佛一束聚光灯,照耀了他们的贫穷。当时的他还不可能想象,真正的聚光灯照在身上时,会照出什么。贫穷与艺术,骄傲与落魄的共存是生命开始时的颜色。这种不和谐的经验如此切身,就像父母的仁慈关爱,间以狂风暴雨般的争吵,是安德森和姐姐从小熟知的场景。
贫穷带来耻辱时,暴力不会缺席。从一开始,朋克带给安德森的就不是暴力反抗,而是某种与父亲所好殊异的“原始与坦荡的生命力”。他见过暴力,那种野兽们热烘烘漫无目的的骚动,并不像电影里拍的那样干净利落。
安德森少年时就读的大型综合学校奥特霍尔,是“一栋威严萧瑟的20世纪30年代大楼”。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在此就读的学生集体卷入部族文化野蛮对抗的潮流,“操场上常攒动着敌对的帮派,校园中随处可见轻微的暴力和要挟行为”。这里存在一种奇怪的错位和残忍,精力被徒劳地消耗殆尽。他选择的音乐反映了真实的周遭,同样的错位不可避免。很长一段时间里,安德森用每分钟33转的速度错误播放45转的朋克唱片,慢速的地狱般的咆哮扭曲了朋克乐的暴力本性。阴差阳错中,这些音乐显出阴郁的美。
安德森开始接近音乐。他抗拒父亲的专横,但父子有一个共同点—对音乐崇高和严肃性不可动摇地坚持。父子无数次的激辩基于一个共识:音乐是催人奋进、超越琐屑的力量,它甚至高于生命。这本书里散见安德森为何决心投入音乐的巨浪,如何寻找伙伴,磨练技巧,琢磨风格,发现想表达之事和表达意义的过程,这里不一一详述,只提两点。
一是糟糕的单薄音响,让他直到二十几岁才“听到”贝司的低频。整个成长期,安德森都不得不透过破损的高保真音响听音乐,养成了听歌只重词曲和和弦序列的习惯,后来写歌也一直追求汹涌澎湃的副歌和简单强大的记忆点。但他没有忘记童年盘桓在家中的古典乐,写歌时常向曾抗拒的古典音乐借鉴戏剧化的技巧。
二是这位热衷走街串巷的游侠,爱把不少歌曲设定在伦敦的特定地区。“我有意回避书写普世经验的陈词滥调,……,我想要好记录周遭所见,真实、不安、细微的世界:缠在树枝上的蓝色塑料袋,电扶梯咔嗒咔嗒的声响——充满美妙而糜烂的细节的伦敦。”“山羊皮”的歌中若有“华丽”,也非对70年代的致敬,“而是根植于人们想要逃离的居所:租来的房间,满是垃圾的人行道,还有宿醉留下的隐隐阵痛”。

这个世界虽然破败、肮脏又怪异,够努力的话,仍能唱出几分优雅与诗意。但不要以为意识到这一点之后,安德森和伙伴们就脱胎换骨,走上年轻乐队迅速成名的康庄大道。他又挣扎了很久,用过失败的鼓机,写过毫无力量的歌,领过失业救济金,一颗心破碎过,才找到能说服自己,打动自己的东西。丧母、失恋和迫在眉睫的贫穷终于凝练,性的骚动和爱的渴望变成声音,他平平无奇的嗓音突然找到了表达愤怒、仇恨、欲望等原始冲动的要诀。
在落笔的过程中,安德森一定又数度重返他生命中的那些“漆黑清晨”。母亲走后的漆黑清晨,他待在霍恩顿街女友贾丝廷的公寓,远离嘈杂,听着钟声,反复感受“失去”在心里轰然下落的失重感。当初恋女友贾丝廷也离开,他再度从黑夜直接滑入漆黑清晨。

安德森和女友贾丝廷(右)在1990年代
最初侵入人生经验的漆黑清晨,或许是安德森童年连续数小时的焦枯难眠,在孤独害怕中“注视着窗帘顶部的褶皱现出一张张狰狞面孔”。日出后,他在窗前远眺马路尽头的一对树木,“目不转睛地望着它们摇晃拍打,它们仿佛受困于永恒的争执,任由狂风的涡流推搡扇动着”。
这些漆黑清晨痛苦而迷人,一再造访他的人生。他与朋友们分享的公寓中,友人随意往来。他们打开窗,让黑暗流入。在朋友、闲聊、烟、傻笑、街道的安全包裹中,漆黑清晨悄然而至。朋友散尽后,他意识到自己依然孤身一人,前途无着。但在贫穷中苦寻意义的日子快要结束,一切将飞速开始。
(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简体中文
简体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