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猿能够变人,仙子幻化成燕子,李太白变红鲷鱼……这些不是童话故事的情节,而是出于名家之手的虚构。
玛格丽特·尤瑟纳尔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发表了数篇故事,故事取材于世界各地的寓言和传说;黑塞的童话集也创作于20世纪初,他的故事与其说是童话,不如说是通过童话体现哲思;卡夫卡的小说创作中除了《变形记》,还有人猿自述变成人的经过的科学报告;谷崎润一郎的人变猴子的故事则带有日式的怪谈色彩。这些故事很多是以“很久很久以前”开始的,当名家开始说故事,他们会有怎样的表现?这些故事或许不算他们最重要的代表作,但读起来也别有趣味。
玛格丽特·尤瑟纳尔《东方故事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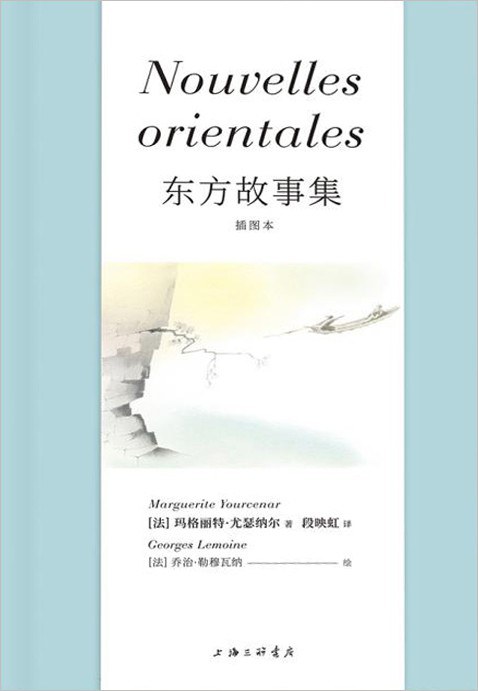
《东方故事集》
[法]玛格丽特·尤瑟纳尔 著 段映虹 译
上海三联书店 2021年2月
《东方故事集》里的故事多数建立在对过去神话和传说重写的基础之上。尤瑟纳尔的故事题材取材广泛,既有希腊传说、巴尔干民谣,也有印度神故事和《源氏物语》,而她重写的重点大都在于欲望,欲望可以战胜坚不可摧的巨人,甚至能达到与天地相通的境界。在取材于中世纪巴尔干民谣的《马尔科的微笑》一篇中,男主人公马尔科在战争中佯装已因风浪死去,想要复仇的人用钉子和铁锤将他的身体打满,用火炭烤他的胸膛,但他纹丝不动,但当姑娘们在他面前舞蹈,他却忍受不了内心的萌动——尤瑟纳尔写道,“忍受酷刑的人嘴角上的微笑,对他而言,欲望才是最甜美的酷刑。”尤瑟纳尔在《燕子圣母堂》里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个严苛的修士受不了凡间四处存在的、诱惑人的仙子,想要将她们栖居的洞口以基督教堂封闭,最终仙子变幻成燕子获救,故事的结局依然是欲望和欢爱战胜了苦修的信条——“泰拉彼翁停下祷告,怀着柔情地观望它们的情爱和游戏,因为对仙女们而言是禁忌的事,对燕子们则不然。”
此外她也重写了仙女“涅瑞伊得斯”的故事。涅瑞伊得斯是希腊神话中海中长者涅柔斯与俄刻阿诺斯之女多里斯结合生下的五十个女儿的统称,泛指山林水泽仙女, 她们天生美貌而善于捉弄人,遇见她们的男子会不可自拔地陷入迷狂:眼见着自己的才智和体力渐渐衰竭,被倦怠和欲望消耗得日渐憔悴。这样的结局虽然不幸,但男子也得以走出事实的世界,进入了幻觉的世界。而在尤瑟纳尔看来,幻觉的世界如此令人迷恋,见识过的人走不出是理所应当的。
黑塞《给所有人的黑塞童话》

《给所有人的黑塞童话》
[德]赫尔曼·黑塞 著 杨梦茹 译
未读/北京联合出版社 2019年4月
《黑塞童话集》的哲思性比奇幻感更令人印象深刻,他笔下的变化并不体现在直接的幻化,更多是个人心性的转变。《神秘的山》里一个意见顽固的人进入群山之间一座不太有名却很险峻的山峰,他怀着征服的欲望,要战胜、夺取和攻克大山,在一次次攀援和受挫中,对自然的爱也逐渐变得充满醋意和猜忌;在某次攀登中他遭遇了事故,从山上坠落、双腿和肋骨摔得粉碎,就在陷入绝境之时,他突然感受到自己的思索和痛苦都与山体相通,而自身的生命与山中物也并无不同,山和人,羚羊和鸟,所有的事物全都在一场无法摆脱的困难中活着,他就在这样的情形下接受了自己垂死的命运,“这个一辈子都不满意,觉得要对抗全世界的人,第一次感受到世上某种和谐与永恒之美,他的心灵为之惊诧……。”黑塞写道,葬身山间的结局并不比人生其他结局更坏,他同意了自己的结局,“他长眠在山的岩石间,遵循着命运的戒律,并不比在度过漫长而且愉快的一生后,被安葬在家乡教堂的树荫下来得坏。”
在另外一篇名为《诗人》的故事里,可以看到和《神秘的山》里登山人一样执着的愿望,只不过征服山脉换成了磨炼诗艺。一位名为韩福的年轻人遇到文辞大师,便拜师学诗艺。开始他感到挫败,诗歌语言根本无法捕捉自然之物的生动和美丽,后来他逐渐体会到,诗歌的艺术看似质朴,却如风吹过水面一般搅动听者的心灵,描述太阳升起和鱼儿嬉戏的情形,如果仔细听,就能听见,“仿若苍穹与这世界每一次于瞬间齐奏无与伦比的音乐,而每一位听众倾听时,各自怀着喜悦或苦痛,念起自己的所爱或所恨,小男孩想着游戏,少年想着心上人,老人则想到死亡。” 追求诗歌技艺的过程,也让韩福身后的世界与时间不再重要和真实。他离开家乡,没有兑现对父亲的承诺,没有迎娶自己的未婚妻。当他多年后再回去时,亲人都已经纷纷离世,又逢花灯节,在千盏灯流过的水面上,他不再能分清何为倒影、何为真实。有意思的是,尤瑟纳尔在《东方故事集》里也处理过技艺世界的真实与现实世界的真实这一主题,在她的描述里,中国画家乘坐自己画成的轻舟消失于画幅之中,这和欲望让人走出现实世界、进入幻觉世界有着相似的妙处。
卡夫卡《卡夫卡中短篇小说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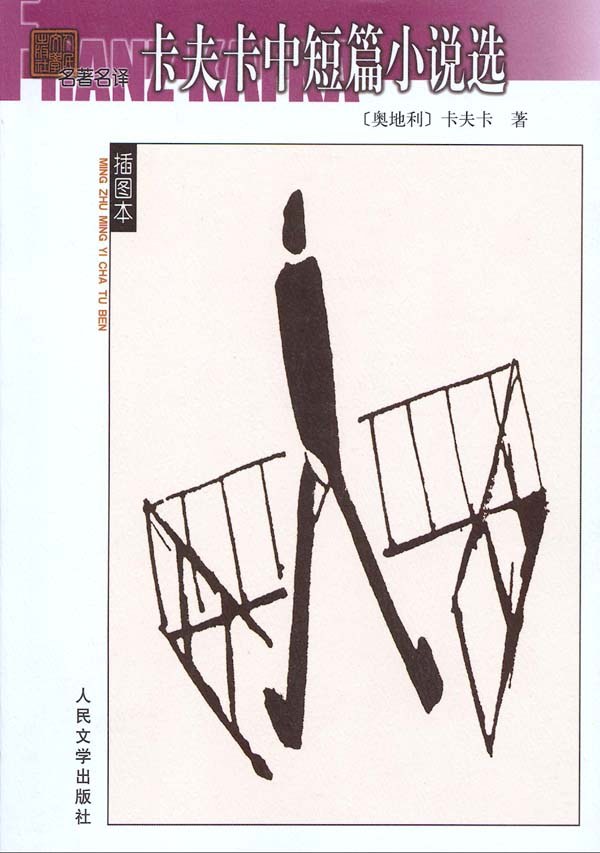
《卡夫卡中短篇小说选》
[奥]卡夫卡 著 孙坤荣 等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4年
多数读者可能都很熟悉卡夫卡《变形记》里旅行社职员格里高利变成甲虫的故事,事实上,卡夫卡还写过一个相反的故事,即人猿变人的故事,也很值得琢磨。《为某科学院的报告》讲述人猿被捕住之后要学着变成人,在变成人的途中他也经历了许多哲学思考,正是这些思考令人类的处境显出了真实的面貌。
故事是这样的:某一个人猿在海边喝水时不幸被人类的子弹击中,装进笼子里,漂泊过海,在笼子里的人猿就开始进行了哲学思考。“他”认为自己需要的并不是自由,而是出路,两者的区别在于自由容易让人受骗上当,因为崇高的希望意味着巨大的失落,还是出路比较实在,所以“他”必须寻找一个合适的出路来摆脱困境。而“他”的出路就在于模仿人类,包括吐唾沫、抽烟以及喝荷兰杜松子酒,因为这样可以吸引人的注意。虽然“他”非常憎恶酒的味道,但为了能进杂耍园子而非动物园,“他”必须提升自己的技艺水平,作者讽刺地写道,不久“他”就用惊人的毅力达到了普通欧洲人的“文化水平”,这为“他”奠定了出路。人猿努力模仿人类,并没有乐趣,而是为了进入杂耍园子;也正是在杂耍园子里他看到,空中飞人在高空秋千上表演,仿佛要变成人猿似的——这种表演让身为人猿的“他”觉得荒唐,“这样的自我约束居然也算人类的自由。”
卡夫卡一直以来对马戏团和杂技表演高度关注,《饥饿艺术家》和《第一场痛苦》都和马戏团有关。前者讲的是一个要超越极限向众人证明自己挨饿本领的艺术家,后者是一个习惯了高空生活的空中飞人艺术家,好像对充满束缚需要苦练的杂耍充满兴趣似的。卡夫卡写道,马戏团艺术家们在技艺上的精进盖过了、也改变了他们的存在本身,也许并非需要跨越物种或者玄幻法术,马戏团技艺本身就能让人或动物完成变形。
谷崎润一郎《怪奇幻想俱乐部》

《怪奇幻想俱乐部》
[日]谷崎润一郎 著 黄洁萍 等译
新民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0年7月
谷崎润一郎的《怪奇幻想俱乐部》也写到了变形,但他笔下的变形更有怪谈的意味。《人变成猴子的故事》讲的是一个艺伎被猴子掳走做妻子的故事。猴子对艺伎的骚扰是变本加厉的,后来还威胁女子,如果不答应,它就会一生一世挡住她的情路,而故事也用算命先生佐证,被猴子纠缠是这位女子的命运,只能随它去了。没过多久,艺伎也确实随着猴子走了。多年后,有人曾在某地温泉瀑布附近看到和猴子玩耍的身影,只见那人身穿破破烂烂的树叶,披头散发,“但从胸前垂着的乳房来看应该是个女人。”
另有一篇讲李太白变成鱼的故事就显得更加荒诞。一位年轻女子收到了一份结婚礼,是一个红绉绸鲷鱼,在她要解开它做衣裳时,这条鱼突然开口与女子对话,祈求她不要这样做,因为它习惯以鲷鱼的形态生存,也在海中游走,只不过这个海并不是咸水而是酒水之海。它就是李太白,极力声称李太白从采石矶落水、沉入长江之后游去了南海,之后就变成了通红的鲷鱼,它不光强调自己是李太白,还打击其他声称是李太白转世的物种(比如鲤鱼、鲈鱼还有章鱼水母等等都说自己是李太白),驳斥其他李白身世的故事,仿佛是对佐藤春夫《李太白》的无情吐槽。这里的两则变形故事,一是少女变成猴子,中间还有算命先生佐证命运不可改,以及路人旁证见过踪迹,细节丰富;一则是红绉绸鲷鱼莫名其妙的自陈,共同点都是与女子有关的怪谈。
 简体中文
简体中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