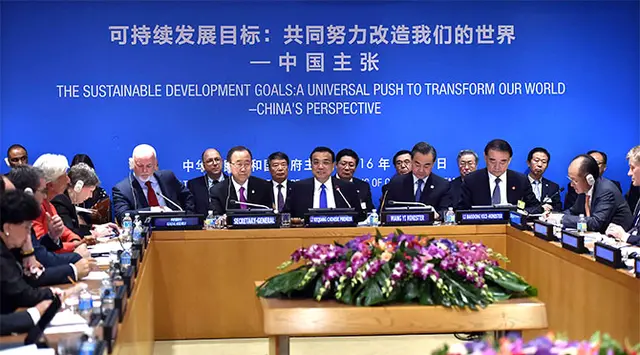当人们反对大火之后的政治抗议的时候,格伦费尔塔公寓(伦敦大火被烧的公寓)烧焦的外壳之下,明火依然可见。“在格伦费尔塔公寓的悲剧中,人们不断嘲讽政策”,灾难新闻发布数小时后,一名推特用户抱怨道:“把这场悲剧赋予政治意义是完全错误的”,另一名网友补充道:“任何想从事故中捞取政治资本的人,都应该在羞辱中绞死。”
然而,即便从狭义上说,政治也关乎权力以及团体内部资源的分配。追踪格伦费尔塔公寓悲剧之后的线索,或者这场觉醒中的挫败,你必然会一头扎进政治中——原始的、关乎生死的、激烈的抗争。正如托特纳姆地区议员大卫·拉米(David Lammy)观察到的那样:“如果火烧到家里边了还不能算是政治,那么我不知道什么才算。”
只要人类还在建造城市,火灾对城市的形塑就如影随形——整座城市的行为方式、受害者以及灾难造成的后果,都与当时的政治秩序密不可分。
“火灾……是一种高度政治化的现象,”《易燃的城市》(Flammable Cities)一书作者解释道,一项关于城市火灾的学术调查揭示了人们如何合法化、强化以及破坏权力。“火灾可以形塑、也可以改变一座城市的统治形式,而且可以利用它将一部分人与另一部分人隔离开。”
火灾的政治性背景,始于防范火灾的系统、以及决策者决定什么人或物最需要保护。首支大规模消防力量的记录,来自于古罗马的城市警卫维吉尔斯·乌尔巴尼(Vigiles Urbani),他在公元 64 年的大火灾中参与了救火行动——那场烧毁了三分之二个罗马的灾难充满政治意味,从讨论火灾的起因(有传言认为,皇帝尼禄是放火烧毁自己都城的元凶),到对城市重建的争论无所不包。
几个世纪以来,各不相同的城市火灾预防措施,被用来加强体制的专制色彩,或者被用以展示自己相对于其他国家的进步、现代化资质。此外,由于火灾而受伤或流离失所的人的社会背景,也可以显示阶级、种族和宗教在城市弱点中所处的不同位置。
“事实上,关于城市火灾政治史的谈论寥寥无几,这本身就是一种政治,”在赫尔大学专门从事灾难史研究的格雷格·班克夫(Greg Bankoff)教授说。他指出,造成这种现象的部分原因,是因为英语的现状——与其他语言不同,不管是化学燃烧过程、还是街区建筑物烧毁时的破坏行径,英语都只有一个词来描述火灾。前者听起来可能自然而中立,但后者就不是那么回事了。例如,在阿拉伯语中,“nar”一词指的是带有温度、热力和光亮的火焰基本形式,而“hariq”则是指由暴力和蓄意破坏造成的火灾。
火灾也有全球意义上的南北划分。北半球(富裕国家)的火灾多指向过去,那时候城市建筑的风尚还是大量使用木材;而南半球(贫穷国家)的火灾,则指向当下持续而巨大的生命损失:据统计,全球每年有 30 万人死于火灾,大部分灾情发生在城市。“公共意识的缺乏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占据西方社会学术圈和决策层主流的那些人,大多生活在西方社会,在那里火灾已经被降格成了一个个人财产问题,”班克夫认为。“然而放眼全球,事情就变得有意思了。”
格伦费尔塔公寓的灾情,被其独立的塔楼街区限制住了。然而和历史上许多重大火灾一样,它使得国家决策的失败显露无疑,并且激起了远超北肯辛顿事件的公共问责。由此,火灾引发了底层社会行动的浪潮,并使关于紧缩、解除管制、以及地方民主问责制的国家关切逐渐成型。它是否会成为制度层面变革的主要催化剂,还有待观察。
但有一点我们可以肯定,这不会是城市火灾打破一成不变政治现状的最后一次。气候变化以及日益加剧的城市化,共同放大了火灾对城荒结合部——那些人类开发区边缘与未开发荒地的交界地带——的威胁。这是个有美国特色的问题,比加利福尼亚州还大两倍的区域,被评为火灾高风险区。
同时,全球范围内正在上升的无固定居所人口——现在的估计是 6600 万——快速涌向城市边缘的新空间,他们往往只是短暂停留、并不常住,这些地方的火灾风险,是最高的。
在这些未来可能发生火灾的地方,我们为阻止灾难所做与未做的事,可以揭示出我们世界的政治结构,甚至可以扮演颠覆它们的角色。“在全球许多地方,火灾可能逐渐远离了大众意识,”班克夫警告说。“而在未来几年内,这种情况就会改变。”
日本,江户(今东京),1722-1723年
一幅印制于 1855 年的木版画上描绘的江户大火。
18 世纪刚刚开始的时候,江户——德川幕府政权的首都,市中心有着巨大的城堡——是当时全球范围内人口最多的城市。城中几乎所有东西都由木头建造,火灾就成了家常便饭,尤其是冬天:空气湿度降到一年中的最低点,从北方来的,吹向海湾的风也最强劲。
当时的官员首要关心的,是保证城堡和军营的安全,这充分反映了当时封建社会的特色。城市其他地方发生的火情,不被作为公众健康事务考虑,而被视为一个社会控制问题。因此,消防系统便依赖于道德规训,以及对惩罚的畏惧。
当发生重大火灾时,官方就利用这机会,将灾难视为人类失败的产物,丝毫不归咎于糟糕的城市管理。火灾也会成为官方展示自身纪律能力的舞台。1722 年至 1723 年间,在一系列火灾发生后,当局发动了一场针对纵火嫌疑犯的暴力镇压。101 人在行动中被捕,他们大多是社会底层贱民或流浪者,最后被烧死在火刑柱上。
里斯本,1755年
一幅描绘 1755 年里斯本建筑毁于地震与海啸的油画。
作为帝国的贸易枢纽和欧洲重要城市,里斯本的发展使其变得充满火灾隐患。当财富不再被君王垄断,新的资产阶级精英开始把火灾视作对个人资本积累——说得再明白点,私有财产的威胁。
1666 年伦敦大火所造成的破坏,使得商人和实业家们不得不将城市防火政策视为公共事业。之所以会如此,或许还因为消防事业有了创新。来自荷兰的简·范德·海登(Jan ver der Hayden)是个博闻的人,他同时也是工程师、推销员、艺术家以及阿姆斯特丹的消防队长。在他还是孩子时,他曾目睹家乡市政厅被大火摧毁,由此他萌生了发明新的移动消防工具的想法,这种工具装备有开创性的喷水软管。
在这样的背景下,1755 年 11 月 1 日,一系列强地震爆发,随后引发海啸及大范围的火灾,由于波及面太广,大火甚至持续了一周之久——这场大火直接将葡萄牙帝国的首都里斯本毁于一旦。火药商店爆炸,教堂、宫殿和图书馆都被巨焰吞噬,庞大的灰尘团从空中倾盆而下,目击者将其描述为“火焰倾泻,来势有如冰雹”。灾难共造成 30 万名居民遇难。一名幸存者说,“自从索多玛和蛾摩拉城被毁之后,我相信世界上还没有哪个地方遭受过这样彻底的毁灭。”
火灾之后,里斯本市中心被拆除,随后的重建工作就完全按照现代风格操作——长长的大道围绕着自由流动的人群和商业活动,建筑物的规模、结构和装潢有着严格的规范。这一景象很快就会在欧洲其他城市上演。
观念上,灾难在欧洲大陆推动了一场意义深远的反思,人们重新评估关于上帝、自然和人类的根深蒂固信念。事件也带来了历史转折,后来为人熟知的启蒙时代到来了。卢梭、康德和伏尔泰都针对里斯本的灾难发表了大量见解,并借此发展他们的哲学观念。
旧金山,1906年
1906 年,旧金山一场 8.3 级地震过后,民众们站在萨克拉门托街上,看烟雾从火焰中滚滚升起。
另一场由地震引发的大火发生在旧金山,时间是 1906 年 4 月 18 日。火灾持续了整整三天,城市居民最密集的那些街区有约 98% 的建筑被烧毁,这场大火灾当时被视为社会均衡器——正如一名记者写道,这场自然灾害“对小旅馆和棚屋、银行和妓院一视同仁。”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20 世纪初,旧金山的城市格局是高度隔离的,山丘和主街道这些物理界限,将不同种族隔绝开来。有的建筑地基坚实,有的只能在垃圾填埋场上找落脚之处。“这场大火以不同的速率和时间,一个接一个地烧毁住宅区,”安德烈·里斯·戴维斯(Andrea Rees Davies)说,他曾当过城市消防员,现在是斯坦福人文中心的副主任,“在火灾发生以及城市作出反应的过程中,旧金山的社会裂痕便展现了出来。”
当火势蔓延到贫穷市民居住的南部市场区时,部队转而保护联邦建筑以及上层家庭,以防备抢劫和逃亡的难民。军人们针对交互光电公司、南太平洋集团这样的大公司启动了应急响应措施,保护他们的货仓,而任由居民区被大火吞没。
同时,作为美国西海岸最大华人社区的旧金山唐人街,也在灾难中被忽视。在一连串的炸药爆炸中,官方消防队几乎没有介入——这些爆炸由消防员蓄意引发,企图造成彻底的火灾,以抽身保护诺布山的贵族建筑。
拉各斯,2002年
2002 年发生在拉各斯市的毁灭性爆炸
那是 2002 年 1 月 27 日的晚间,尼日利亚最大城市拉各斯市北部伊凯贾军事区的一家街道市场着了火,火焰随后蔓延到储藏有高性能炸药的军火库,所引发的剧烈爆炸,甚至在 30 英里外都能感受到。燃烧的碎屑降落到临近的几个街区。在之后的恐慌中,据信有超过一千名市民罹难,多达两万人无家可归。
事后人们发现,此前政府官员忽略了把炸药存放在更安全地点的命令,军方基地指挥官为事故表示了歉意——然而这对于愤怒的拉各斯市民众而言无疑是火上浇油。从 1990 年代到 2000 年代,这场大火是数起洞穿尼日利亚经济文化中心的灾难中的一次,它凸显了尼日利亚经济中的罪孽之处:靠原油出口而获得的大量横财,落入了贪腐官员和商业巨头的腰包中,绝大多数国民却依然穷困潦倒。
这一时期的许多火灾,都发生在充斥着市集、棚户区和高层建筑的城市中,这里的政治和经济形势已经高度紧张——政府资产往往是最后遭难的,人们甚至怀疑,这是政府故意放火以掩盖地方腐败的手段。
政府在应对火灾方面的不力,导致一些消防员遭受到市民的袭击,因为人们指责他们反应过慢且效率低下。作为还击,一些关键的人口密集区被消防局列入不提供消防服务的黑名单。
布宜诺斯艾利斯,2004年
布宜诺斯艾利斯一家音乐厅大火过后,遇难者的亲友们为他们点上蜡烛
2004 年 12 月 30 日,3000 名年轻人聚集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市西边的“克罗马农共和国”音乐厅(Cromañón Republic),以庆祝即将到来的新年。在当地摇滚乐团“流浪者”(Callejeros)表演的时候,喷出的焰火点燃了悬挂在天花板上的塑料网,火焰很快蔓延到剩余的装饰品,而它们大多数都由木头和泡沫塑料制成。燃烧过程中,熔化和燃烧着的残渣不断掉落到下方人群身上。
很快人们发现,音乐厅六个安全出口中的四个都用铁链锁上了——以防止观众逃票。事故共造成 194 人遇难,大多数致死原因是吸入了有害气体。
灾难发生时,阿根廷已结束独裁时代,民主政体已运行了二十年。在经历了导致数百万人丧生的经济危机之后,阿根廷正谋求经济复苏。
在接下来的十年,克罗马农事件及其后续影响,与政治斗争,特别是腐败、人权问题和更广泛的政府失败一起,成为了当代阿根廷挥之不去的梦魇。
祭奠死难者的葬礼游行,很快变成一场示威,人们与防暴警察发生激烈冲突。布宜诺斯艾利斯市长最终受到弹劾,并因火灾事故被免去公职。2008 年的一次审判中,“克罗马农共和国”音乐厅的所有者以及“流浪者”乐队的经理被双双判处徒刑,两名政府官员也因渎职被判有罪。
乐队成员最开始被判无罪,2011 年案件重审的时候,他们被认定犯有谋杀罪,每人受到11年有期徒刑的判决。
(来源:界面)
 简体中文
简体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