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评论家、《西方正典》的作者哈罗德·布鲁姆曾有一个经典的论断,把菲利普·罗斯视为美国当时在世的最伟大的四位小说家之一。罗斯在美国文坛的核心地位确实不可动摇,他在27岁所著的第一部小说就拿下了美国全国图书奖,后来更是包揽了普利策奖、布克国际奖、卡夫卡文学奖等等,唯独与诺贝尔文学奖失之交臂。
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教授但汉松改写了罗斯所著的《人性的污秽》中的一段话来评价罗斯:“你还是得承认这个作家是自多斯·帕索斯以来揭露美国最透彻的人。他把一支温度计插进了这个国家的屁眼。菲利普·罗斯的美国。”“温度计”是在测量一个发烧的国家,正如罗斯在用文字测量美国的狂热。
曾几何时,美国是很多人向往的国度,美国梦的中产阶级神话曾激励了几代美国人和美国移民。而今,民粹主义猖獗,冷战思维在美国社会甚嚣尘上。那么,美国到底是什么?美国的历史、现在和未来,这些谜语的答案是否能到文学中寻找?日前,但汉松在线解读了美国文坛神话菲利普·罗斯和他笔下美国人精神生活的病理切片,借以一窥美国的心灵史。
大历史下的家庭悲剧
罗斯的“美国三部曲”包含了《美国牧歌》《背叛》(又译《我嫁给了共产党人》)和《人性的污秽》三部小说。“三部曲”在情节上并不是一个连续有机的故事整体,但它们在主题和风格上有很多相似的地方。这三部作品也是罗斯由少年得志到步入花甲的一个重要变轨。1995年,罗斯与第二任妻子布鲁姆离婚。两次失败的婚姻,加上前妻对他的辛辣指斥,使社会对罗斯的批评纷至沓来。尽管罗斯落入了情绪的低谷,却同时步入了创作的爆发期。他以一种悲观压抑的笔调,用一种聚焦式的历史思维,去回顾对他生命影响最大的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以及九十年代。
在罗斯的创作生涯中,内森·祖克曼这个角色反复在其作品中出现。祖克曼也贯穿了“三部曲”的始终,他不仅是一个叙述者,还是一个倾听者,是一个故事发展的催化剂。他的身份就像一个侦探,他去探寻三个主人公意识当中潜藏的秘密——有时候是通过交谈,有时候是通过查证,但更多的时候是通过祖克曼自己的想象。罗斯在这个角色上投射了很多自己的影子,可以说祖克曼是罗斯的另外一个镜像。罗斯巧妙地把他安插在小说文本当中,通过他去探寻笔下那些美国悲剧人物的内心。
但汉松认为,“三部曲”采用了“家庭悲剧+大历史”的基本结构。五六十年代以及九十年代波澜壮阔的历史,包括杜鲁门、美苏冷战、反越战运动、克林顿,都在小说中作为重要的背景出现。但同时,“三部曲”中真正的故事聚焦在一些具体而微的、平凡的美国人身上,罗斯是通过一种个人的戏剧化的失败来折射和隐喻一个国家的历史变轨。“‘三部曲’中有三个现代悲剧意义上的反英雄,一个是’瑞典佬’利沃夫,一个是艾拉,一个是科尔曼·西尔克。这三个人都或多或少地承载了各自时代的命运,他们不仅仅是时代的见证者,也是时代的人质,被时代所裹挟所绑架。他们的命运、他们的内心都是时代所塑造的,他们想反抗,但是最终却无能为力。”但汉松说。
《美国牧歌》:幻灭的美国梦神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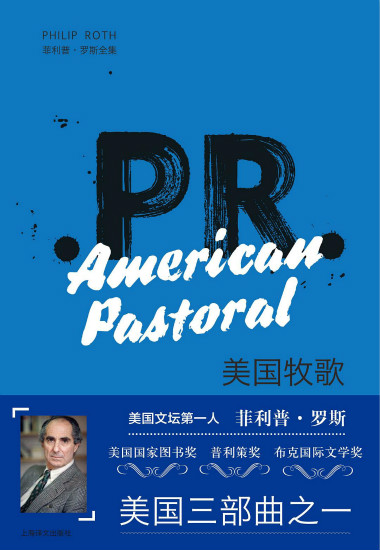
《美国牧歌》 [美]菲利普·罗斯 著 罗小云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20-6
《美国牧歌》中的主人公“瑞典佬”利沃夫是一个犹太人,但他凭借自己的天赋和努力离开了犹太社区,成为了比美国白人中产阶级更像美国人的美国人。瑞典佬是典型的美国梦追逐者,能够按照自己的人生规划去实现野心,是一个践行着“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的手套工厂老板。他还娶了新泽西小姐,生下一个女儿,组成了一个完美的家庭。但讽刺的是,在动荡的六十年代,他的女儿梅丽成为了一个炸弹客、一个恐怖分子。
瑞典佬不明白,他给了梅丽牧歌般的成长环境,她怎么会成为恐怖分子,去放炸弹、杀人,去背叛她的家庭、背叛她的祖国,将胡志明视为偶像。罗斯希望带领读者追问,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发生的,错误是如何铸就的?《美国牧歌》是一部关于美国梦的小说,是一部关于失乐园的小说,是一个美国梦如何变成美国噩梦的故事。它首先是一个典型的家庭悲剧,但在家庭悲剧的背后是整个五六十年代,美国最激烈动荡的20年。正是这个时代,给一个普通的中产阶级家庭带来了撕裂性的影响。
但汉松指出,美国从建国开始就不是靠血缘关系或地缘关系,或者民族国家统一等手段形成的,它是一个依靠神话构建的国家。“五月花号”就是这样的一个神话——你只要相信美国梦,你就可以选择成为美国人。美国梦也就自然包含了一些美国例外论的说辞,包括天定命运论(Manifest Destiny)、“山巅之城”等等,认为美国人是上帝的选民。今天的美国人则认为美国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超级大国,有着世界上最好的工厂。但这种美国梦式的天真正是罗斯想要解构的。越战的故事、种族暴力的故事,其实不只是一个人或一个家庭的失乐园,而是整个国家的失乐园。它把二战后洋洋自得的美国人带进了悲惨的现实中,撕裂了美国中产阶级美好生活的梦想,把发生在亚非拉国家的暴力战争和社会不公带回了美国。小说中瑞典佬居住的田园牧歌式的小城,最后因为1968年之后的种族主义暴力而成了一座废城。
然而在但汉松看来,小说不仅讽刺了瑞典佬这样一位天真的美国父亲,还批判了另一个人物,那就是女儿梅丽,她代表了六十年代那些愤怒激进的美国青年。六十年代美国学生运动激进化,青年们崇拜亚非拉革命,崇拜胡志明、切·格瓦拉、马尔库塞,但这其实构成了另外一种天真。瑞典佬的天真是相信美好的中产阶级美国梦,而梅丽的天真就是希望彻底地打破美国梦,再去寻找一个公正的、普世的、完美的社会秩序。
小说中,梅丽及其同党与瑞典佬就工厂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对于梅丽和那一代激进青年而言,工厂是《资本论》中榨取工人剩余价值的肮脏邪恶的场所。但是对于老一辈的美国人来说,一个世代相传的工厂代表着一种艺术、一种诚实,是美国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一种具体体现。但是那些青年过于天真浪漫,他们对自由的理解其实是偏颇且脱离实际的。小说中的瑞典佬批评他们:“你不知道工厂是什么,不知道制造业是什么,不知道什么叫资本,不知道什么叫劳动,对什么叫雇用、什么叫事业,你连起码的知识都没有。”小说家借此表明,满脑子剥削、压迫、反抗这些大词,这样一种理想主义其实也是危险的。
《背叛》:“每个灵魂都是制造背叛的工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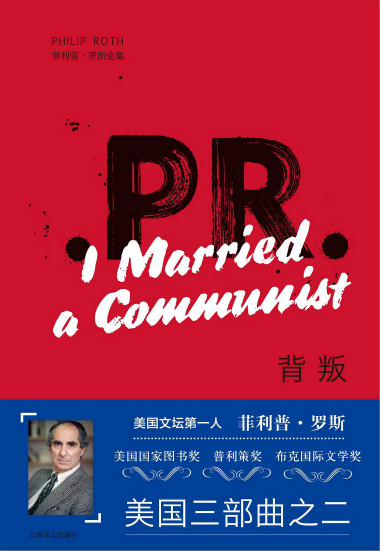
《背叛》 [美]菲利普·罗斯 著 魏立红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20-5
作为“美国三部曲”第二部的《背叛》在主题上与《美国牧歌》有相似之处,它讲述了主人公艾拉美国梦破灭的故事。艾拉出生于普通家庭,他做过挖沟工人、侍者、矿工,接受过美共的教育,对于马克思、列宁、恩格斯都非常的熟悉,他的身上体现了五十年代美国老左派的缩影。艾拉表面上看是一个像托马斯·潘恩一样的美国乌托邦的追随者,但同时他又是一个非常肤浅的人。他年轻时以解放世界为己任,但他后来连他的妻子他都没法解放。随着妻子的背叛,被污蔑为苏联间谍,艾拉的演员生涯告终,幻灭的不仅是他个人的美国梦,更是左派的乌托邦理想。
与《美国牧歌》聚焦于反越战学生运动不同,《背叛》关注了于1950年代席卷美国政坛的麦卡锡主义。因而作品的一个核心主题就是告密和背叛,用书中的原文来说,“每个灵魂都是制造背叛的工厂。”罗斯的文字直指麦卡锡时代的告密文化、背叛文化,这种国家层面的政治气候已经渗入到了普通人日常生活的机理当中。很多人以爱国为名告密,但是这种告密其实带有着一种变态的心理需求:即使不能给自己带来什么好处,他也愿意去害人。
但汉松认为,这部作品更像是一部思想小说。借小说中祖克曼这个角色,罗斯思考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艺术的目的是什么?艺术的追求是什么?艺术跟现实的关系是什么?罗斯写道:“政治最会普遍化,而文学最会个别化。两者的关系不仅是互逆的——还是敌对的。”他认为,文学与政治必然是紧张的关系,因为政治会不断将世界简约成一些类型、一些阶级、一些属性,但是小说家的使命是突破这些概念,是把个体当中最幽微的东西、最不可通约的东西,以最诚实的方式,戏剧化地展现出来。在这个意义上,政治是要剥夺人的自由,但文学是要救赎人的自由。
《人性的污秽》:身份政治背后的伪善

《人性的污秽》 [美]菲利普·罗斯 著 刘珠还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20-6
《人性的污秽》的主人公科尔曼原本是一位古典文学系的教授,他在课堂上使用“spook”(鬼魂)一词描述两名缺席的黑人学生,却因“spook”还有“黑鬼”一词而被学生冠上种族主义者的罪名,他因此愤然离职。但随着故事的发展,作为科尔曼朋友的作家祖克曼发现,科尔曼并非他自称的犹太人,而是一个黑人。这对精彩的反讽烘托出了书中一个重要的主题。小说表面上描写了美国的种族主义给人带来的屈辱、对人的异化,但是科尔曼却背叛了自己的种族:他既不想当黑人也不想当白人,他说“我就想当我自己”。
但汉松认为,罗斯在书中非常尖锐地批判了身份政治。身份政治是一种对差异的崇拜,但是在罗斯看来,不管是什么民权运动,在这些政治正确的说辞背后,这种文化亢奋的背后,都存在着一种伪善和虚假。这种伪善和虚假让一个人明明是黑人,却因为歧视黑人而堕入丑闻的深渊。罗斯认为,所有的身份其实都是一种压迫,所有的身份都会让我们成为一个“非我”。这个主题或许对美国当下的“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反性骚扰运动以及封杀文化(cancel culture)具有警示意义。
(来源:界面新闻)
 简体中文
简体中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