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21世纪走入第三个十年,我们或许已能够以更完整的历史语境审视中国社会在世纪之交发生的剧变:人口的大规模流动,以及随之而来的身份流转、悬浮状态和不确定性。这正是路内最新长篇小说《雾行者》的时代背景。
《雾行者》是路内新长篇三部曲(《云中人》《雾行者》《救世军》)中的第二部。从构思到出版,这部47万字的作品刚好花费了十年时间。时代变迁一直是路内小说中的重要元素。他的上一部作品《慈悲》追踪了50年间的个人命运沉浮,《雾行者》则聚焦于1998-2008这跨世纪的十年,以打工青年周勋和文学青年端木云这两条线索,讲述了一起牵涉伪造身份证的凶杀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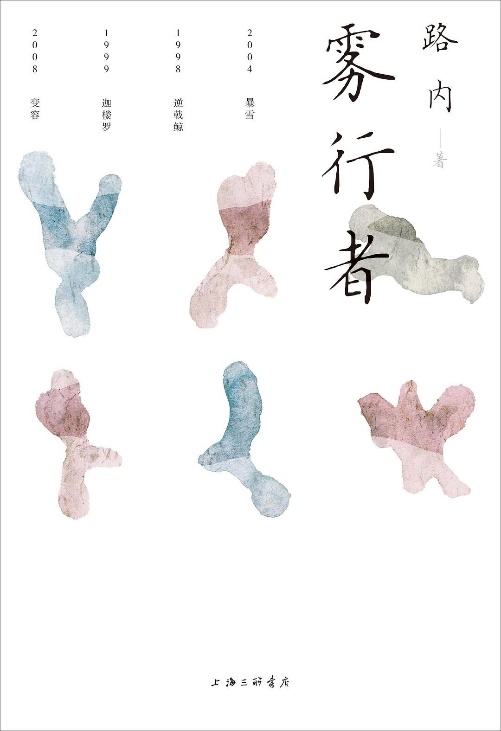
《雾行者》
路内 著
理想国·上海三联书店2020年1月
在日前举行的《雾行者》的新书首发式上,梁文道称自己最早是在杂志上读到路内短篇小说的,读完之后他认定路内是一位长篇小说作家:“因为他的短篇让你觉得故事没有完,或者有一个更大的背景故事被埋在底下,我们看到的是冰山一角,总是有发展的可能。”《雾行者》虽长达47万字,却依然给他这样一种感觉。“这是路内很特殊的一种能力,他总在用他已经写出来的东西去指向一个你说不清的、更大的存在,”梁文道说。
我们该如何理解《雾行者》故事背后宏大而复杂的时代、土地和人物?随着时代更迭变迁,文学又是如何与现实产生关联的?借由活动上路内、梁文道与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戴锦华的对谈和这本新书,我们得以回首世纪之交时刻的中国变迁。

活动现场
世纪之交的人口流动与身份流转
在路内看来,在跨世纪的十年间,他所目睹的最大变化就是人口流动。改革开放后,大规模的人口流动直到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才真正开始。这种巨变带来的感受,首先是无所适从。生于1973年的路内回忆说,在自己的少年时代,如果遇到外来流动人口,就知道某个地方发了水灾,他们是来要饭的。“但是90年代之后,当你看到一批一批的年轻人来到城市,他们没有水灾,他们只是离开故土到一个地方工作谋生。一开始,我所在的那个城市的居民会感到很惊讶:为什么会来这么多人?或者说,国家是怎么了?”
无法理解的新现象常常被人们当成是需要解决的问题。90年代初,流动人口有了一个颇具贬低意味的名字:“盲流”。梁文道回忆了自己第一次来到中国大陆时所见的景象。他想穿过一个广场进站乘车,气温很高,人满为患,十分钟的路程那天一个多小时也没走出去,他困在广场上的人群中,身边的黄牛和盗版碟贩子来来去去。直到公安来了,人群才散开。“在当年,他们把这种人口当作问题来处理,直接拿一个非常强力的水龙头进来冲。一开始大家逃散,但后来很多人就开心地坐在那儿让他冲,因为太热了。本来警察是想赶人走,结果来了一群人躺在地上,洗澡一样。”
“移动很容易包含着一个人身份的改变。身份的改变里面充满太多空隙、太多可能。在那个年代,身体的流动和身份的变化是同步发生的。”梁文道认为,与人口流动同时发生的是人们身份和立场的变化。在人脸识别、监控和天网进入我们的视线之前,在快速的流动过程中,《雾行者》中所描述的身份造假或冒名顶替可能是常见之事。

与人口流动同时发生的是人们身份和立场的变化
在流动的年代里,身份不再构成一个严肃的问题,不仅可以改写,甚至可能在人潮涌动中断裂或消失。戴锦华在对谈中也回忆起了一个看似日常却仿佛梦魇的经历。一次从深圳乘火车前往广州,她在两三个小时的候车时间里坐在候车室读书。偶然抬头,她发现几乎每个方向的座椅面前都有一块电视屏幕,屏幕上播出的不是电视节目,而是寻人启事——没有图像、没有声音,只有一行行快速滚动的文字。绝大多数启事都是寻找家人,上面写着姓名、身份证号、最后和家人联系的时间,知情者请速与家人联系云云。十几分钟过去,寻人启事没有一条是重复的。戴锦华形容那一刻的感觉犹如噩梦,“我并不是一个矫情的人,也不是很易感的人,但我就是突然被那种噩梦的感觉抓住了。你突然发现,就在这十几分钟的过程中,有几百人上千人,他们和家人失去了联系。你可以去想象他们的故事,而我觉得我们的想象力肯定不够。有多少人无奈地断掉了和家人的联系,有多少人不知道在哪里结束生命,可能没有人来认领,没有人来辨识他们。就是那样一个大的过程。如果非常浪漫、非常宏观(地说),你可以说这是一个史诗一般过程。”
漂浮、悬置、不确定,成为了20世纪末21世纪初中国的时代底色。路内提起自己在小说中写到的一个意象:“内省的年轻人离开家乡,涌入城市新建的开发区。那些重工业、老苏联的建筑看上去坚不可摧,但瞬间楼就空了。而开发区里那些轻质构建的厂房,你一看就知道是随时都要跑路的,拆了就能走,但是人们就在往那里面涌。”这仿佛一个寓言:在世纪的结尾,人们离开了传统的、持久的、固定的生活,投入大雾笼罩的时代与大雾笼罩的异乡。

在流动的年代里,身份不再构成一个严肃的问题,不仅可以改写,甚至可能在人潮涌动中断裂或消失
作为世界观的文学观
仅仅讲述世纪交替打工青年犹如漂浮雾中的命运,一部小说已可以足够丰满充实。路内为何选择在《雾行者》里设置一位文学青年?为何要在一部记录时代的文学作品中探讨“何谓文学”的元问题?
路内回应道,在作品中设置现实与文学两条线索,并不是要在小说中间去炫耀所谓的“文学观”。“文学,其实是一部分人的世界观,”他说。他成长于苏州的一个工人家庭,母亲是女工,父亲是工厂的工程师。回忆起青年时代,他提到自己对文学的兴趣其实来自于资源匮乏。他小说中的人物曾经有一段对话:“你为什么喜欢文学?”“还不是因为我们穷么?因为文学,你有一支笔一张纸你就可以开始创作了。”
在家庭穷困、资源有限、父母也没有受过良好教育的情况下,路内认为,一个人基本的人格和审美,只能通过阅读文学作品来培养。“当然那个时候社会风气比较好,你通过看报纸都能知道哪个文学作品比较好,进行自我教育,胡乱地来拼凑自己的人格。等你到了20岁,你就踏上社会了,这个时候再带着你的被胡乱拼凑出来的人格,去和这个胡乱拼凑出来的世界去碰撞。”带着从文学世界中拼凑起来的很多幼稚、极端、不入流的世界观,走入正在发生剧变、不断流动的现实,他产生了自我怀疑和自我否定,并在这个过程中不断推翻自己。这也便是路内在作品中将文学与现实并置的意义。

路内
戴锦华也认为,做文学青年在她的时代的确更像是一种世界观,是一种对于何谓世界、何谓人的整体理解,“今天小说和梦想,和疯狂,和拒绝稳定安逸、物质富足的生活联系在一起。文学青年可能是我们这个世界上一种不合时宜的人,但文学代表我们是人,不是畜牲,不是吃饱穿暖就够了的一种东西。”更重要的是,文学以一种朴素、直接的方式联系着作为实践的人道主义:“就是你爱不爱人,你有没有舍伍德·安德森那种梦想,我想把这个世界的所有空间压成一个空间,把所有的人压成一副身体去爱。”
然而,从文学中拼凑起来的人道主义世界观,如何照进一个不理想的时代?前者能否遏制现实中的暴力和恶行?答案也许不总是乐观的。戴锦华曾读过一本党卫军日记,给她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在前半本日记里,主人公作为一所德国大学里的德语系学生,阅读歌德、学习德国古典文学、哲学,接受欧洲传统人文主义精神的教育。后来他成为党卫军,每天的日记都是关于怎么杀人。这两部分之间没有任何过渡。“二战的暴行对于现代文明是来说意味着很多层的断裂,这个断裂是其中之一,但很少被人们讨论,”戴锦华说,“即欧洲的古典文学、哲学、人文主义传统的教养之下出现的纳粹党徒和德国军人。”
梁文道曾在日本神风特攻队队员的书信中读到一种更为悲哀的撕裂。《神风特攻队、樱花与民族主义》一书收录了神风特攻队队员日记和书信,向我们展示了这群传统认知中最臭名昭著的军国主义者们鲜为人知的一面。神风特攻队的许多成员并非最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而是日本精英大学里的文学青年。二战进行到最后阶段,人手短缺的日本不得不把这些精英分子送上战场,去执行必死的任务。临死前,在与同学、老师的最后通信中,他们谈论的是读书心得。“他们很多是左派,很多是共产主义者,讲马克思和《资本论》。很多在谈歌德、康德、孟德斯鸠,也有自由主义者。那个心态变化很有趣,”梁文道说。这些文学青年被迫接受了为国牺牲的任务,当死亡无可避免、迫近眉睫,他们如何说服自己这是一件有意义之事?文学此时派上了用场。梁文道提到,他们最后的绝笔信内用到了大量文学隐喻,把自己冲向美国基地或战舰这个行为形容为烈火新生,如同涅槃。“他们认为自己的牺牲绝对不是为这个军国牺牲,而是要毁灭日本。他们认为,我这么死,我们国家就能彻底完蛋,就能带来焕然的新生。很多左派青年希望这一次日本能得到教训,让日本经过彻底的毁灭,然后建立一个社会主义新日本。”在这些充满文学意味的绝笔信里,这些青年将毕生的文学理想用于处理一个问题:我怎么看我的死跟这个国家之间的关系。“我非常不认同这个国家、我觉得我死得没有意义,但我现在必须给它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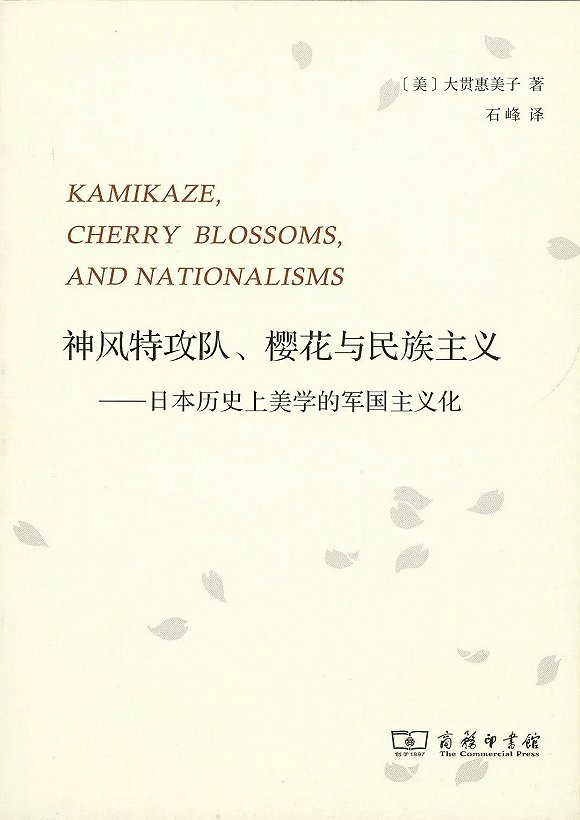
《神风特攻队、樱花与民族主义》
大贯惠美子 著 石峰 译
商务印书馆 2016-10
二十年过去,世纪之交的某些挣扎和困惑如今已开始显得过时。在写作《雾行者》期间,路内的感受尤其明显:“这个小说写的是一代身份证的冒用。但是当人脸识别出现的时候,你就骗不过去了。你用的是电脑,电脑不会跟你撒谎。”如同90年代作为“问题”的人口流动,在21世纪的第三个十年,我们需要面对的或许是面对后人类现实的问题。
“当人们恐惧着人机大战的时候,可能更大的问题是,人类把自己提升或者降低为机器。那时候可能就不再能定义人与物了,这个更值得我们恐惧。或者是赛博客化的人类人体与肉体凡胎的人类的分化,比阶级分化可怕一百万倍。”戴锦华指出,“最近我开始讨论未来,因为我真的觉得我们的未来成为了问题。我并不担心未来是影像主宰表达,还是文字继续主宰我们的表达。我关心的是人类是否还有未来,以及怎样的未来。”面对新的时代议题与焦虑,今天的文学还能为我们提供一种世界观、烛亮复杂而荒诞的现实吗?
 简体中文
简体中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