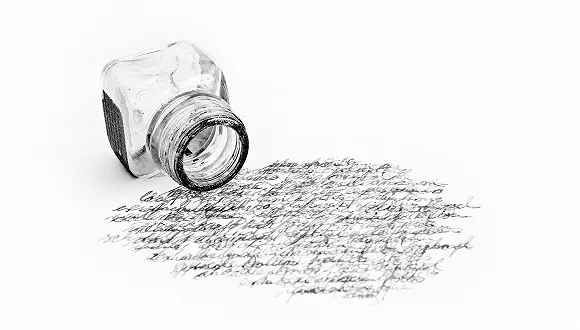诗人北岛日前在豆瓣上发出了自己的一首诗歌,题为《进程》:“日复一日/苦难/正如伟大的事业般衰败/像一个小官僚/我坐在我的命运中/点亮孤独的国家/死者没有朋友……我建造我的年代/孩子们凭借一道口令/穿过书的防线。”作者在社交账号发表诗歌,本是与读者建立联系的良好契机,而诗人与诗作却遭受到了猛烈的攻击,北岛随之将评论区关闭并称:“这是讨论诗的平台,但不应使用语言的暴力。我从此关闭诗和诗的评论区。”
2017年,北岛曾挪用奥地利诗人里尔克《安魂曲》的诗句,“因为生活和伟大的作品之间总存在某种古老的敌意”(这原本指的是诗人难以保持生活与艺术的距离), 以鼓励诗人在全球化同质化的时代中保持质疑与追问,“为什么中产阶级生活方式不可能产生伟大的作品?为什么体制中的诗歌创作课不能制造伟大的作品?”在今天,“古老的敌意”似乎也指向了诗人的诗作与受众之间的关系,这不禁令人发问,读者真的读懂诗了吗?一首诗应当如何阅读?或者说,如果一首诗与现实相关,我们应当如何理解诗歌与现实的关系?借着近期出版的几本书,我们来谈谈如何读诗。
拆解诗的标准:《什么算是一首好诗》

《什么算是一首好诗:诗歌鉴赏指南》
[德]汉斯-狄特·格尔费特 著 徐迟 译
三辉图书·人民日报出版社 2020年2月
在《什么算是一首好诗》一书中,柏林自由大学教授汉斯-狄特·格尔费特将诗歌定义为“语言的结晶”,并提出了品鉴诗歌的多重标准,其中一条标准是“客观与真实”。
他认为,好诗的标准之一应当是它既不是私人独白,也不是纯粹直陈事实,而是来自人类内心并能与其他内心产生共鸣的东西。诗歌最特别之处就在于反映主体真实的声音,同时保持在普罗大众之中的客观性。
诗歌如何徘徊在主观性与客观性之间?格尔费特以一位步入中年的诗人的诗歌为例,证明这首诗虽然抒发的是真情实感,但仅仅从个人角度出发,并未达到客观化的要求,读者仅仅能从诗人个人命运这一点上形成共鸣。
诗歌客观化的美感的要求,来自康德对美的定义,即无利害的愉悦,所谓的无利害指的是以一种审美的目光观赏,而非以一种功利的打量。作者认为这就是艺术的审美感念与启迪性当中最为重要的,就像优秀的音乐和绘画一样,能够将主观的东西广泛地客观化的诗歌,可以使得诗人的个人经验超越个人的范畴,令更多人感同身受。
反讽与幽默是另一条有意思的标准,作者以海涅的反讽诗为例,展现了反对传统的力量有多么强大。诗人海涅在浪漫主义热烈发展的情形下出现,而他的诗作像是对浪漫主义的一盆凉水。他有一首诗是这样讽刺爱情故事的老套的——“少年爱上一个女孩/而她却选了另一个/她爱的却另有其人/那两人双宿双飞……这故事多么老套/却总在新鲜出炉/要是落在谁头上/谁的心儿碎两半” 。另一首诗描绘了一位傍晚海边吹风的女孩是如何感伤——“站在海边的少女/叹息悠长而惊惶/日落西山/触动她无尽的感伤。/我的小姐!清醒点吧/这只是一出旧戏/它刚刚从前方落下/又将从后面升起”。作者认为,海涅通过嬉笑怒骂为他的诗歌赋予了“沙龙式的轻盈感”,从而保证了诗歌的真实性,相比之下,那些比他更严肃的同行只是严肃地沉浸在过分感伤的无病呻吟之中。
《什么算是一首好诗》一书强调,诗歌的本质就是一些超出期待的东西。对于诗歌赏鉴,作者贯穿全书的一个观点是:所有艺术——包括诗歌艺术——都是从对凡常的偏离中产生的。诗歌的语言、比喻以及风格更应当与日常有所区别,诗歌应当反对“刻奇”。
“刻奇”指的是流行的俗套、那些过度感伤与浮夸的表达,在作者的定义中,这个概念虽然在20世纪初才被提出,但19世纪初就人尽皆知了。“刻奇”夸张地表现个人情感,甚至溢出艺术载体,刻奇要么呼唤回归天真、故乡和自然,要么皈依于当局权威、爱国忠君,正因为刻奇具有麻痹人心的作用,所以格外具有感染力甚至令人上瘾。纳粹就是用“刻奇”艺术诱惑德国民众陷入歧途的,“他们用纽伦堡党代会闪闪发光的穹顶为人民降下了一场迷狂的庄严阵雨,又用血与土的艺术满足了百姓回归美好世界的那份渴求。”然而,这“刻奇”的盛宴,提供的不过是虚伪的归属感罢了。
诗歌公共性的必要:《从催眠的世界中不断醒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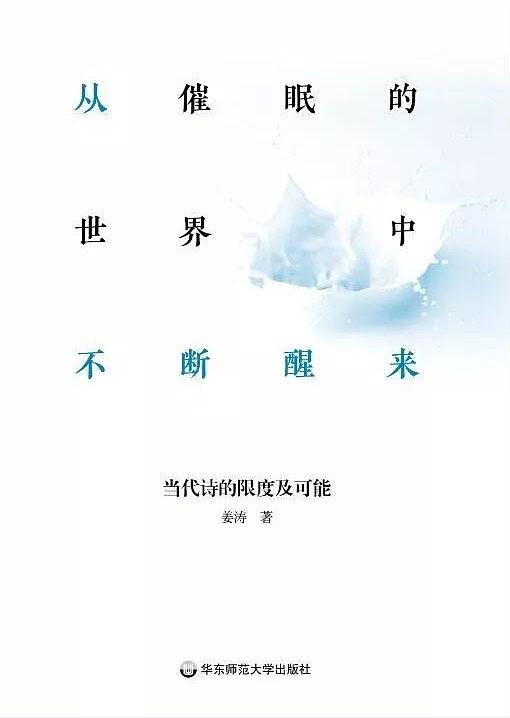
《从催眠的世界中不断醒来》
姜涛 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0年1月
汉斯-狄特·格尔费特认为诗和小说不同,小说家的现实是不断变化的人类生活,而诗人的现实是经过锤炼的普遍适用的经验。那么诗歌应如何书写现实?诗人应放弃这“不断变化的”现实的具体的生活吗?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姜涛在《从催眠的世界中不断醒来》一书中似乎在反对“诗歌与生活之间有古老的敌意”,他认为,诗人在为诗歌建筑门槛的同时,也应当意识到诗歌有公共性的必要,因为诗歌对于现实应当有质疑与反思的力量,安守于诗歌手艺与内向抒发的诗歌可能会丧失与现实对话的力量。
在《浪漫主义、波西米亚诗教兼及文学嫩仔和大叔们》这一节内容中,姜涛分析了诗歌行业化的现象:一些资深的写作者将写作视为严肃的、需要磨练的手艺,遵守行业自律,内心存有伟大诗歌传统的谱系。而他认为,为诗歌写作树立行规、建设门槛的做法,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具有革命性,但在外在的环境改变之时,行业也可能转向内向化、保守化,缺乏自我更新的能力。诗人固然可以勤勉地、严肃地写诗,然而这些诗歌是否真正有价值,或者说是否与现实相关,却是存疑的。在这里,维护行规似乎与诗人的形象相悖,诗歌效忠的也只有行规而已。
具体到前些年广受热议的工人诗歌来说,它们不仅仅是记录工人生活的资料,或者是供其他群体想象工人生活的消费品。工人诗歌体现出了内在的丰富性以及对语言的探索。以矿井工老井的诗作为例,他在他的矿井劳作经验中引入神秘的自然感受,“漆黑的地心,我一直在挖煤/远处有时会发出几声,深绿的鸣叫/几小时过后,我手里的硬镐/变成了柔软的枝条。”诗中并没有常见的“诉苦”或“对抗”的主题,这不仅展现了工人诗歌中可能存在的丰富性,甚至有可能打破知识分子与工人的二元结构,最终使得“他人的眼光”转化为一种普遍的体悟。
姜涛在书中对“文学公共性”意义的阐释尤其值得注意——他提倡文学的公共性,并不是鼓吹公共题材的优先性,以耸人听闻的头条博取公众的注意力,而是指向创造出一种联动的思想氛围,使得作者与读者可以破除各自原有的认识格局,从而认识到他人的处境、发现现实中的责任与权利,最终翻转“文艺孤独的美学内面”。
“文艺孤独的美学内面”可能是这本书中反复提到并质疑的、与诗歌的公共性关怀相反对立的一面,也是贯穿中国新诗发展的潜在脉络之一。姜涛认为,很多诗人写诗都是将一个文艺孤独的、去政治化的自我当成前提,这也造成了诗歌见识比较浅的结果。在《从“蝴蝶”、“天狗”说到当代诗的“笼子》中,姜涛如此写道,与温柔敦厚、普遍亲切的古典诗相比,中国当代诗有一种走向“狭”的趋势。如朱自清《诗言志辨》所说,中国新诗就是建立在与政教系统分离的基础上的,古诗作者写诗与社会人伦、政治关系紧密,而当代诗人成为了纯文学的创作者,与之对应,当代诗人的角色也发生了变化。
当代诗人不再有兴趣扮演启蒙者、反抗、文化英雄,他们更倾向于“不及物”的书写、构建纯文学的另类现实,但问题在于,如果诗歌越来越狭窄,那么“制度性的人格的封闭与偏枯”也普遍存在,然而现实本身是不值得书写的吗?日常生活的字词不能入诗吗?并非如此。书中写道,“尘世不是一地鸡毛的平庸琐碎,更不是泡在荷尔蒙里的物质或身体,它同样是一个极其严肃的领域,需要诗人的写作去探索、去塑形。”毕竟,诗意的世界并不是真实社会的“飞地”。
杜甫的价值:《诗的引诱》

《诗的引诱》
[美]宇文所安 著
译林出版社 2019年7月
姜涛在评述中国新诗时,有意将之与中国古诗做对比,那么,如果说中国古诗确实内在于政教系统,与社会政治关系密切,它又是如何做到的呢?在《诗的引诱》一书的“杜甫”一节中,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提出,杜甫许多诗作都是对于重要政治历史事件的反应,远远超过同时代大多数诗人,正是这种与历史的契合度——具体到对安禄山叛乱事件的记录——为他赢得了“诗史”的称号。
宇文所安从对杜甫的生平追溯中得出了这位诗人关注政治历史的原因,杜甫出生于京城地区的一个古老而有名望的家族,家族与京城地区的联系加强了他对于国家的关注。安禄山事件是八世纪中叶的重大事件,盛唐诗人不可能没看到这件事的重要性,但奇怪的是,重大事件却很少被写入诗歌。宇文所安说,这并不能说明当时的诗人无动于衷,只是体现出了诗歌本质的普遍观念。比方说战争只能在送别、个人叙述及游览战场的诗中顺便提及,而杜甫写到了具体的战争以及个人经历,这使得他的作品风格发生了独特的改变——在战乱前,他与同时代的诗人显示出了许多共通的地方。
公元755年底,安禄山在洛阳称帝,叛军向西击溃唐军,玄宗仓促逃离京城,途中处死了宰相杨国忠和玄宗宠妃杨贵妃。几年后,杜甫根据叛乱爆发后自家的迁移经历,书写了《彭衙行》,详细叙述道,“忆昔避贼初,北走经艰险。夜深彭衙道,月照水白山。尽室久徙步,逢人多厚颜……“这首诗以诸多细节描述了杜甫一家艰难上路的情形,小儿啼哭饥饿,途中遭遇雷雨,路上湿滑泥泞,更觉衣裳薄寒,兼及用野果充饥、在山林间露宿的经历。宇文所安认为,这首诗虽然叫做“行”,但并不符合八世纪关于“行”的概念,更是一首以自然主义风格写就的应景诗。
杜甫不为约定俗成的诗歌体裁所限制,书写了其他诗人未曾提到的事物,杜甫甚至在诗中简述了城中衾裯只能换斗米的市场价格:“城中斗米换衾裯,相许宁论两相直”——后代诗人注意到了这一点,并开始有意模仿杜甫的自然主义与细节书写。在将家眷迁至安全地点后,杜甫又多次陷入政治风波,先是被叛军捉住,逃离叛军阵营,到达凤翔行都,被授予左拾遗,再度陷入政治风波,后来终于得以离开朝廷回家省亲,也是在这次去羌村的途中,他写下了最著名的叙事长诗《北征》。
正如宇文所安指出的,杜甫对中国诗歌的贡献在于对题材的处理。杜甫作诗大大超出了传统题材的限制,开辟了许多新题材,诸如儿子生日、庭树枯死等,扩充了既有题材的范围。中国文人写诗会抱怨官场对个人的束缚与个性的压制,但并不会具体书写诗人坐在桌案前面对大叠公文的情形,杜甫却有这样的创作。他在一篇“苦热”(苦热的诗题来自南朝)诗中书写了自己在炎炎夏日被公文逼疯的情形,“束带发狂欲大叫,簿书何急来相仍。南望青松架短壑,安得赤脚踏层冰。”
这里需要指出的一点是,杜甫的诗歌并不是完全的自然主义书写,他笔下的自然具有象征意义,宇文所安称他为或许是最不愿意让自然界以本色呈露的一位诗人。《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的“茅屋”与“大厦“在自然世界与象征世界之中自由移动,这样一来,作者并非在向朝廷权威祈求,而是向宇宙秩序的更高权威祈求。
随着杜甫诗人自我形象的成熟,其晚年的诗歌也阐述了对于文学价值的看法——“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在诗歌创作上,这句话表现为杜甫坚定持续地做着永久、秩序及文明的表达。正如宇文所安所谈到的,杜甫与同时代人一样对自然表现出了敬畏,但更偏向于秩序、文明以及艺术的一边,而这在唐代诗人中是非常少见的。
 简体中文
简体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