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爽张恒事件引发了大量关于代孕的讨论,人们的关注点聚焦于代孕产生的伦理问题、中国目前的代孕规制,以及商业化代孕对女性和儿童利益的损害。但如若查找文献,我们会发现十几年前的代孕问题研究和今天的讨论范围几乎相同,有关伦理法律的理论之争浩瀚如烟,而关于现实的描述总是支离破碎,散落在时间的轴线之外。我们很难知道,代孕问题是如何发展至今天这一步的。
想要了解当下,总是无法绕开过去。当代孕的历史被淹没在激荡的现实与喧闹的声浪中时,我们回到文学,冀望捡拾几块时间的贝壳。观20世纪30年代的乡土文学,代孕问题野蛮地从“典妻”中浮现出来,继承了“五四”思想的新一辈作家不耻于“吃人”的“借腹生子”,而新世纪作家却以中日战争、文革等历史为背景板,将女性重新锁进“大地之母”的角色中,这种用历史架空历史的叙事失败在莫言的小说《蛙》中得以巧妙呈现:莫言的《蛙》无疑是一部生育史,而整个故事的讲述者蝌蚪却因无力反思这一沉重的历史导致了两种失败——一个是自我救赎的失败,一个是叙事的失败——作为丈夫和父亲,他因软弱在计划生育中失去了妻儿,却错误地通过找人代孕生子来赎这份罪,造成了另一种他无法认知、无法讲述的悲剧。
“典妻”与“借腹生子”:女性的自我与名分之争
如今人们讨论的代孕一般指人工授精代孕和试管婴儿代孕,代孕母亲不需要和委托方发生性行为,但在这些代孕技术出现之前,有性行为的“借腹生子”早已存在。“有我的使女辟拉在这里,你可以与她同房,使她生子在我膝下,我便因她也得孩子。”西方将代孕上溯至《圣经》故事——拉结嫉妒姐姐利亚为她们共同的丈夫雅各生了四个孩子,自己却难以怀孕,便如是将自己的侍女辟拉献上,以求得子。中国的借腹生子故事则常常与“典妻”关联。
所谓“典妻”,便是将自己的妻子按一定期限租与别人。受典者大多没有儿子,租妻便是为了延续后嗣。据清人徐珂的《清稗类钞》,典妻在吴越之地时常发生,成俗久矣。民国时期,在“五四”精神的影响之下,冥婚、人肉药引等“吃人”陋俗成为文学揭露和批判的对象,典妻也不例外,20世纪30年代,左翼作家柔石的《为奴隶的母亲》与乡土作家罗淑的《生人妻》即以此为题。

《为奴隶的母亲》
柔石 著
除了宣扬个体的独立自由,“五四”对“人”的另一项重要发现在于把女性当作人来看,立志于将女性从贤妻良母的身份中解放出来,让她们堂堂正正做一个人。柔石没有让春宝娘(《为奴隶的母亲》)像卖草人的妻子(《生人妻》女主人公)那样逃跑,他通过春宝娘被典后的故事讲述了传统代孕方式对女性的伤害:春宝娘被迫与自己原来的孩子春宝分离,在新家被秀才的正妻百般刁难,忍气生下秋宝后又被剥夺母亲的身份,只能当孩子的婶婶,等典当期限一到,她又要二次经历母子分离,回到家中,春宝也不再与她亲近。春宝娘虽然逆来顺受,不如《生人妻》女主人公那么具有反抗精神,但这两篇小说无疑都对女性作为人的遭遇抱有义愤和同情。作者没有把她们套进妻和母的壳子里,为了让这些壳子显得光辉神圣而改造她们愤怒、屈辱和痛苦的能力,相反,藉助“借腹生子”这样有悖常伦的情节,小说对“从来如此”之事提出了质疑——从父从夫不是天经地义,而在“吃人”的父权社会为母,不过是当奴隶。
严歌苓的小说《小姨多鹤》同样讲述了借腹生子的故事。比起这两篇30年代的小说,严歌苓的语言和叙事自然更新,但思想上却绝看不出对“五四”有什么继承和发展,倒不如说是大踏步后退。小说主人公竹内多鹤是日本战败后被抛弃在中国东北的孤女,她几经艰难,逃过死亡,最后被装进麻袋卖给张家作为传宗接代的“工具”,生下了三个孩子。坎坷的身世再加上后来经历的种种政治运动以及家庭纠纷没有激起多鹤的怨恨,反倒牵引出严歌苓所崇拜的女性气质以及她信奉的“女性主义”——坚韧、忠贞、跪着宽容一切,换句话说,近乎消灭了自我的任人宰割。
多鹤一面要微妙地平衡她与张俭之妻朱小环的关系,一面又要以饱满而纯真的热情去迎合张俭的情欲,同时还得为三个孩子无私奉献。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讲师马兵在评论这部小说时说,“小姨多鹤”的称谓暗示了多鹤“名分的尴尬”,“但无妨这个韧劲十足的女人依凭身体次第展开的母性、情人性和妻性。”
母性、情人性、妻性,恐怕便是这类代孕文学的终极要义。在这些作品中,代孕女性不光要满足男人的生殖需求,还得满足他的性需求,并且通过自我压抑来成全家庭与社会秩序的正常,历尽磨难屈辱之后才能获得名分(最终成为妻)。这听起来与一些霸道总裁代孕女友文相似,只不过严歌苓用历史苦难替代了“玛丽苏”作为叙事的刺激和推力而已。对于这类文本而言,女性的身体被降格为男性与社会欲望的载体,身体不再是她与世界接触的媒介和自我存在的证明,曾经从名分中解放出来的女性又再次被囚进牢笼。

《小姨多鹤》
严歌苓 著
作家出版社 2008-4
莫言的《蛙》:生育史视角下的商业代孕
在莫言的小说《蛙》中,现代代孕技术登场。成为代孕母亲的陈眉可以说非常符合黑市商业代孕孕母的标准相:出身农村、受教育水平有限、经济条件差、急需用钱。陈眉本是高密最美的女人,她南下广州打工,却被工厂里的一场大火毁容,回乡后,为了筹措父亲陈鼻的医药费,无奈在牛蛙厂为蝌蚪和小狮子夫妇代孕——这座牛蛙厂看似做动物生意,实际上是做人口买卖,里面有二十来位女性为出大价钱的高官和商人代孕。
上世纪末,中国第一例试管婴儿及代孕婴儿诞生后,代孕黑市逐渐形成。武汉某代孕公司负责人王峰曾向财新记者表示,国内做一单代孕业务的利润在30%-60%。这个灰色地带需求大、利润高,中介机构向委托方收取高额费用,支付给代孕母亲的则很少,两头盘剥。《蛙》中的陈眉生下儿子后,说好的代孕费五万元缩水成一万。从工厂到蛙(谐音“娃”)厂,陈眉的身体一路受资本盘剥:毁容用一块黑纱将她罩住,分隔于“正常”社会之外;代孕又掏空了她最后的精神——体内孕育的生命给了绝境中的陈眉一丝希望,她觉得自己是一个丑陋的破茧,却有生命在其中孕育,然而这个生命一出世便被夺走,“我(陈眉)就成了空壳。”
生命连接着喜悦、憧憬和爱意,许多代孕母亲都有类似的体验。然而,莫言笔下的代孕还有些救赎意味,这是陈眉的自我救济,更是全高密人经历计划生育之后的集体救赎。小说中的姑姑万心是一名乡村医生,她用双手迎接了上千个婴儿,也用这双手断送了上千条生命,她是送子娘娘,也是阎王爷。年轻时候的姑姑是最坚定的政策拥护者,宣称“党指向哪里,我就冲向哪里”,老来却被蛙和婴儿化身的恶鬼纠缠,认为自己“不但有罪,而且罪大恶极,不可救赎”。计划生育几乎改变了小说中每个人的命运,它像挂在高密人心头的石块,不管他们再怎么烟酒鱼肉假装寻常,只要稍稍扭动,必会扯起一阵钻心的痛。蝌蚪从前不敢阻拦姑姑强制自己的第一任妻子王仁美流产,导致手术台上一尸两命,而陈眉之所以会去打工,就是为了把超生费连本带息地还给嫌弃她是个女孩的父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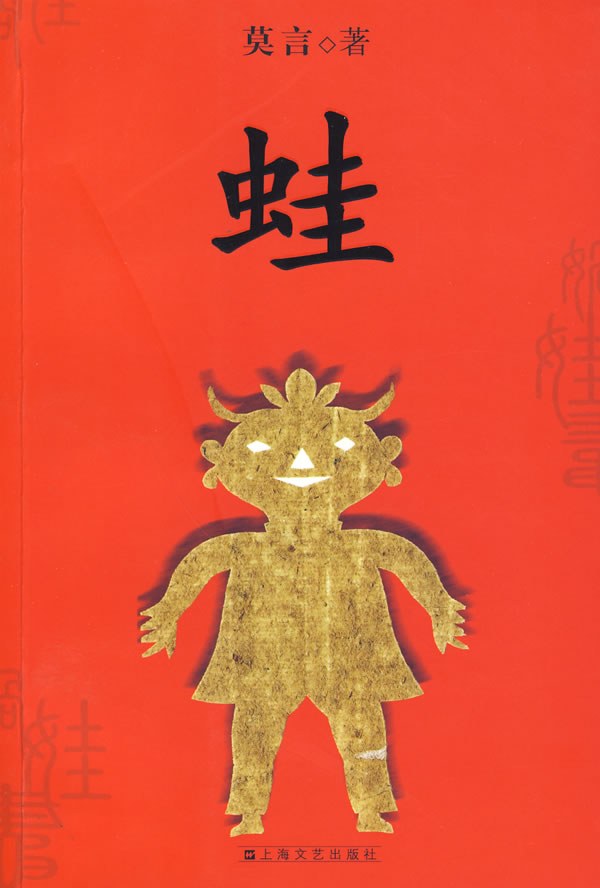
《蛙》
莫言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9-12
清华大学卫生法博士刘碧秋在《我国代孕的立法与司法问题》一文中提出,现有对代孕问题的讨论,不论是权利、尊严还是经济分析的进路,都没有抓住中国人对生育“最核心、最本质”的理解。带着20世纪的血腥战争以及计划生育造成的创伤,中国人对生育的复杂情感恐怕不是传宗接代、种族延续、天性自然所能统摄的,它还涉及一种“更日常的、生育本身的尊严”。正如刘碧秋指出的,代孕在中国被“一胎”政策嵌入了独特的语境,抛开其余伦理问题不谈,一方面代孕合法化会扰乱“一胎”政策所代表的国家人口治理术,另一方面却从补救该治理术所造成的“失独”问题中获得了正当性。
对当年的悲剧,蝌蚪觉得只有生一个儿子才能“赎罪”,姑姑也觉得帮这个计划外的孩子名正言顺地出生能够补过,于是,全乡人在小说第五部分上演了一出合骗陈眉、夺走孩子的闹剧。他们渴望洗清自己手上的鲜血,却没想到这救赎是另一种荒唐和残忍,罪恶牵连着罪恶。中国艺术研究院学者李松睿如此评论小说《蛙》:
反思与叙事无能:代孕故事中的历史缺位
有趣的是,《小姨多鹤》和《蛙》中都浮动着日本帝国主义的暗影,尽管它日落西山,但依旧在大地上留下一片阴影。对此最简单的解释是,似乎只有在叙事中掺入更泯灭人性的战争作为背景,流产、借腹生子、代孕等有违人伦的情节才能获得谅解。多鹤作为日本女子为中国人传宗接代,带有一种强烈的政治性赎罪意味,也唯有她是战败了的日本人,“一夫二妻”才在新社会情有可原。只不过严歌苓没有把这种民族对民族、国家对国家的赎罪作为多鹤的动机,多鹤和她笔下的许多女性角色一样有着无可救药的单纯,她所做的事全都出于私人的爱——爱男人、爱孩子。在曾经的敌国生活,多鹤从未想过融入中国社会,却“因为致命地爱上了张俭,不加取舍地接受了他的祖国”。
历史就这样与人物分割开来,漂浮在故事背后,偶尔在有需要时为故事提供一点合理性与刺激,却无力成为故事的一部分。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曾在《拼贴、讨巧与落后的女性观:严歌苓笔下的大历史小人物》一文中分析认为,严歌苓擅长写大历史下的小人物,但历史于她的叙述而言只是“一层简单的包装纸”,“为故事添一圈光环”。因而,这类历史叙事总是失败的,它飘飘悠悠,轻轻一吹就飞走了,没有厚重之感。

1983年北京街头的计划生育海报。来源:视觉中国
《蛙》中的文学爱好者蝌蚪遭遇了同样的失败。莫言的《蛙》由五部分组成,前四部分是蝌蚪为写作姑姑的一生收集的素材,第五部分是蝌蚪最终创作的小说同名剧本,每一部分开头都有一封蝌蚪写给日本作家杉谷义人的信。按原计划,蝌蚪应该在剧本中有序地呈现姑姑的一生,前四部分的素材积累也依时间顺序展开,一切清晰稳当,但第五部分的戏剧没有呈现姑姑的一生,只能勉强看作对第四部分代孕生子的补充,时间在这里戛然而止,线性而有逻辑的故事变成了几个混乱的场景。作为整个故事的讲述者,蝌蚪在这里陷入了叙述的无能,好像他对自己、姑姑以及所有高密人罪与孽的反思冲垮了他的语言表达能力,一部生育史的书写最终失败。
李松睿认为,这种失败是因为无力认识现实。当蝌蚪得知杉谷义人是当年侵略高密乡日军将领的儿子后,他开始在信中展示自己在道德上的优势,宽恕为父忏悔的杉谷,并表示当今世界最欠缺的就是杉谷这样正视历史的精神,“如果人人都能清醒地反省历史、反省自我,人类就可以避免许许多多的愚蠢行为。”然而,在第三封信里谈到计划生育时,蝌蚪又显示出有悖此精神的优越感,相信可以为了地面上的雄伟的建筑而忽略建筑下的“白骨累累”。故而他的反思总是残缺的,以致推倒出用黑市代孕来为自己赎罪的方案,姑姑等人莫不如是。高密人深感罪恶,却不敢也不能细想其由来,最后为了金盆洗手而把孽债抛给最弱者,用牛蛙养殖场里的黑市代孕来粉饰蓬勃的假象。
日本在此不止象征着战争对整个国家人口的屠戮,它还与自我构成了一组道德水准和历史反思能力的对照。许多专家在分析当下代孕黑市时都会指出,黑市难禁的一个原因在于需求大,需求又从何来呢?《蛙》的结尾处,姑姑问根本没有怀孕的小狮子奶水多不多、旺盛成啥样儿,蝌蚪回答道:“犹如喷泉。”
尾声
代孕固然颠覆了我们对何为自然生育、何为父母的认知,但脱离具体现实与历史情景来探讨这些问题是远不足够的。代孕在很大程度上被割裂于生育史之外,给人造成这种新技术横空出世、与过往没有任何瓜葛的错觉。“典妻”陋习、国家仇恨、苦难叙事等等,代孕问题背后有太多我们隐而不谈的脓疮,因而我们也无法真正理解在年轻人生育愿望降低、育儿成本大幅提升的当下,代孕为什么一边被口诛笔伐,一边还有大量尚不能满足的需求。刘碧秋曾经用小品《超生游击队》里的一段话来指认中国人生育观的特质:“我罚得起我就罚,罚不起我跑。我们的原则是:他进我退,他退我追,他驻我扰,他疲我生。我跟你说,我就不信,按这原则就保不住儿子!”这个1990年的小品很可能被今人嘲为生育观落后的典型,但它也的的确确包裹了计划生育时代的巨大哀痛,在今天,我们的生育观真的走出了传宗接代的藩篱、卸下了这份哀痛吗?
 简体中文
简体中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