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的发展能否解决伦理、美学的问题?过去几千年间,人文没有讲清楚的问题,科学能不能提供终极方案?科幻作家刘慈欣与哲学家江晓原曾经就这些问题有过一段对话。刘慈欣认为,科学和技术能够解决人类的一切问题,现在还没有全部解决,是因为科学的发展不够充分。当江晓原质疑说,科学能否解决人生目的的问题时,刘慈欣给出了一个颇让人吃惊的回答:“科学可能无法回答人生目的的问题,但我们可以通过科学来取消这个问题。”
在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周濂看来,这是他“有限阅读”中见过的“最极端的科学主义”:它不但要为世间所有的疑问提供答案,还要通过修剪问题的方式来确保其稳定性和唯一性。日前,周濂与哲学家陈嘉映在“Naive理想国”咖啡馆围绕“科学主义与科学精神”进行了一次“互为脚注”式的对谈。
他们从伽利略对纯粹客观世界的发现谈起,聊到了科学研究思路的特质、人文与科学的区别。在科学狂飙突进的今天,人们要么采取科学主义的态度,认为科学可以取代人文,回答一切,要么希望两者可以井水不犯河水。针对当前的困境,周濂提出了自己对打破隔阂的“第三种文化”的构想,而陈嘉映则显得不那么乐观。但毫无疑问,陈周二人都不赞成科学主义对人生目的等问题的统一式回答,“问题是坐落在每个人具体的生活语境中的,每个人都赋予问题以不同的答案。”科学精神指的是承认科学确立的事实和发现的真理,并接受其对严肃思辨的制约,而不是用科学压倒、甚至取消一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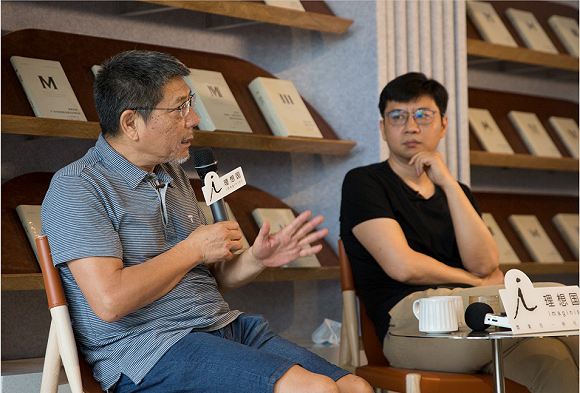
陈嘉映(左)与周濂在活动现场 来源:理想国
研究科学不等于放弃人文,当代人的困境在于丢失了科学以外的精神
科学作为一种思考方式,其独特性在哪里?陈嘉映从伽利略所说的“第一类性质”与“第二类性质”出发,梳理了近代科学与人文的不同。
作为近代科学的先导者,伽利略将事物的性质分成了两大类。第一类性质即客观的性质,例如杯子的形状、体积、材质等,它不但对人是原则性的,相对于其他事物来说,这种性质也不会有任何改变;而第二类性质却与主观有所关联——它不但是人与人之间主观判断的差异性,还强调人类群体与其他事物之间的差异性,例如大部分人类对颜色的认知没有争议,但对不怎么依赖视觉的狗来说,世界本是无所谓颜色的。
伽利略认为,自柏拉图以来,哲学中的经典问题已代代相争了两千年,后人的见解却不见得比前人高明。这是因为他们在忙着琢磨万物的性质及其关联之前,没有先对性质进行区分,抓住“世界的本质”——第一类性质。在他看来,哲学(当时科学还没有从哲学中分立出来,伽利略等人即自称“自然哲学家”)要想向前发展,首先得把两类性质分清楚,而后再集中研究第一类性质。有关这类性质的真理不会因人类发生改变,随着时间的推移,人类便能依靠可积累的真理认知把哲学带出原地踏步的窘境。
除了区分两类性质,伽利略还定义了何为“物我相关”的陈述,何为“物物相关”的陈述。当我们用“冷热”这样“物我相关”的语言来描述天气时,常常陷入主观式的争论;但如果我们说“今天是37摄氏度”,争议便不存在了——物物相关的陈述让争执不休的人们在同一个层面上达成共识,推进讨论。“我们采取物物相关的陈述,采取量化的语言、数学的语言,便可以对第一性质做披荆斩棘的推进。”周濂说道。
可以说,伽利略所做的两个“区分”是科学研究思路及其精神的核心。然而,人类能够满足于对第一性质的研究,而不关心美丑善恶、是非正义的问题吗?陈嘉映特别强调,伽利略发现了一个纯粹客观的世界,但他不是科学主义者。“伽利略只是说,新的实验哲学家,也就是后来的科学家,要想取得进步,就必须集中于对第一类性质的研究。但他并没有说而且他也不认为,人类就应该满足于研究第一类性质的生活。”
“牛顿沿着伽利略的路在走,但他也不是一个科学主义者。在人生的后几十年,他没有研究科学,而是在研究圣经,这和牛顿作为科学家的光辉形象有点不合,但牛顿的两个形象不是互相矛盾的。对牛顿来说,他要弄清楚世界的结构,是因为他相信上帝绝对不会糊里糊涂地造出一个世界来。上帝是充分理性,他一定是根据一个非常理性的图景来创造世界。研究物理学,是为了更好的信仰上帝。” 陈嘉映指出,对牛顿和伽利略而言,无论再怎么研究第一类性质,它也只是整体生活中的“一小块”,这两位科学革命的先导者与集大成者的背后有“更大的东西”。“现在科学主义与人文有这么多冲突,最主要的原因在于现代人已经丢失了这块‘背后的东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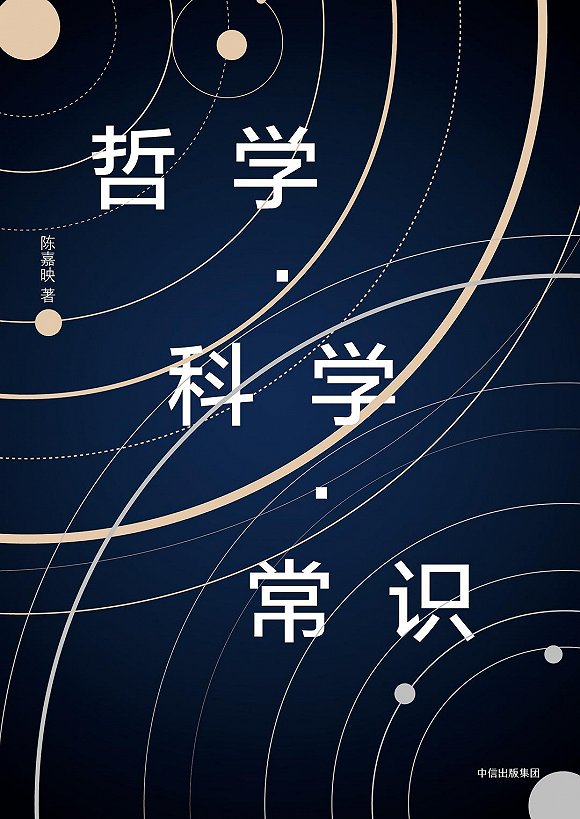
陈嘉映在这本《哲学·科学·常识》中探讨了科学与哲学之间幽微复杂的关系。
《哲学·科学·常识》
陈嘉映 著
新思文化|中信出版集团 2018-3
科学主义的问题在于用“how”来回答“why”
如果我们采用第一类性质与第二类性质的视角来追问哲学为何“原地踏步”,所得的答案大概与启蒙运动时期的哲学家们一致:科学突飞猛进,哲学停滞不前,是由于我们没有用科学的方法来研究何为正义,何为良善生活、人生目的、美丑善恶。启蒙运动之后,就有一批哲学家尝试用科学的方法来研究第二类性质的问题。在周濂看来,这种试图用科学来解决一切非科学领域问题的做法带有很强的还原论色彩。
还原论对问题的追溯永远是朝下的。比如我们在谈论经典的身心问题、自由意志问题时,一些科学家就想从粒子的层面去寻找答案,这就好比用肾上腺素解释革命,用多巴胺阐释爱情。“还原主义也许是成立的,但它是否能原路返回呢?”周濂认为,还原论在逆向复原建构的过程中,必然有所丢失。科学主义者可以用还原论将第二类性质的问题化归到第一类性质中去,却无法原路返回。
面对这样的质疑,一些科学主义者可能会辩护说,现在的科学水平不能很好地去建构,也不能很好地去描述细节,是因为科学发展还不够到位,我们对事实的认识还不够充分。对此,陈嘉映回应道,还原论实际上还是在用“how”来回答“why”的问题。“为什么巴勒斯坦的小孩看到以色列的军队会朝他们扔石子、扔自制炸弹?为什么马克龙在黎巴嫩则受到民众欢迎?我们当然可以去查不同人群的神经系统与体液循环,但这只能告诉我们这些反应是如何做出的,而不是为什么做出。最初的好奇心没有得到解答,甚至可以说没有被问。”
跨越科学与人文的“第三种文化”是否可行?
英国小说家C·P·斯诺在《两种文化》中描述了人文与科学在现代社会的分道扬镳。这两种文化互不搭理,也不明白对方在说什么。人文文化代表者不懂相对论,科学文化的代表者从不阅读莎士比亚。今天,科学高歌猛进,一些人充满信心地断言,科学迟早取代人文,另一些人则主张相安无事的态度,让科学的归科学,人文的归人文。在这两种主流观点之外,周濂提出了“第三种文化”的构想。
“所谓第三种文化,即是借助现代科学,更深入地把握人文社科所关心的主题,与此同时,人文社科又能够保持自己相对的独立性,不完全被科学主义所吞噬,还原到粒子层面。”周濂说道。

《两种文化》
[英]C·P·斯诺 著 陈克艰等 译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3-1
在谈论“第三种文化”的可能性时,周濂引用了美国语言学家史蒂芬·平克的两句话。“平克说,科学告诉我们,世界是可以理解的。这句话看似卑之无甚高论,但仔细琢磨它的意思,实际上是在说,科学不是信口开河的,不是用图像的、寓言的或者神话的方式去理解世界,它有特定的方式,人类能用这种崭新的眼光来打量世界,本身就是极为诗意的浪漫。平克另一句话是说,要让世界告诉我们,我们关于它的各种看法是否正确。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从古至今许多关于宇宙和人类自我的理解,都被颠覆掉了。科学虽然不能取代人文的理想,但它可以限制我们的各种理想。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对‘第三种文化’有所期待。”
与之相反,陈嘉映对“第三种文化”的看法较为消极。他的这种态度可以从其对还原论的批判中看出端倪:“你沿着‘how’的路走,不会回到‘why’,你只不过会在路上慢慢遗忘掉后者而已。”一旦走上向下追溯的科学之路,就永远不会回来。同时,陈嘉映也怀疑科学的勃兴到底对人文理想提出了多少新的限制。在他看来,即使没有科学,好的哲学也不是用空想的方式来思考的。
在提问环节,有观众提问,如果科学是在解释“how”的问题,那么人文真的能回答好“why”吗?周濂说:“好的哲学提供较好的答案,坏的就提供坏一点的,但问题在于,哪怕提供了较好的答案,它也不是所有人都接受的答案。”“人文真的能回答好why吗”这种提问方式本身就暗含了寻求唯一正确答案的倾向,而这正是科学主义者的雄心所在。“这个问法本身就错了,因为问题是坐落在每个人具体的生活语境中的,每个人都赋予问题以不同的答案,这是人文想要保持的多样性和差异性,它和科学那种乘风破浪、一往无前的思路是极为不同的。”
 简体中文
简体中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