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4月7日,现居瑞士洛桑的“新浪潮”名导让-吕克·戈达尔(Jean-Luc Godard)出现在Instagram直播平台上,与瑞士ECAL艺术与设计大学电影系主任里奥内尔·拜尔(Lionel Baier)对谈了100分钟。一同参与的,还有近年来经常与戈达尔合作的女摄影师、制片人法布里丝·阿拉诺(Fabrice Aragno)。画面中,89岁的戈达尔看上去精神矍铄。两位年轻人来到了他的家里,全程佩戴口罩,他则跟他们开玩笑说“你们俩看上去就像是詹姆斯·恩索尔(James Ensor)油画里面走出来的人”。整个直播,吸引了全世界近四千名网友的关注。以戈达尔在电影史上的江湖地位来说,这个人数,真不能说是很多。尤其对比网红直播卖货时的关注人数,更可以说是有些寒酸了,想到他拍过的《精疲力尽》、《狂人皮尔洛》、《蔑视》等诸多经典,甚至都要让人觉得有些心酸了。
当然,因为现场并无同声传译或英语字幕的关系,法语问答的语言壁垒,多少阻碍了世界各地戈达尔影迷的加入。不过,在遥远的中国,戈达尔做直播的消息,迅速在各种朋友圈中发酵,据说当晚近四千在线观众中,有至少三分之一来自国内。而在文青扎堆的“豆瓣”上,戈达尔的名下甚至也在第一时间出现了《戈达尔直播实录:新冠疫情时期的影像》这么一个新建电影条目。

虽说谈话的主题是新冠疫情,但戈达尔并非医学专家,他也只能从自己的老本行——电影的角度来讲述一二。正如许多人早已指出的,他也将新冠肺炎病毒的传播,与信息的传播做起了比较,认为“病毒也是人际交流的一种方式,需要有接收者。就像我们传递信息的时候,哪怕是在社交网络上,光是传出去还不够,也许多对方接收你的信息”。
除了信息之外,语言也是戈达尔十分感兴趣的一个话题,从早年作品《电影史》到近期的《再见语言》,语言本身都是其关键主题。因此,当里奥内尔·拜尔向他询问如何看待这个特殊时期,电视新闻记者都只能困在家里做报道的时候,戈达尔的回答则是:其实不论在哪里做新闻,他始终觉得新闻主持口中说出来的话语,都是不可避免经过了扭曲变形之后的信息。因为首先这都是别人写好的新闻稿,其次这些文字本身——按照戈达尔自己的定义来说——也不能算是语言(language),只是话语(speech),只是对于语言的糟糕的复制品。看过《再见语言》等作品的人或许都了解,对戈达尔来说,语言与影像(image)关系密切,而这种出自于政客、新闻记者的话语中,却欠缺了足够的影像,因此常让这位电影大师不屑一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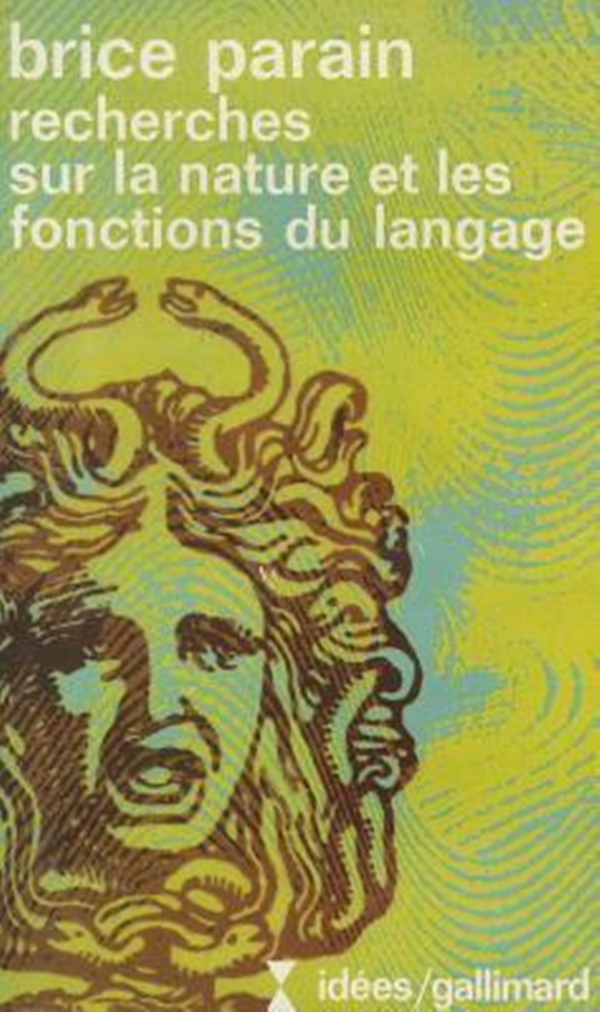
戈达尔说,自己十五岁时因为读了《语言性质与功能研究》一书,有很长时间不想说话。
关于语言,戈达尔在直播时还透露了一件有趣的往事:“大约十五岁的时候,我有那么一两年的时间,一直都没再说话,把家里人给吓坏了。”据他解释,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当时读了法国哲学家布里斯·巴兰(Brice Parain)的《语言性质与功能研究》(Recherches sur la nature et les fonctions du langage)一书。有趣的是,他1962年拍摄的《赖活》一片中,特意请到巴兰客串登场,在片中饰演一位哲学家。

戈达尔拍摄《赖活》时,找来哲学家布里斯·巴兰客串演出。
在戈达尔看来,正在研究新冠病毒的这些科学家,其实和电影导演也很相似,都是通过镜头在看问题,区别仅在于一个是电影镜头,另一个则是显微镜的镜头。不过,相比科学家,导演还有一个优势。“科学家最终还是会落入话语的陷阱之中,还是会陷在一堆文字和数字之中,而我们拍电影的,相对来说就可以更自由一些,电影成了我们对抗文字的抗生素。”
他还谈到了自己近期一些作品中将电影片段、文学章节和绘画作品熔于一炉的拼贴风格,戈达尔引用了法国电影前辈布列松(Robert Bresson)的话:“希望能将本身没有关联的东西给放在一起。”他诚恳地向正在看直播的影迷推荐布列松的那册《电影书写札记》,称之为“我们时代的电影《圣经》”。
被问及是否怀念“新浪潮”时期自己的那些战友时,戈达尔顿时来了精神。他回答说,自己非常想念他们:“因为我们当年的关系很密切,总是聊个不停。不过,我和特吕弗、里维特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一般也不太谈各自的生活,都是谈电影,可能只有和侯麦谈生活谈得多一些!我们当时都很爱去看电影,但每个人的方式又各有不同。里维特可以一整个下午都坐在电影院里,同一部电影反反复复看上四遍。我则是不同的电影,可以一天看四五部,但都不一定完整看,这也是一种观影方式。但不管怎么说,我们这些人都是一个小团体——甚至还可以再算上夏布洛尔。”
(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简体中文
简体中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