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是避风港。”这句话在今天听来无比真实。只有回到家中,我们才能自由地展现疲惫和沮丧。人总需要一个可供蜷缩的角落,不管是一套属于自己的三居室,还是一个租来的小房间,只要我们寄寓其中,就可以称之为“家”。
有“家”就可以免于流离失所、受人侮辱吗?不一定。在这个城市改建频繁、租房问题频发的时代,家的买卖与租赁充满不确定性,安全与尊严剧烈摇摆,似乎随时可以被剥夺。
房子和家之间的关系如何?是否只有通过占有房产,我们才可以成为完整的人?法国哲学家加斯东·巴什拉与亨利·列斐伏尔都思索过屋宅空间问题,一个看见了诗意,一个看见了政治性的剥削压迫。这份书单从巴什拉开始,先走进宁静的乡间,同哲学家一起畅想人、家宅同宇宙的关系,再跟卡尔维诺笔下的马可瓦尔多走进方格垒砌的城市丛林,考察现代都市居民对居所的不断逃离。如果说马可瓦尔多的故事没能回答人为什么逃离之后还要返回,小说《书店》主人公弗洛伦斯的经历则填补了这一空白——居所是我们在荒漠中唯一可以支配的空间,然而,弗洛伦斯被特权驱逐的遭遇暴露了严峻的现实:合法拥有的房产,随时可以被合法褫夺,人有两种身份,根除者与被根除者,前者统治着后者。驱逐大量存在,美国人类学家马修·德斯蒙德在《扫地出门》中指出,驱逐,只会让贫穷的人更贫穷,富裕的人更富裕,因为这是把部分人的贫穷转化为另一部分人财富的关键手段。恩格斯在《论住宅问题》里讲道:“在这样的社会中,住宅缺乏现象并不是偶然事件,它是一种制度。”不论我们多努力地想沿着巴什拉的小径走下去,最后都不可避免而绝望地发现,回到恩格斯、列斐伏尔等人所讨论的空间政治学,几乎是当下思索家屋者的宿命。毕竟,我们只是凡人,在连吃饭睡觉都岌岌可危的时候,有谁能诗意地思考呢?
《空间的诗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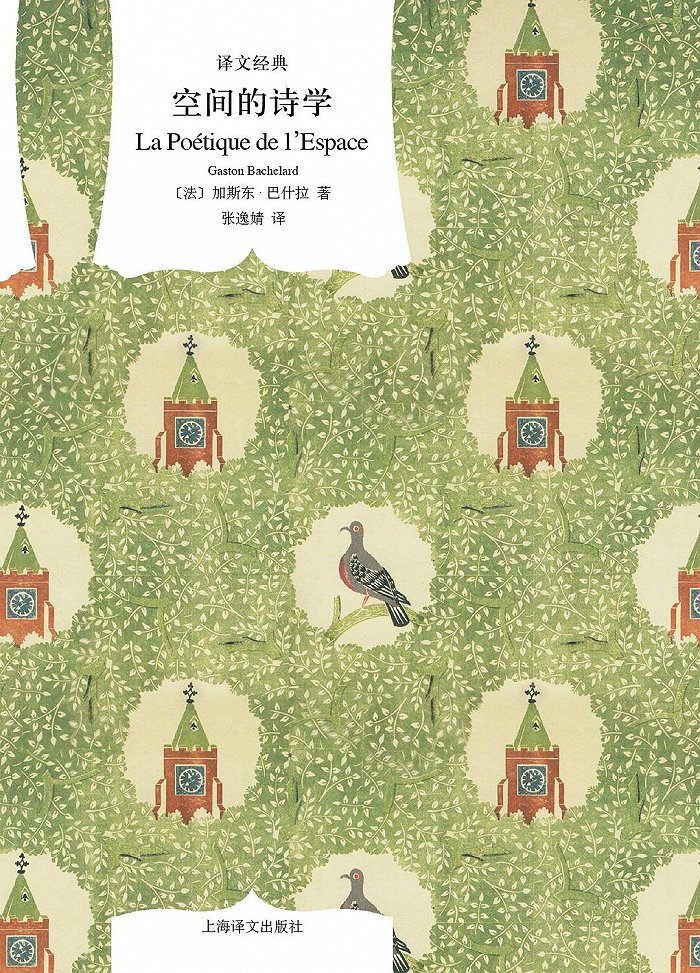
[法] 加斯东·巴什拉 著 张逸婧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3-7
走在寒风凛冽的晚上,看见别人家窗户背后的灯光,你会想起什么?里尔克曾同两个伙伴走在路上,望见远方的地平线上有座小屋,四下是漆黑的田野沼泽,屋里透出光亮。“尽管我们一个紧靠着另一个,但三个人仍然是孤立的,因为我们都是第一次看见黑夜。”里尔克的这句话出人意表。行路人的孤独感是可预见的,但它通常被解读为漂泊者对居家安稳的艳羡,对自身状况的叹怜,窗户背后的灯火像是屋内世界对屋外人的排斥、轻视与责备。里尔克所体验的孤独则不然,这静谧的孤独洋溢着喜悦,因为诗人于“第一次看见黑夜”——灯火没有照亮户外,却唤醒了诗人体内无数个交叠的时空,让他重新认识广阔的黑夜、无尽的宇宙。
法国哲学家加斯东·巴什拉在《空间的诗学》一书中提出,家宅是人类最初的宇宙,它不仅是肉身的居所,还是意识的栖居地,“把人的思想、回忆和梦融合在一起。”不论是过着相对安定的生活,还是成为城市游牧人,我们的一生都在不断回溯最初蜷缩过的那个角落,让生命意义得以阐释。巴什拉认为,唯有作为空间的家宅才能“悬置”飞逝的时间,将记忆和经验放进千万个小抽屉。当我们走进新的空间时,家宅所贮藏的时间碎片开始释放活力,把过去、现在与未来、人与宇宙联系在一起。
“家宅总是排除偶然性,增强连续性,没有家宅,人就成了流离失所的存在。家宅在自然的风暴和人生的风暴中保卫着人……在我们的梦想中,家宅总是一个巨大的摇篮。”流离失所即无处安身,但巴什拉着意的不只是没地方吃饭睡觉、遮风避雨,他对家宅的思考更为抽象:“偶然性”的威胁不直接来自迁徙流动,而是意义的断裂;家宅是个体认识自身同他者、乃至宇宙关系的钥匙,没有家宅,时间又开始了无情的流逝,失去记忆庇护所的我们不再有隐秘而广阔的内心空间,一切都在变得狭小单调,窗后的灯火难以唤起里尔克式的孤独感。
巴什拉在书中反复强调,人不是如形而上学家所说的那样“被抛于世界”,在此之前,“人已经被放置于家宅的摇篮之中。”家宅被连根拔起,最可怕的不是颠沛流离,而是失去独特的自我、幻想的摇篮,被剥夺做梦权利的人变成了丧家犬一般的存在。
《马可瓦尔多》

[意] 伊塔洛·卡尔维诺 著 马小漠 译
译林出版社 2020-1
巴什拉笔下的家宅充满诗意,读来却与我们的生活相隔万里,因为他所讲的家宅必须要有阁楼和地窖,在垂直的方向上构成完整的梦境,无怪乎对他而言家宅总是一个幸福的空间,而城市居民所住的“层层叠叠的盒子”不在讨论范围之内。
抛开巴什拉定义家宅的严苛条件,现代都市人的居所同样影响着他们内心的认知结构。马克瓦尔多和自己的老婆、四个孩子挤在一间半地下室生活。这名蓝领工人的眼睛从未适应过都市生活,标志牌、红绿灯、橱窗都留不住他的目光,而一片枯叶、一只瓢虫、一个蛀虫洞,自然的每一个细节都逃不过他的双眼。对居住条件糟糕的都市人来说,居所不过是水泥丛林的一个触角,迈入家门,如同走进一场相似的不幸。半地下室无数次地把马可瓦尔多推出门去游荡——街头尚有自然可以寻觅,屋内的逼仄、嘈杂却比城市还要城市。
在一个闷热潮湿的夏日夜晚,马克瓦尔多决定到公园的长椅上去睡觉。他每天早晨上班都会经过这个公园,已经幻想过很多次躺在绿荫下,伴着自然的黑暗入睡,在晨间的阳光和鸟啼中醒来,不必忍耐老婆的鼾声、孩子们的哭闹。然而,半夜跑到公园后,马克瓦尔多没有得到想象中的宁静和清爽,反而和公园里吵架的情侣、闪烁的灯光、施工声以及垃圾恶臭搏斗了一夜。他的睡眠变得比在家里还要脆弱,只要认定了什么事情可能会影响到他,他就再也睡不着,到了后半夜,就连“真正的安静”也变成了一种搅扰,他需要比安静“更柔软的声响背景”,于是他偷偷打开喷泉,在人造的声响中入睡。噪声已经无法抵达他的睡眠,只有垃圾堆的恶臭潜入梦境,幻化为烂掉的死老鼠,躺在一家人的饭碗里。他拔下毛茛属植物,企图用它遮盖臭味,但最后真正让马可瓦尔多入睡的,恐怕是与无处不在的城市彻夜纠缠所产生的疲惫。
对马可瓦尔多而言,公寓居所同城市一样,叫人难以忍受又无可逃避。但它不像巴什拉认为的那么无聊,完全消灭了居住者的内心生活,至少马可瓦尔多不断在失败与成功的轮替中寻找与自然的联结。这种乐趣不光在街头的一片绿地中得以实现,居所在适当的情景中也得以把不利转化为有利:马克瓦尔多后来和家人们搬到了同幢公寓的阁楼居住,每逢下雨,天花板的滴水声就“让人不寒而栗,好像是风湿病发作的征兆”,但有一次,他听着雨声却有说不出的欣喜——他在养一盆本来快要死了的绿色植物,雨越是大,那盆植物越是以令人惊奇的速度疯长,繁茂的绿叶给他带来无尽的快乐。
巴什拉将家宅内外的世界明确区分开来,人拥有了与自然混为一体的家宅后再去探寻屋外,和宇宙的关系也显得那么融洽。城市取消了居所内外的分别,在街头挣扎的人,在家也要挣扎。屋内不是一个自足的世界,源源不断地为我们提供勇气,相反,我们必须日复一日地埋头行走,才能找到足以支撑我们返回荒漠的绿意。
《书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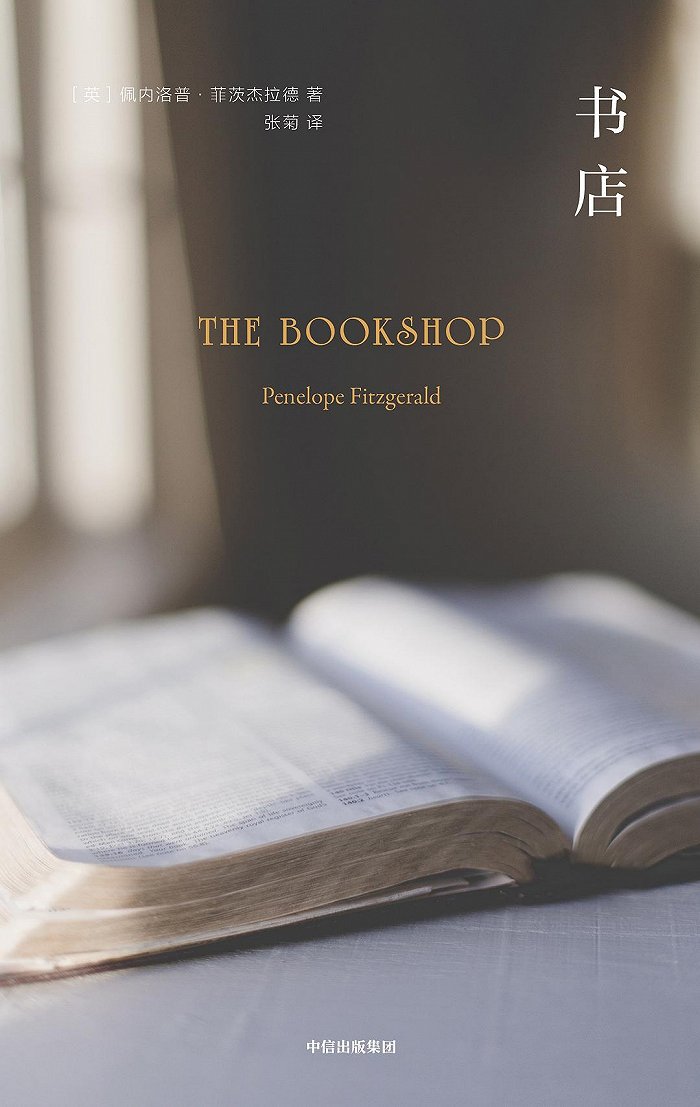
[英] 佩内洛普·菲兹杰拉德 著 张菊 译
中信出版集团 2019-5
既然现代性的居所这么折磨人,我们为什么还要回去?简单地说,因为我们还需要一个空间来完成吃喝拉撒睡的基本需求。再提高一些,人际关系、人的追求也需要有空间来承载和实践。在一个缺乏公园、小商店、餐馆茶馆等空间的城市,人们在街上疾步走过,鲜有机会停下来交流,即使住在同一个社区的人,也很少有交集。外面的世界比里面更荒芜,居所就成了我们最后的阵地。不管是组织亲朋聚会,还是开餐馆、办沙龙,一个属于私人的空间为丰富个体与社区的生活提供了基础。
弗洛伦斯·格林为了开书店,在哈德堡盘下了一栋老屋。老屋是五百年前用泥土、稻草、树枝和橡木横梁建造的,前面有个很大的房间,后面是厨房,楼上有个斜顶的卧室,旁边还有一个散发着海腥味的牡蛎棚。在弗洛伦斯搬进来前,老屋荒置已久。哈德堡这个小地方没什么人做生意,许多人对弗洛伦斯开书店的想法不以为意,但书店的经营情况比大家想的要好。老屋书店很快就成了镇上居民常去的地方,就连德高望重、深居简出的布伦迪西先生也对书店经营颇为关注,还第一个登记为租书处成员。这里地处偏远,只有两个人因为工作的关系每周去伦敦,现在,伦敦布兰普顿书店的漂亮面包车频频出现在哈德堡街头,为小镇增添了活力。
老屋书店的经营不说蒸蒸日上,也足以维系自身的运营。然而,小镇上颇有权势的加马特夫人却视之为眼中钉,她本来想把老屋建成一个“艺术中心”,好和奥尔德堡竞争。加马特夫人的侄子是西萨福克郡的议员,他提出的一项房屋法案通过后,弗洛伦斯被迫从老屋中搬出,没有得到一分钱的赔偿。
佩内洛普·菲兹杰拉德在小说中写道:“人……以根除者和被根除者来划分,其中前者,始终统治着后者。”哈德堡的根除者,不但霸占空间,还要霸有文化。加马特夫人是镇上最有“品位”的人,艺术只能由她来代表,弗洛伦斯的书店生意算不上有益于社区精神文化的工作;在BBC工作的米洛·诺斯本应该是文化教养的代表,但他自私冷漠,用一种精于算计、毫无原则的教养为自己谋取好处。除了布伦迪希先生外,弗洛伦斯的伙伴主要来自工人阶层,例如在书店打工的克里斯蒂娜,她厌恶书籍,却勤劳、聪明、正派。布伦迪西先生谴责完加马特夫人倒在大街上死去,哈德堡正直、善良与文化、上流阶层的最后联系就此中断,只剩下根除者与被根除者。
原以为属于自己的空间、最后的营地,轻而易举就被合法褫夺。那条法案授权给地方议会强制购买任何建于500年前、没有用于居住的建筑,可是弗洛伦斯不还住在那儿吗?法案在对居住和赔偿条件的解释上取得了一致的灵活性,即服务于根除者的利益。至于弗洛伦斯这个人和她所做的事,被认定为是无关紧要的。在小说的最后,弗洛伦斯坐在离开的火车上,“羞愧地低着头”,她感到无地自容,“因为她生活了将近十年之久的小镇,并不需要一家书店。”剥夺一个人的房屋等同于宣告他没有价值,丧家之犬的最大苦楚不是流浪,而是不被需要。
《扫地出门:美国城市的贫穷与暴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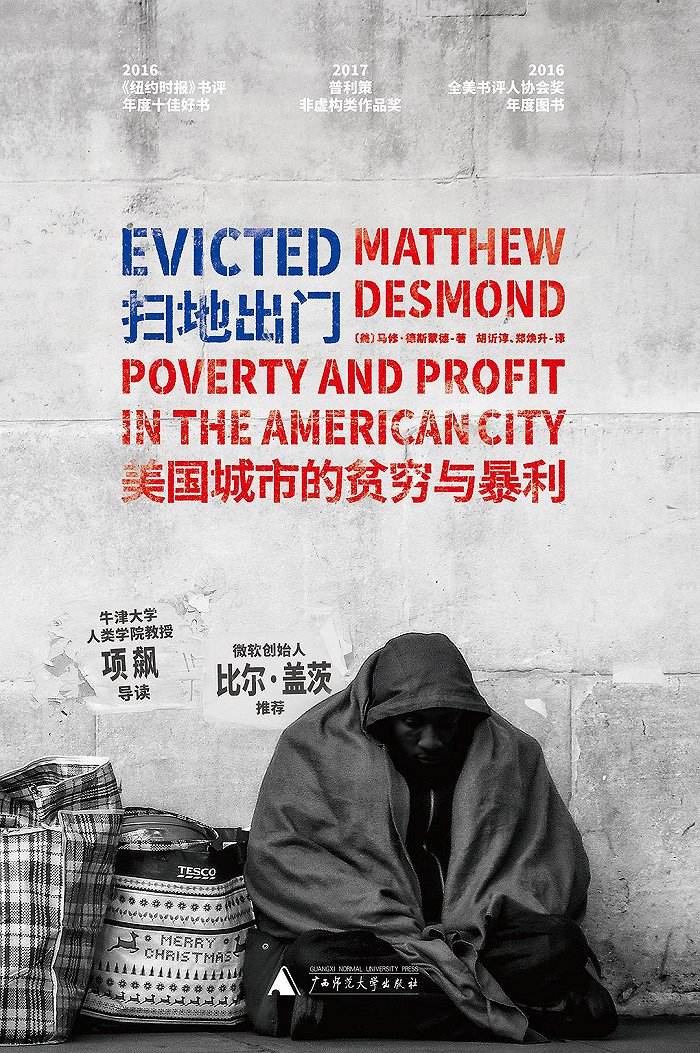
[美] 马修·德斯蒙德 著 胡䜣谆 郑焕升 译
理想国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7
《书店》里的弗洛伦斯遭到驱逐,或许可以说是一场私人恩怨,但在现实中,驱逐更多是系统性的。研究显示,失业、失学往往紧随驱逐而来,疲于应对住房问题的人很难再有多余精力投入到职场和学业生活。被驱逐的人不光会失去有形的房产、衣物、家具、书籍,还会失去他们建设家园所付出的时间,同时,频繁的流动也破坏了邻里间的信任感。
通常,驱逐被看作对各方都没好处的事,但美国人类学家马修·德斯蒙德在密尔沃基进行了一年多的田野调查后发现,驱逐其实是一桩暴利买卖,能够将“一些人的贫困转化成另一些人的超额利润”。黑人房东谢伦娜是这本非虚构著作的主要人物之一,她在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的时候买下了密尔沃基贫民区的几处房产,按理说这些房子没有升值空间,但谢伦娜看中的不是未来,而是当下。她深谙穷人的生存法则,被扫地出门的人大多没有钱买房,被驱逐记录又使他们无法入住公共住房,只好选择性价比极差的贫民窟出租房,就算价格再不合理,他们也只能选择忍受,不断突破自己生活的底线,节衣缩食,把房租凑齐。
“贫民窟是个好地方。那儿是我的金母鸡。”谢伦娜对德斯蒙德说道。在畸形的房地产业中,贫穷不光是天价房产的结果,还是可以用来榨取的资源,唯有占有住宅,才可能免于被驱逐的命运,摆脱贫穷,获得尊严、安全、自我与意义,房产证成了丛林世界里的盔甲。人类学家项飙在此书的导读中指出,这种“家天堂”意识实际上异化了人与生俱来的基本权利,每个人都应当拥有和享受的生存空间成了需要拼命占有的东西,而一旦占有房屋的逻辑成为主流,排斥和驱逐就不会消失,因为驱逐是“占有的前提”,也是“提升占有物价值的手段”。正如项飙所言,占有和竞争形成了恶性循环,“为了买房安家,我们承受更多的工作折磨,工作折磨又让家居这个避风港显得愈加宝贵。于是,人之为人的基本需求(住所)成了我们全力拼搏的目标,实现人之为人的基本手段(工作、学习、在街上和人相遇交流)成了折磨和负担。”
德斯蒙德尖锐地指出,人穷,不代表不能过稳定的生活。类似“买不上房是因为你不够努力”这种论调我们已经听得太多,但在房价奇高的今天,有多少年轻人能在没有父母帮补的情况下买上房呢?退一万步,假设人人都终将成为“房奴”,在拿到房以前就不配拥有安居之地吗?穷,不是原罪。
《空间与政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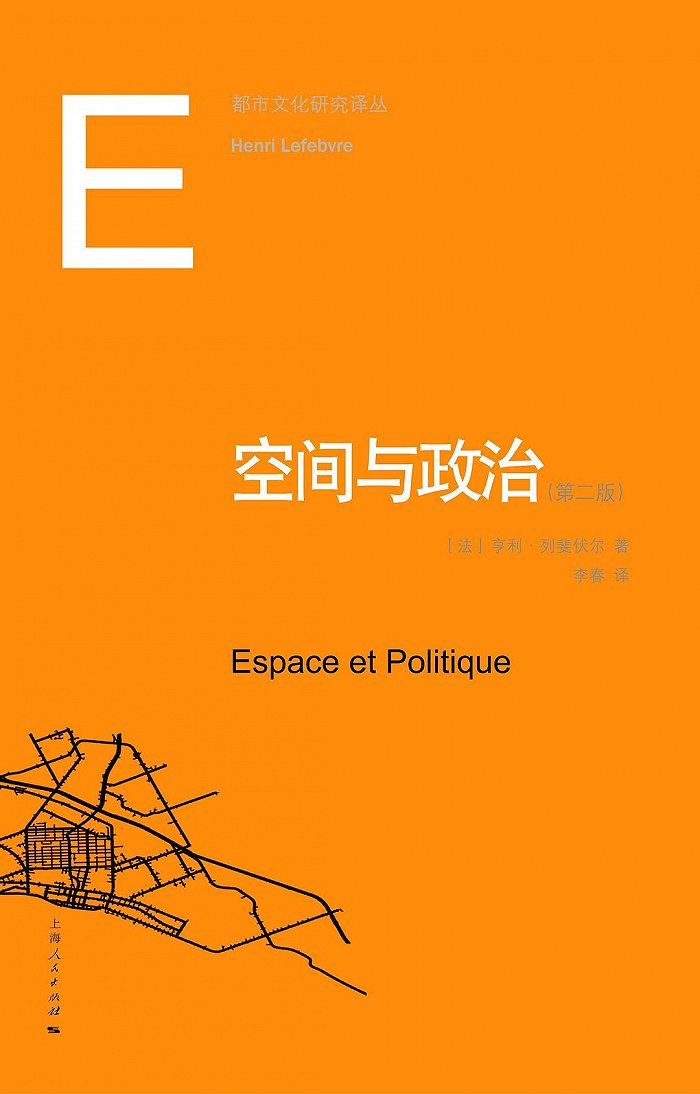
[法] 亨利·列斐伏尔 著 李春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5-8
回过头来再看巴什拉谈论家宅的方式,那种诗意多么珍贵而奢侈。项飙认为,家之所以重要,无非是因为要有地方吃饭喝水,把家提到“人性、意义、精神、民主的层次”,在占有与竞争的恶循环下,是为家所遭遇的“双重异化”添柴加火。的确,无论是马可瓦尔多这样的现代城市居民,还是古代的游牧民族,都可以对巴什拉的诗意家宅提出异议和补充;项飙在上世纪90年代前住分配宿舍、过集体主义生活的经历也可以证明,成为完整的人不必要有一栋在垂直方向上完整的家宅,更不需要一张房产证。但这并不是说,家屋同“人性、意义、精神”没有关联,我们今天的问题很可能不是诗意化的家屋为买房风潮煽风点火,而是面对严峻的现实,是否还有真正将家屋诗意化的可能。
巴什拉生于十九世纪末的法国,哲学家亨利·列斐伏尔比他晚出生十几年,他观看空间的方式永远是政治性的。在《空间与政治》一书中,列斐伏尔指出,在当前的资本制度下,政治经济学是围绕空间来展开的,空间被设计为稀缺的商品,所谓的“不动产”成了“动产”——只有流通起来,空间才会化作财富。巴什拉把空间视作记忆、时间的悬置定格,它涵容了个体与宇宙的关系,但列斐伏尔的空间是资本秩序的体现(谁被分配在中间,谁被驱逐向边缘),同时也是资本权力用以完成和巩固自身的工具,除了城市住房,郊野的山壑、海岛等等无一能从资本与权力的空间规划中逃离。一个打工人,只有放弃足够多的如厕空间,才能兑换黄金沙滩的一次性体验券。
在一个有产者还想占有更多房产,无产者随时可能流落街头的年代,很难再有巴什拉那样的思考方式。毕竟,一旦你开始严肃思索住房问题,要么就会陷入无家可归的恐惧,要么就会为自己有房而羞愧难当。
 简体中文
简体中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