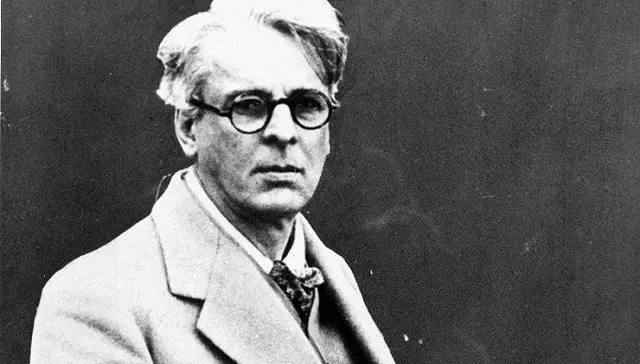今天是爱尔兰诗人叶芝的诞辰纪念日。关于叶芝,人们印象最深的还是那首他为心仪女演员茅德·冈所写的情诗《当你老了》。1893年叶芝创作这首诗时,两人都正值青春年华,但叶芝却明白红颜易逝,真正的感情应当经受住岁月的磨砺。时至今日,《当你老了》仍是许多读者心中爱情诗的典范,然而,这首诗的广为流传也在某种程度上掩盖了叶芝其他抒情诗的光芒,以及在爱情之外更值得关注的成就。
19世纪末至20世纪20年代,爱尔兰正经历人民民族意识普遍高涨的时期。当时,社会各阶层纷纷要求摆脱英国的殖民统治,实行自治,与政治上的民族独立运动相呼应,爱国的作家们创作了大批表现爱尔兰人民生活、反映民族精神的作品,形成了一场蔚为壮观的文艺复兴运动。叶芝正是这场运动的领袖人物,他与格雷戈里夫人、约翰·辛格等人创立了“爱尔兰文学剧场”,并在此基础上创建了“艾比剧院”。叶芝的剧作《胡里痕的凯瑟琳》于1902年首演,以象征的手法指出英国人的殖民统治是造成爱尔兰贫穷、羸弱的根源,唤起了人民强烈的民族感,为爱尔兰民族戏剧的繁荣揭开了序幕。
在诗歌方面,叶芝继承英国浪漫主义的传统,以民族诗歌形式描写爱尔兰人民的生活。他的早期诗歌多取材于爱尔兰本土的传奇与民谣,热衷于以民谣体裁寻求某种复调或吟唱的叙事效果。韵律感强烈,充满柔美、神秘的梦幻色彩是他作品的特色。对他而言,放弃民谣就是放弃诗歌的口头传统,放弃他的民族身份与归宿。他曾在《致未来的爱尔兰》一诗中写道:
进入不惑之年后,叶芝在伊兹拉·庞德等人的影响下,创作风格更加趋近现代主义,但民谣仍在他的晚期作品中占据重要地位。他曾于1923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理由是“以其高度艺术化且洋溢着灵感的诗作表达了整个民族的灵魂”。在近日出版的针对叶芝的诗歌研究著作《我们隐秘的法则》中,美国诗歌评论家海伦·文德勒以科学家一般精确的诗歌细读法和批评实践原则分析了叶芝的诗歌形式。她认为,现代诗人中只有叶芝如此坚定,一生都在创作民谣。他最早的民谣作品深受英国诗人司各特、华兹华斯等人的影响,但很快就开始实验性地创建个人风格,并将爱尔兰的政治和历史融入其中。经出版社授权,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从书中选取相关篇目,以揭开叶芝与民谣之间的不解之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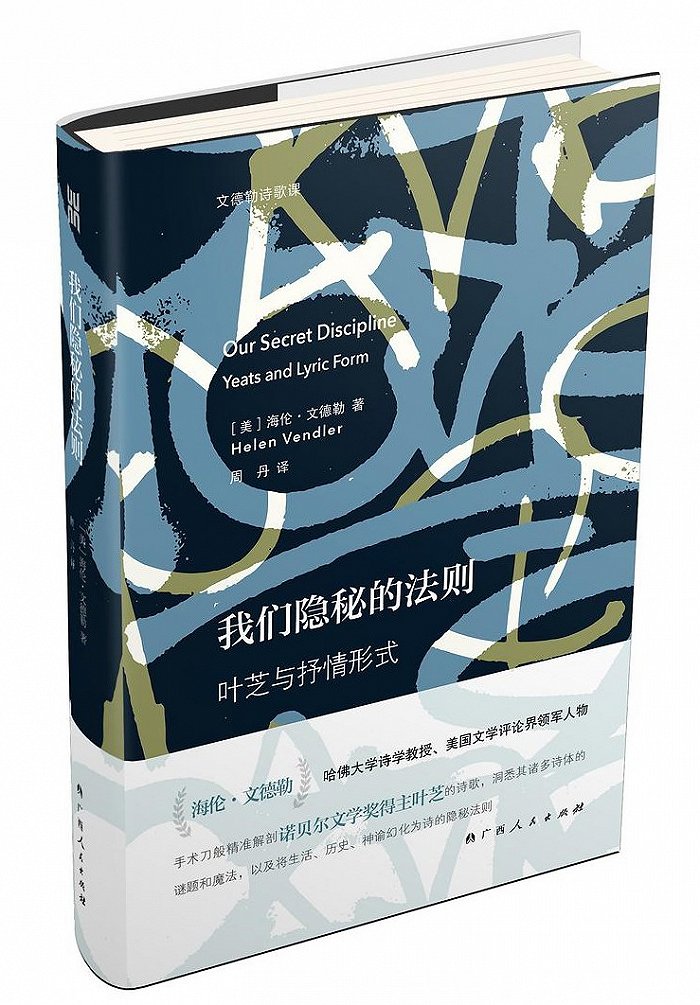
《我们隐秘的法则:叶芝与抒情形式》
[美]海伦· 文德勒 著 周丹 译
广西人民出版社 2021-04
从传统到实验:叶芝的民谣创作
文 |海伦·文德勒 译 |周丹
叶芝的民谣创作超过半个世纪。民谣在他创作早期(在他的民族建设时期)和后期(晚年追寻“原初”)都十分重要。叶芝一生都在钻研如何写作一首现代民谣这个无解的问题,因此,在他的创作生涯中,对民谣体裁的长期探寻与修改在他的事业中占据独特位置。它们启发叶芝进行执着而不懈的创作,其他任何形式都无法比拟。
与19世纪前辈诗人一样,从司各特和华兹华斯到济慈,叶芝拓展了民谣的范围,同时还保留许多民谣的传统特质(虽然也时不时打破常规),比如叙事情节、四行诗节(有时伴有叠句,有时延展至六行)、简单处理的手法、突出戏剧性时刻、运用对话、非个人化和以集体的声音进行表达。作为青年诗人,叶芝自然选择以常见的民谣诗节开始创作。后来,叶芝的民谣不再单以叙述为主,而是加入更多抒情、玄学主题,同时创造了多种民谣诗节的复杂变体。最后,他实验性地将抒情歌曲附着于民谣故事主体。
叶芝的作品经过推敲琢磨,而非仓促而为;他的作品并非典型的“街头民谣”,而是能与司各特和华兹华斯这些文学巨擘的民谣比肩的。
01作为爱尔兰民族之歌的民谣
在叶芝早期民谣中,《欧哈特神父谣曲》(1888)等部分作品以传统方式展开变化事件的叙事内容。但是《茉儿·梅吉谣曲》(1889)采用华兹华斯式主题——被抛弃的女人,强调说话者的情感而非故事情节。《茉儿·梅吉谣曲》展现了一个弃妇内心的心烦意乱。故事令人哀怜,她无意间闷死了自己的孩子,因此被丈夫扫地出门:
《茉儿·梅吉谣曲》沿袭了边疆民谣用词简练、叙事直白的优点。但是,叶芝早期的民谣内容仍属于华兹华斯民谣传统的一个分支——叶芝笔下的主人公绝大多数都生活拮据、疲于生计或者不再年轻。叶芝写作有关神父的民谣,比如神父吉利根和欧哈特,暗示他想吸引爱尔兰信奉天主教的读者,将他们囊括于他想创造的民族文学中,这个想法或许没有什么美学价值但却足够慷慨。叶芝早期的民谣仍基本处于民谣的范畴之内,并且看不出他在形式上的任何创新。
到1897年诗集《苇间风》,叶芝的民谣开始不同于前辈诗人的作品,神秘主义题材开始浸润他的作品。尽管《有福者》是以国王和隐士(爱尔兰语分别为Cumhal和Dathi)的对话展开,尽管这里的隐士(hermit)在基督教中寓意为“上帝的母亲”,但在诗尾,同样是这位隐士,他却建议国王,人醉酒后可能得到天启,从而能像玫瑰十字会成员一样窥见神秘的未来。原本普通格律的民谣诗节(4-3-4-3,abab)因能知晓未来的喜悦,其节拍竟如扬抑抑格般轻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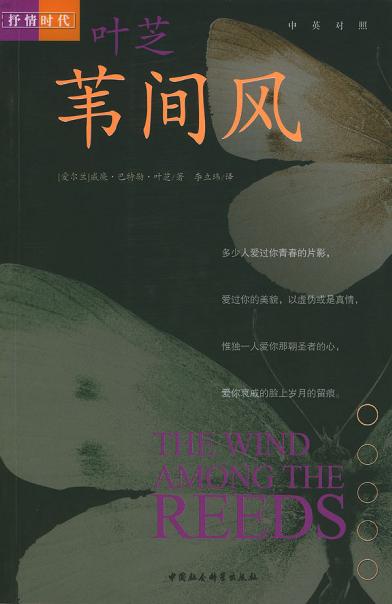
叶芝的诗集《苇间风》
数年之后,常见的民谣人物形象如茉儿·梅吉等在诗集《绿盔》(1910)中已不见踪影。民谣《他的梦》其说话者是一位舵手,谈吐得体,话里还有些神秘的象征。舵手略微调整民谣诗节的格律(abab)4-4-4-3,以便重述他的梦想。在梦里,他以一种特别的方式躺在船上,即“死亡”,这让岸上围观的人动容落泪:
这首民谣披着梦境的外衣,变成了一首象征主义作品,最大程度减少了叙事的内容。不过,由于说话者的声音来自人群的集体思想,因而篡夺了诗人给躺在甲板上的舵手命名的特权,这样一来,民谣匿名集体创作的特质得以保留。因此,叶芝将《他的梦》的抒情氛围适当地附着于民谣集体特质;不过这首诗里超现实的象征主义意象与更为粗犷的民谣传统相背离,叶芝很快便放弃写作象征主义民谣,一如之前放弃以情节为中心的民谣类型。

诗人叶芝,图片来源:图虫
这时起,叶芝开始对时事民谣进行实验,后来他获得了巨大成功,部分缘由归因于他在剧院的工作让他接触到真正的口语措辞。诗集《责任》(1914)收录了他就休·莱恩遗产纷争所创作的数篇专题民谣,这一纷争源起英国国家艺术馆拒绝都柏林市政府设立画廊、存放莱恩藏画的要求。《1913年9月》,原名《爱尔兰传奇故事——读国家艺术馆质疑报道有感》,以长节奏(即四音步四行诗4-4-4-4)写作。每节诗有八行,由两节民谣四行诗组成,隔行押韵(ababcdcd):
在这首讽刺民谣中,1798年反英斗争牺牲的那些英雄代表爱尔兰“真正的”集体。作为一个疏离的英裔爱尔兰诗人,叶芝一直厌恶同时代中产阶级天主教徒的狭隘和市侩,视他们为陌生的“你们”:
叶芝选择以民谣形式表现《1913年9月》里的事件,他暗示读者“浪漫的爱尔兰”最脆弱的文学体裁就是民谣,但是,他将其立为民族之歌,并在诗里点名那些逝去的英雄。叶芝认为自己是更好的集体代言人。从他最后的民谣作品《黑塔》可见,尽管叶芝从未放弃将民谣等同为爱尔兰人的抵抗,但是他并没有将民谣限于政治话题。尽管他有时会弃用“身份卑微”的说话者,但是,这类“卑微”人物形象的感染力重现于后期作品,比如主人公疯珍妮和老汤姆。
02高雅与低俗的矛盾结合
为了找到高雅与低俗之间的共通点,叶芝有时会过于低俗化。以《在圆塔下》这首民谣为例,在格兰达洛的一个修道院附近,比利·伯恩斯睡在曾祖父残破不堪的墓边,梦见太阳国王与月亮王后在圆塔下载歌载舞,最后双双环绕旋梯登上塔顶。叶芝为在此诗达到高雅与低俗的融合,强行将民谣中粗俗的措辞,加之于炼金术中象征男女完美结合的金和银之上。比利梦见太阳与月亮之舞随着他们步上圆塔顶端而渐入高潮:
通过这种“低俗”的民谣形式,贬低象征皇室贵族间两性行为的神秘主义炼金术,叶芝究竟想获得何种效果呢?他描述的两性行为是比利·伯恩斯讲述的身体咆哮和欢腾与宇宙升华感觉的矛盾结合,世俗的肉体变成了“天上”的太阳和月亮。比利·伯恩斯是叶芝民谣作品中刻画的众多爱尔兰幻想家和警句创作者之一,其中最有名的当属疯珍妮。

叶芝之墓,位于爱尔兰斯莱戈。图片来源:图虫
叶芝写过两首关于复活节起义的民谣:《十六位死者》和《玫瑰树》,一直没有发表,直到1921年才与《1916年复活节》一并出版于诗集《麦克尔·罗巴蒂斯与舞者》中。在这两首民谣中,叶芝尝试以那些死去爱国者的角度思考。
《十六位死者》的标题让人痛心和毛骨悚然,但是它却不失为一篇值得品味的民谣作品,叶芝的民谣措辞并未掩盖可怕的高贵感。这首诗虽简单直白却不显“低俗”,并且其诗艺饶有趣味:即便叶芝几乎每行诗都精选单音节词结尾,但是每节诗里至少有一个出人意料的押韵。他不想用一些陈词滥调歌颂那些被处死的爱国人士,因此他设想描绘了这十六个人死后的生活,他们依旧在就义的地方“徘徊”,而鬼魂并不会如此。反抗的大锅已经架好、水已沸腾,他们在此游荡,或者说这些新近的流浪者在此“徘徊”,不停地搅动大锅以保持活跃。民谣中的说话者转投革命,赞成迅速应对处决,否认长久以来爱尔兰的政治争辩:

1916年爱尔兰复活节起义,都柏林萨克维尔街的一角被大火严重损毁。图片来源:图虫
第二节生动地叙述了这支死亡之舞——尸体聚于此搅动这沸腾之锅,近距离描述皮尔斯、麦克多纳糟糕的身体状况。说话者指责“你”竟然还在争辩(就像当初的叶芝也曾如此)主张等待1914年战争结束后观望议会将采取什么行动:
想象一下,叶芝的同辈诗人被残忍地剥夺了身体感觉和血肉,叶芝让他们的尸体——现已为白骨——无声地见证在暴力面前大谈逻辑是多么地荒谬可笑。说话者感到恐惧和痛苦,这些情感在他脑海中生成了如下意象:诗人皮尔斯失去了耳朵和声音,诗人麦克多纳创作的手指露出森森白骨——他们都陷入困境,几近无声,只剩下寥寥数语。但是他们的白骨获得的应该不只是这可怕的呼唤和怜悯,叶芝不仅“治愈”了皮尔斯的“聋哑”,还赞美了这十六个死者。在他关于他们的最后一瞥中,他们最终找到了爱尔兰的革命前辈并且与他们畅谈,不再像从前泛泛而谈“舍与得”,而是与他们进行“骨与骨”之间的交流,因为叶芝已然了解肉体消失的真相:
《十六个死者》出色地实现了“高雅”与“低俗”之间的平衡,这正是叶芝认为民谣形式最终所能呈现的形式。这种融合让民谣在抒情诗的道路上更为别致。
本文书摘部分节选自《我们隐秘的法则:叶芝与抒情形式》一书第五章,较原文有删减,小标题为编者自拟,经出版社授权发布。
 简体中文
简体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