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 现任《泰晤士报》亚洲主编兼东京分社社长理查德·劳埃德·帕里(Richard Lloyd Parry)在调查3·11大地震引发的一起悲剧事件后认为,“他们(日本政治精英)的忠诚是为了更崇高的事业,远比公共责任或个人尊严更崇高——为了保护组织声誉免受进一步损害,最重要的是保护其免受法律制裁。”他看到,在备受称道的坚忍的日本国民性背后,是无数政治冷漠、对国家意识和民主制度毫无兴趣的民众与徘徊于停滞和失望之间的政治生活。
旅美日裔社会学家桥本明子曾提出“漫长的战败”一词,用以形容二战的文化创伤持续塑造日本国民战后意识与身份认同的道德框架的情况,“这种对国家的疏离感和怀疑态度,呼应了战败后的日本社会经历的那种影响深远的信任危机。”日本历史学家小熊英二也指出,至今为止日本仍然在被“战争留下的东西”束缚着,无论是国际秩序还是国内秩序都仍然处于战争余波中所建立起来的框架范畴内。
在3·11大地震十周年之际,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重刊旧文,以期与读者一同了解和分析从二战至今的、长期笼罩日本的沉重历史包袱与冷漠失落的公民社会。
保守的政坛:天皇制与维持现状的政治精英
1889年,日本颁布《大日本帝国宪法》,根据第一条规定“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之天皇统治”,天皇自此拥有了总揽统治权。天皇直接统治的体制在日本二战战败投降后结束。1946年11月3日,日本颁布《日本国宪法》,天皇再次成为纯粹仪式性的角色,是日本国家与国民的象征,且不再被视作“天照大神的后裔”。
卢梭在《战争与战争状态》一文中提出,战争就是国家之间对于主权与社会契约的攻击。在战争中,参战国家的终极目标就是改写敌国的宪法,即国家存续所仰仗的基本秩序。日本历史学家加藤阳子援引卢梭的观点指出,战后日本在联合国军最高司令官总指挥部(GHQ/SCAP)的指导下颁布的新宪法即为一例:二战结束后,战败国(德国、日本)的宪法——或者说是最根本性的社会秩序——需要以战胜国(英国、美国)的议会制民主为范本进行修正。当然,对于日本自身来说,颁布新宪法也刻不容缓,这是因为当战争带来大量伤亡、全社会都面临劫后余生从头再来的境遇时,国家需要与国民制定新的社会契约,为国民提供新的愿景和目标。
“国政源于国民的严肃信托,其权威来自国民,其权力由国民的代表行使,其福利由国民享受。”《日本国宪法》的前言堪称是“民有、民治、民享”这一美式价值观的翻版,给人耳目一新之感。然而正文第一条就是关于“象征天皇制”的内容。学界普遍认为,天皇制之所以被保留下来,是因为当时驻日盟军认为这将有利于战后日本的秩序恢复。日本思想家鹤见俊辅在与上野千鹤子和小熊英二的访谈中指出,驻日盟军总司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把天皇、文部省、东京帝国大学(今东京大学)这明治日本的三大统治根基原样保留下来,没有改变培养领导者的方法,在统治和经济方面被证明是有效的。
然而这样做的弊端就是日本缺乏战后清算,很大程度上阻碍了日本的战后转型和身份重建。除了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被控告和处决的甲级战犯外,还有数千名级别低的施害者因在东亚和东南亚地区犯下战争罪行被控为乙级和丙级战犯。然而日本没有进行全国性的清算:昭和天皇裕仁作为战时日本总指挥逃过了起诉,包括军队、官僚、政府、商业人士在内的大部分日本人宣称受到欺骗性的军国主义政府误导也未被追责。虽然成千上万的平民因与战时政府勾结而遭到整肃,但随着冷战在东亚地区的升级,很多人甚至在占领结束前便获得了赦免。在鹤见俊辅看来,正是因为战争发动者没有接受裁决,直至21世纪初,日本国会内仍然有很多人认为二战中日本的所作所为是正确的。
在这样一种大背景下,日本的官僚体制和政治精英大体被保留下来。鹤见俊辅指出,从明治时代起,在东京帝国大学等名校接受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便开始大规模进入政坛掌握权力。这样就形成了一种政治共识:通过考试进入名校,以第一名的身份毕业,掌握欧美先进知识的人才有资格参政。鹤见俊辅将之批评为日本知识分子的“第一病”,即对时代主流观点亦步亦趋,缺乏批判思考能力:
逃过战后清算后,右翼政治精英又跟随最新的趋势“变节”,转向亲美。对此持严厉批判态度的鹤见俊辅认为,日本政治精英往往空有争强好胜之心,但缺乏实干和远见,“说想当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但当了之后要做什么呢,谁也说不出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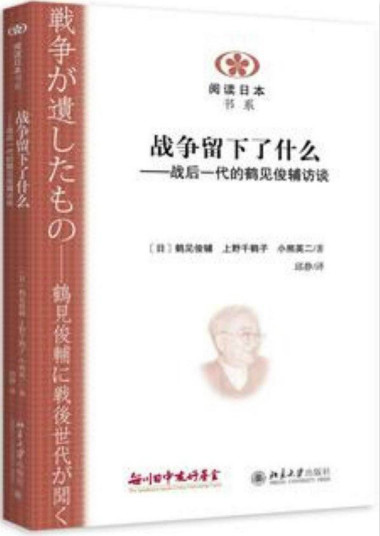
《战争留下了什么——战后一代的鹤见俊辅访谈》
[日]鹤见俊辅、上野千鹤子、小熊英二 著 邱静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年6月
在政治精英的基本构成战后未被打破的情况下,日本政坛较为保守,倾向于维持现状。《泰晤士报》亚洲主编理查德·帕里观察到,尽管日本具有成熟民主国家的一切要素——成文宪法、司法独立、新闻自由、多个政党和清明选举——但日本的政治生态却缺乏活力,至今仍未建立起真正具有竞争力的多党制。他指出,日本的民事司法体系与民主一样,从表面上看无可非议,但“这一体系的核心偏向维持现状以及支持它的私人和公共机构”。
在纪实作品《巨浪下的小学》一书中,帕里深入调查了3·11东日本大地震引发海啸后发生在宫城县石卷市雄胜町釜谷村的一起悲剧事件,并得出了上述结论。2011年3月11日,大地震引发海啸冲击追波湾,位于河道沿岸的大川小学因疏散不力,造成包括师生在内的84人丧生,被洪水围困的78名孩子中只有4人生还。在事后的调查行动中,悲伤愤怒的家长们发现政府官员们一再掩盖疏散措施的漏洞,把事件定性为意外而非人为的悲剧,借此推卸学校和政府的责任。石卷市政府或教育委员会没有一人因此事故被解雇、处罚或正式批评。即使大川小学的家长们于2016年打赢了与石卷市政府的官司,获得了超过1000万英镑的赔偿款,仙台地方法院也未在判决词中要求校方和教育委员会的相关人员担责。
日本官僚体制的自保倾向和政治精英逃避战后清算,在多大程度上共享着同样一套内在逻辑,或许有待商榷,但官僚体制拒绝承认个体失误或系统性的制度失败并为此担责,的确违背了战后日本与国民达成的“民有、民治、民享”的新契约。这亦对日本人的政治参与造成了不良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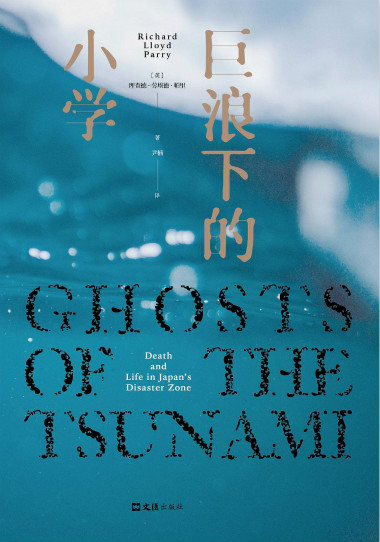
《巨浪下的小学》
[英]理查德·劳埃德·帕里 著 尹楠 译
新经典/文汇出版社 2019年10月
“不爱国”的国民:冷漠的日本民众与停滞的政治生活
帕里发现,在海啸发生后,幸存者迅速自发组织起来展开自救,在巨大的灾害危机面前,日本社会依旧保持着井然秩序。从表面上来看,这是人人称道的坚忍不屈的日本国民性,但帕里却认为,这实际上也意味着日本国民对政府期望过低,长久来看对民主制度有害。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一局面的造成亦和日本二战战败有着脱不开的关系。加藤阳子在《日本人为何选择了战争》一书中指出,直到1937年中日战争全面爆发,日本民众一直试图通过政党政治来实现国内的民生改革,期望形成能够真正代表民意、实现政权有序更迭的政治体制。这其中有选举权不断扩大的结果——从甲午战争(1894-1895)到日俄战争(1904-1905),日本政府为了筹措战争资金不断上调税率,这也在不经意间扩大了拥有选举权的人数(根据1900年修订的众议院选举法,缴纳直接国税10日元以上者拥有选举权),上层阶级之外的日本人也开始对政治参与有所期待,希望自己的利益能够得到表达和尊重。
然而,在二战前日本的政治体制之下,那些呼吁以改革提高国民生活水平的要求在既存政党、贵族院、枢密院等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下无法实现,这导致许多民众开始转向支持看似有诚意推动民生改革的军部。加藤阳子指出,到1930年,日本全国约一半就业人口为农民,此时25岁以上的男子已有选举权,普选也已经举办了三次,但即使如此,保障农民权利的法律仍然不为帝国议会所重视。更雪上加霜的是,1929年从美国开始的经济大萧条波及日本,受冲击最大的就是农村地区,农民迫切希望获得政府补助、低息贷款等政策,然而当时的执政党不为所动。只有军部提出了救济农民、国民保健、劳动政策等民生计划,这对当时的日本民众来说的确极具吸引力。然而被大多数人忽略的一个事实是,军部之所以勾勒出这些美好的蓝图,是为发动战争做好准备——农民占日本劳动人口的半数,又是主要募兵来源。军部在分析一战德国战败的原因后得出结论,只有妥善组织国民才能防止国家在战时从内部崩溃。历史证明,日本悍然发动战争非但没能给日本国民带来他们满怀期待的改革,反而将其拖入了毁灭深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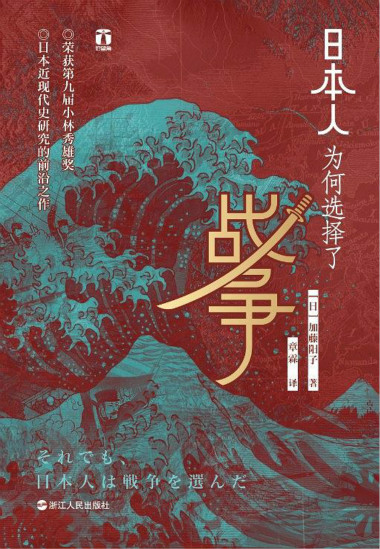
《日本人为何选择了战争》
[日]加藤阳子 著 章霖 译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9年9月
1945年,日本在投降后失去主权,被战胜国占领达七年。在此期间,战胜国几乎对日本社会的各个方面——从政府到法治,从经济到教育——进行了彻底的改革。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日本政府在二战期间行事不计后果,极大地辜负了人民的期望”的概念随着战后教育系统的灌输深入人心。桥本明子指出,尽管日本历史教科书长期被外界指责为淡化日本战时罪行、强化日本作为战争受害者的心态,但课本中讲述的战争故事依然让战后的年轻人了解到了人民惨遭国家背叛的巨大悲剧:
这一方面将日本的战败文化转化为了与德国的“赎罪文化”不同的“和平文化”(日本人意识到只有在和平状态下国家才不会随便拿捏国民的命运),另一方面也加剧了国民对国家的不信任感。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战后年轻一代政治热情的高涨与退潮。1960年5月19日,首相岸信介强行表决通过日美新安保条约,允许美军驻扎日本,使用日本当地设施。在美国正参与越战、二战结束才满15年的背景下,该条约引起了日本民众对“日本将再次卷入战争”的恐惧。与此同时,日本政府从“满洲事变”(九一八事变)以来一直罔顾民意的记忆依然鲜活。鹤见俊辅指出,战后选举权的进一步扩大(投票年龄降至20岁,女性也在名义上获得了选举权)让人们产生了“政府应该听取民意”的想法。这带来了1960年代日本风起云涌的学生运动,其中最知名的就是“60年安保”抗议和“全共斗”(1968-1969)。在小熊英二看来,支撑着学生运动的,是战后日本始终存在的“不能抛弃为大义而赴死的纯真的少年少女们”的伦理。
然而进入1970年代,左翼学生运动变质沦为暴力冲突和派系内斗。1970年3月31日,日本新左派的一个地下分支“赤军派”成员携带武士刀、手枪和炸药劫持了一架从东京飞往福冈的日本航空班机飞往朝鲜。更令全日本社会震惊的是1972年2月的“联合赤军”事件。该团体在长野县浅间山庄与警方交战,杀死了一名警察和一个平民。更恐怖的是,该派系领袖在被收押时承认,他们在几周前因为意识形态问题在山庄内处决了14名组织成员。同年5月,日本赤军又攻击了以色列罗德机场,造成26人丧生。极端学生团体的恐怖行经浇灭了日本年轻人的政治热情。小熊英二指出,在“联合赤军”事件后,为了某种理念去死的“为公”思想退潮,让位于“利己”思想。恰逢1970年代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消费社会兴起,日本人对政治的兴趣不再能和对物质的兴趣相提并论。
在今天,日本是国民国家意识和爱国情感最淡漠的国家之一。桥本明子援引相关调查指出:只有23%的日本人相信他们的政治领导人,在全球135个参与调查的国家中日本位列127;只有54.2%的日本人宣称为国家感到自豪,在受调查的74个国家中排71位,且这种趋势在二三十岁的年轻人以及女性身上更为明显;在高中生中,为日本国歌、国旗感到自豪的人数在11%-13%之间徘徊,远低于美国的54%-55%和中国的48%-50%,表示对自己的国家没有骄傲感的日本高中生(48.8%)比例也高于美国(37.1%)和中国(20.3%)。“这种对国家的疏离感和怀疑态度,呼应了战败后的日本社会经历的那种影响深远的信任危机,”桥本明子写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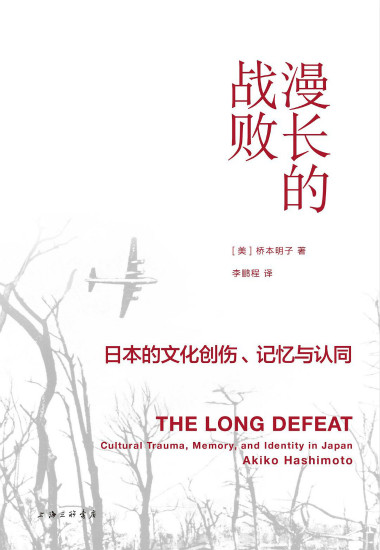
《漫长的战败:日本的文化创伤、记忆与认同》
[美]桥本明子 著 李鹏程 译
理想国/上海三联书店 2019年7月
帕里认为,近年来日本领导层与民众之间的隔阂越来越大,无论是执政党还是反对党,都缺乏能够获得民众信任、具备能力和远见的优秀领导人,这无异于一场严峻的民主危机。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发生后,时任首相菅直人在福岛核事故问题上处理失当,支持率大跌,当年9月不得不引咎辞职,自2009年9月起首次成为日本执政党的民主党也在选举中接连败北。2012年,安倍晋三携战后长期执政的自由民主党重回政坛中心,直至今日。帕里观察发现,许多投票给安倍的选民既不喜欢他也不认同他——他对核能的支持、对二战历史的右翼立场、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以及因此在东亚地区引起的反感都令人忧虑——然而他是唯一一个能够给出切实经济恢复政策的候选人,这让很多日本人觉得别无选择。
对于“不爱国”的日本年轻人来说,一个无法逃避的问题在于,他们必须面对生活在一个经济和地缘政治上都充满不稳定性的时代的严酷现实。自1990年代初经济泡沫破灭,日本的经济前景一直不甚明朗,企业不再能提供终生就业的保障;与此同时,东亚地区的经济与政治格局也在发生急剧变化,中国的崛起打击了日本的自信心,各国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则加剧了东亚地区内摩擦的可能性。
日本正是带着这样的历史包袱进入了令和时代。出路何在?在帕里看来,日本人首先要做的,就是打破政治冷感,重拾个人权力意识,向权威发起冲击,而不再是默默忍耐。站在“令和”之初远眺未来,这样的一天有可能到来吗?
 简体中文
简体中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