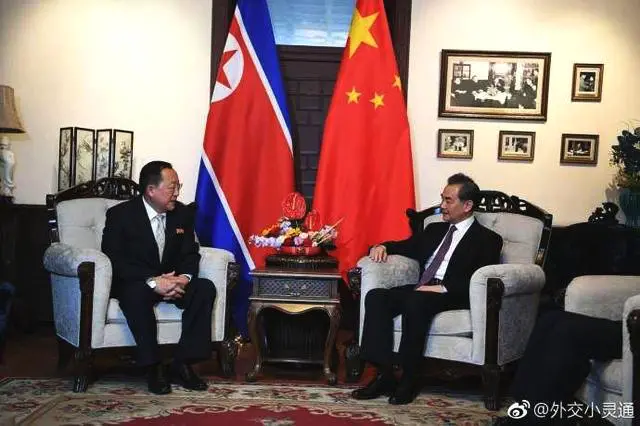紧跟七夕之后,最重要节日便是中元节了,又称“盂兰盆节”,后被民间称作“鬼节”。鬼节自唐朝开始出现在人们的生活中,日渐成为一个重要节日。美国汉学家太史文曾说:“作为一个复杂的象征性事件,鬼节让社会各个阶级聚于一处,并体现出了多种价值观的混合,这种混合令人回味。”
实际上,鬼节根植的土壤与中国历史上的鬼文化息息相关。鬼文化对于现实影响深远,招魂、守孝、服丧等丧葬仪式是中国几千年来延续不断的传统。在现实之外,鬼文化在中国文学领域同样大放异彩,以记叙鬼怪故事为主要内容的志怪小说正是其杰出代表。此类古典小说诞生并流行于魏晋南北朝,一方面不乏宗教迷信思想,另一方面也展示了文人对未知世界的奇幻想象。在所有这些想象和延伸中,“人鬼恋”是不得不提的存在。
自魏晋南北朝开始,人鬼恋的情节开始在志怪小说中出现。这类讲述生者与鬼魂之间婚姻恋情的故事最显著的“套路”是,男女/人鬼双方大多超越了现实束缚,更加自由地表达欲望与爱恨——这或许也是其在古今吸引了众多鬼故事爱好者的原因之一。今天,界面文化为大家梳理了中国古典文学中人鬼恋故事的现实基础、演变与发展,以及我们在当下语境内可如何从性别观、婚姻观等角度审视此类不凡恋情。
冥婚习俗是人鬼恋的现实起源
《说文·鬼部》给鬼下了个定义:“鬼,人所归为鬼……鬼阴气贼害,故从厶(古同‘私’)。”在生者眼里,鬼多是有害的,文学里也有许多恶鬼的形象和故事。受这种观念影响,招魂等丧葬仪式往往系统而隆重,目的之一便是为了求得心安:为死者举行隆重的丧葬仪式,取悦鬼魂并令其满意,以防止鬼魂作祟,活人从而获得安宁。基于这种心理,冥婚现象出现,并成为了孕育人鬼恋故事的现实起源。
据史料记载,冥婚最早出现于周代。《周礼·地官·媒氏》中写道:“禁迁葬者与嫁荡者。”此处的“迁葬”和“嫁荡”是冥婚的两种不同表现形式,分别指为未婚成年人死后、未婚未成年人死后举行的婚礼。自周代到民国这2000多年间,举办冥婚的风气在市井平民与帝王大夫之间一直持续,《北史》《旧唐书》《元史》以及各地地方志都对此均存有记载。甚至是在现代,冥婚也仍在山东等地流行,学者刘晓撰写的《山东省莱芜市冥婚习俗调查与研究》便是这一事实的佐证。
关于冥婚的漫画
文学上,冥婚被拿来借鉴写成故事,人鬼恋便是其中一种。在这些故事里,男性与女鬼相遇,进而相恋,成家或者一拍两散。冥婚甚至还影响了人鬼恋故事的分类。山东大学教授洪树华在《宋前文言小说中的冥婚及其文化意蕴》一文中,将宋代以前文言小说中的冥婚故事分为“合葬式”、“入墓庙结为夫妇式”和“女鬼自荐枕席结为夫妻式”三种类型。以清代蒲松龄所著的《聊斋志异》为例,其中的人鬼恋故事大多在这三类的范畴中,是对当时冥婚习俗的直接反映。
冥婚还影响了人鬼恋故事的创作思想。传统的鬼魂信仰认为“鬼无所祭、无所归必为害”,未婚的鬼魂更甚,因此,让鬼在阴间过上夫妻生活,使其死有所归,成为家族合法成员而享受祭奠的话,鬼便不会再外出作祟,生者也能过上安宁的生活。冥婚的这一出发点也在人鬼恋故事中得到了再现。在《聊斋志异》中的《莲香》和《鲁公女》等篇章里,未婚夭亡的女鬼来到人间,寻找男性来摆脱凄凉的游荡生活,便是冥婚文化理念的投影。
每一个时代的人鬼恋故事都在创新
自魏晋南北朝起,人鬼恋故事有了一个较为清晰的发展脉络,其思想内涵也不断变化:从重视门第到自由恋爱,再到强调道德,人鬼恋的故事看似大同小异,其实也一直在创新。到了20世纪,人鬼恋的故事甚至还涉及到了对革命的探讨,再一次拓宽了这一类型在文学上的表现与摸索。
中国文学史上的第一篇人鬼恋故事是《列异传》中的《谈生》。在这篇小说里,男主人公因女鬼最终收获了爱情、家庭和地位,门第的差别与变化耐人寻味——从寒酸的平民到显贵的望族,男主人公的变故在相当程度上是当时人们渴求翻身变名流的愿望之寄托——这与魏晋时期“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严格的门阀制度不无关系。
到了唐朝,因科举制度出现,门阀制度开始没落,这类讲述贫寒男性赢取富贵人家女鬼的人鬼恋小说发生变化,不太可能再有一个《谈生》那样的“完满”结局。《裴徽》便是佐证之一:男主人公长孙绍祖与女鬼相爱,女鬼也赠送他财物,可财物并不十分值钱,长孙绍祖也并未因此获得社会地位。
及至宋代,门阀制度彻底衰落,市民阶层兴起,个性解放思潮萌发,人鬼恋的小说主角们也开始了自由恋爱。汤显祖的《牡丹亭》是个中翘楚:杜丽娘因爱而死、因爱而生的故事被传为佳话。清代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开始在人鬼恋小说中宣讲道德的重要性。在聊斋的故事里,道德成为了决定一些男主人公命运的砝码:男性若是正人君子,最后便能收获圆满爱情;若是存有邪念,轻则受到惩戒,重则搭上一条性命——《聂小倩》、《画皮》等许多篇章都证明了这一点。
《聊斋志异》 蒲松龄 著
除了道德宣教之外,《聊斋志异》的创新还在于将女鬼身上的人性与鬼性高度融合。蒲松龄通过营造气氛、描摹鬼的形态和“超人”的能力来体现女鬼的鬼性,又使他们褪去了鬼可怕可憎的原始面目,反而充满了光辉温暖的人性美。《聂小倩》一文里,女鬼聂小倩在被宁采臣的正直感动后,帮助他转危为安,还嫁给他做鬼妻,后生育两个儿子。这样的故事安排,与明朝瞿佑的《剪灯新话》中《牡丹灯记》的写法大有不同:在瞿佑笔下,女鬼在身份暴露之后,便拉上男主人公到阴间做鬼夫妻去了。
民国时期科学主义思潮兴起,但人鬼恋故事不但没有消失,反而因时代发展增添了新的内涵。1937年,徐訏发表短篇小说《鬼恋》,讲述了一个不那么正统的“人鬼恋”故事:一位还活着的女子,却始终自称是鬼,在爱情与革命之间,她选择了后者。李碧华后来的《胭脂扣》以殉情而死的女鬼返阳的桥段,道出了她对爱情的怀疑:真正的爱情,在这个年代是否还存在?
深陷“套路”的性别观和婚姻观
纵观中国文学史上的人鬼恋题材小说, 我们不难发现其中某些“套路”:故事里几乎只有女鬼而没有男鬼,形成了一种“生男女鬼”式的故事模板 ;结为婚姻的爱情也大都获得了男方父母的肯定,等等。这样的安排映射了封建时代的现实,而在当今语境下,我们又该如何审视此类“套路”所折射出的性别观和婚姻观?
自古以来,人鬼恋小说的作者绝大部分是男性,再加上故事情节部分雷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明“生男女鬼”模式折射出了男性作者群体自身的愿望和心理需要。在《聊斋》以前,人鬼恋小说中的男主人公多为寒士,无论与女鬼的最终结局完满与否,大多能从中获得一定的好处。《聊斋志异》则将男主人公固定为书生形象,联系蒲松龄本人平生不得志的书生经历,便更能说明其创作包含着对自身情感的宣泄和慰藉,是带有男权色彩的文学想象。
蒲松龄画像
从社会角度看,“生男女鬼”的人物关系模式是男尊女卑、重男轻女的封建传统思想的产物。在大部分人鬼恋小说里,女鬼逐渐集美貌、智慧等美好品质于一身,对男主人公保持忠贞,一直在为男性服务。《聊斋志异》中此类女鬼形象被高度美化,而妒妇等不受待见的女性形象则遭到丑化和贬低,《江城》中的江城、《马介甫》中的尹氏都是这类妒妇的典型代表。这样的情况,是男性本位主义统治文学创作话语权的表露,也是以男性为主导的儒家伦理对男女两性双重道德标准的体现。
在婚姻方面,人鬼恋小说仍大多遵循“父母之命,媒约之言”这一封建婚姻的准则。即使男女一人一鬼、属自由恋爱而非父母指定,但如果要走入婚姻殿堂,竟也要经过父母的允许。在《聊斋志异》的《聂小倩》中,女鬼聂小倩先讨得宁母的欢心,打消她的疑虑后,方才获得了与宁采臣结婚的允许,最后共结连理。《聊斋志异》中其他人鬼恋主角也大多按照此类模式走向了圆满的结局:男女双方因两情相悦而恋爱,最后遵从了封建婚姻制度而使爱情合理化。这一过程实现了儿女自主选择同父母之命的巧妙结合。
值得注意的是,人鬼恋故事中还不乏“二女共伺一夫”的情节,且女方身份多变,可为人、鬼、妖——《聊斋志异》之《莲香》《巧娘》中的“二女”是一狐一鬼;《小谢》《连城》中的“二女”是两个女鬼;《淞滨琐话·玉》《章阿端》中的“二女”则是一人一鬼。在这些故事里,”二女共伺一夫”被描述成一件美事,女方毫无怨言,反倒为促成另一人与伴侣的结合而感到皆大欢喜。这样的桥段所映射出的婚姻观,无疑凸显了男性在封建社会中的权威地位,亦是一种以男性为中心的中国古代文化的体现。
注:本文部分参考了范治梅的《悲欢人鬼恋 阴阳两世情——<聊斋>人鬼恋故事研究》以及刘卫国、陈淑梅的《古今“人鬼恋”模式的演变》。
(来源:界面新闻)
 简体中文
简体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