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上个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生产的一大批作品被称为“革命历史小说”,这些作品“在既定意识形态的规限内讲述既定的历史题材,来实现既定的意识形态目的”。文学批评家黄子平则试图在其中寻求新的解读可能性。他1996年由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推出的《革命·历史·小说》由此而来,这本书为当代文学史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见解,而且其文本细读的方法也树立起了典范。该书曾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在2001年推出简体中文版《灰阑中的叙述》,多年来一直是中文系现当代文学研究生的必读书目。
《革命·历史·小说》曾在2018年由牛津出版社推出增订本,但因一直没有在大陆再版,旧书网上的价格一度炒到了两三百元。经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洪子诚推荐,北京大学出版社日前出版了该书的增订本。新版中补充了黄子平的长篇访谈,涉及他对自己学术道路的清理;还增加了黄子平在中国人民大学任教期间和学生围绕本书展开的课堂讨论,对该书中一些隐而未发的话题加以延伸。
如果把中国当代文学的起点定在1949年,那么黄子平是当代文学的“同龄人”。他1977年进入北京大学中文系读书,在80年代成名,90年代离开大陆,随后在香港浸会大学中文系任教,如今是中山大学(珠海)中文系的讲座教授。他为人们留下最深记忆的事迹之一是,1985年他和钱理群、陈平原进行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提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论述框架,这一文学事件至今还在影响着中国当代文学的批评研究。他们三人也因此被称为“燕园三剑客”,黄子平更是被誉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领域的“第一小提琴手”。
在日前举办的“当代文学:形式与历史——《灰阑中的叙述(增订本)》线上新书分享会”中,洪子诚谈到,他从黄子平这本书里看到,我们不仅要关注文学文本里说了什么,而且“要特别关注怎么说,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说”。他称黄子平“把内容跟形式之间沟通起来,内容是一种有形式的内容,形式也是一种内容的形式,这一点给我印象很深刻”。
“灰阑中的叙述”究竟是什么意思?为何对现当代文学研究如此重要?在这次线上新书分享中,除了洪子诚和黄子平之外,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李浴洋、上海师范大学师资博士后刘欣玥、北京大学中文系在读博士李超宇也给出了各自的思考。

陈平原、钱理群、黄子平
从“铁屋中的呐喊”到“灰阑中的叙述”
《灰阑记》是一个古老的故事,讲的是两个母亲争夺一个孩子,两个人吵架到包大人面前,包拯灵机一动,在地上画了一个圆圈,这就是“灰阑”。包拯让两个“母亲”每人拉住孩子一条胳膊开始拔河,谁先把孩子拉出灰阑就把孩子判给谁。在争夺中,亲生母亲不忍心看自己的孩子啼哭或者脱臼,就撒了手。最后,英明的包大人把孩子判给了放手的这个母亲。
《灰阑记》的故事有很多改编版,德国作家布莱希特就写有《高加索灰阑记》。黄子平从香港作家西西的《肥土镇灰阑记》里看到,在灰阑中任人摆布和撕扯的孩子,突然开口说话了,他的心中所想让包大人自以为聪明的断案方法瞬间变得愚蠢而可笑。黄子平看到,灰阑其实无处不在,所有的叙述都处在这样或者那样的灰阑当中。
黄子平认为,西西小说走出灰阑的方法是援引图书材料和新闻材料来给现实体验做注释。在他眼中,灰阑中的孩子说话,是为那些由高音喇叭发布的权威言辞所做的注释。李超宇认为,“这种注释可以称为一种反注释,即反过来的一种注释,似乎可以对权威言辞有所消解。但是问题在于,灰阑当中,弱者的话语常常很轻易地被打发掉。即使是英勇的反注释,也照样会被纳入法力无边的大注释圈中消失得无声无息。”叙述好像虽然能在某种程度上突破第一层的小的包围圈,但是无法突破更大的包围圈,“就好像孙悟空跳不出如来佛的手掌一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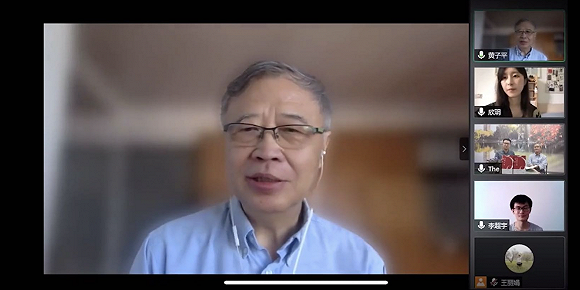
活动现场
但李超宇也看到,黄子平并没有因此放弃叙述,他认为,在《
:时间与叙述》一文中,有一节题为“叙述以反抗‘绝望’”,不妨将之看成作者的一种自况。黄子平在文中说鲁迅“比别人都更充分地把这一‘叙述使命’跟个人的生命体验融为一体,从而借此在语言异化和历史困厄的双重危机中,探询生命的意义和人类生存的境况。叙述成为静夜中的一种挣扎,成为‘明知前路是坟而仍是走’的写作实践。”李超宇认为黄子平也是如此,即使被锁于灰阑之中仍要叙述。
刘欣玥进一步分析说,“灰阑中的叙述”可以看作是鲁迅的“铁屋中的呐喊”在20世纪末乃至今天的回响,两者共同关涉了现代中国文学、现代中国人如何发出声音、如何启蒙、如何自救的这样一个历史命题。刘欣玥说,“铁屋中的呐喊”在鲁迅那里更多涉及的是先觉者如何发声,去唤醒沉睡在铁屋中的老中国的儿女的命题。但是到了“灰阑中的叙述”,姿态变得更加温和,同时不失清醒和坚守。“现在每个人都有发言的权利,每个人都有发言的渠道,但是我们很容易被调门更高、更强势的声音所席卷和魅惑,进而放弃思考。”正如在《灰阑记》里,大家常常只看到断案的包青天,看到两个争夺子女的母亲的申诉,却很少看到那个被争夺的孩子也可以自己发声。因此,“在这样一个无往而非灰阑的世界里,我们需要的可能不仅仅是帮助弱者发声,还要去倾听更边缘、更微弱但是可能是更智性的声音,学会对他们做出有效的声援和回应。”
重读、重写、再解读
李浴洋记得,黄子平曾经说过“所有的证据都在文本里面”,他重视文本,对文本的态度是“既信任又不信任”。一方面对所有的文本首先采取不信任的态度,从正面看、从侧面看、从背面看,看出文本的“秘密”来;另一方面,与同代的学者相比,黄子平的研究又体现出了一种对文本的执着,那些学者可能会直接使用历史材料或批评材料,黄子平则始终“信任”文本本身。
对于这一评价,黄子平说,对文本的细读在中文系或文学批评界一直发展得不够。“我们太早地把‘新批评派’的细读方法超越了,或者说把它抛弃了,这是不对的。”他认为,一定要“重读”,因为对一个文本读一遍,是不会有什么心得的。正如李超宇所说,正是通过“重读”,黄子平发现了文本内部的矛盾、杂糅、暧昧之处,“把文本的缝隙扯得更宽一些,让读者看到性、宗教、江湖等范畴和革命历史小说之间复杂而微妙的关系”,甚至还可以用作家本人的创作谈来解构作家的写作。

《灰阑中的叙述(增订本)》
黄子平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0-02
刘欣玥提到,今天可以把《灰阑中的叙述》放在起源于80年代广义的“重写文学史”的思潮中去看待。“重写文学史”最早是1988年上海学者王晓明和陈思和在《上海文论》主持的专栏,以当时的审美标准重新评价过去的名家名作以及各种文学现象。“重写文学史”思潮在80年代出现还有另外的寓意,就是要找到一个全新的框架,使现代文学中被侮辱、被损害的人能够重新发出声音。
“重写文学史”作为一个口号正式提出是在1988年,但是关于重写文学史相关问题的讨论和努力早在80年代更早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其中就包括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参与的“20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挑战曾经依附于政治史的文学史叙述,要求把文学史重新还给文学。
刘欣玥看到,虽然“重写文学史”专栏只开了一年《上海文论》就关闭了,但是关于重写的热情和思考并没有终止。刘欣玥认为,在一个整体的、更大的“重写文学史”的脉络中,黄子平每一步都没有缺席。在这个大时代的文学研究的转向里面,黄子平曾经和一批他的同代学者共同关切着如何重新去组织文学史叙述的问题,他们之间的对话也构成了《灰阑中的叙述》的语境,“这本书也是在这个过程一步一步实践出来的产物,是曾经非常贴近时代脉动的见证。”
《灰阑中的叙述》非常重要的背景就体现在“重读”和“重写”之中。黄子平说,其实重读、重写、反思、再解读都是同一个意思。“这个几乎就是80年代的一个潮流,表面上是一个动词,反复出现,但是它是一个思潮,对习以为常、已经没感觉的东西,人们希望重新读出它里面的各种缝隙、各种内在的矛盾。”
 简体中文
简体中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