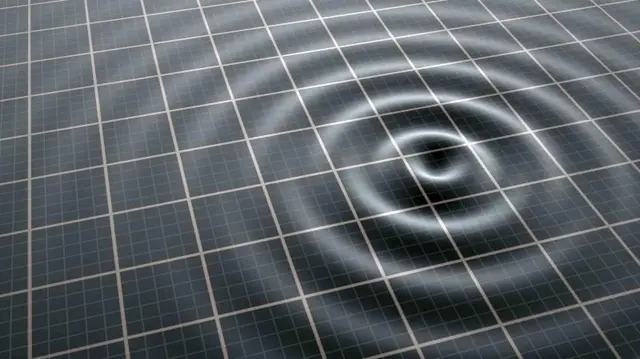“各种人,在这里找到了自己顽固的家乡感。”
又至春节,又是一年返乡潮。尽管如今经常能听到“年味淡了”、“春节越过越没意思”的说法,尽管如今的拜年给红包正在逐渐被微信红包取代,但春节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地位仍然无法撼动。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可能是故乡的食物。能和家人团圆、能在除夕之夜一起吃一顿年夜饭,对很多人来说意义非凡。每当这时方才觉得,月是故乡明,胃是故乡胃。
在春节到来之际,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经出版社授权,选取了王恺《浪食记》中的两篇文章,试图以此对故乡和食物的关系稍作梳理:一篇讲的是故乡的食物如何跟随人口流转,来到许多人拼搏奋斗的北京;另一篇则关注张爱玲想象中的故乡美食“粘粘转”。相比一生漂泊、只能通过文字来想象家乡安徽小吃的张爱玲,在北京打拼的人们何其幸运。他们因为不愿意亏待自己的故乡胃,索性把故乡美食一起搬到了北京。王恺以饕客的视角,记录下了这些在城市夹缝和边缘中生根发芽的故乡美食,它们和主流话语中那些精致的菜品不同,它们热闹、活泼、接地气,充斥着无限的原始生命力。
《北京温暖了流浪异乡人的胃》
从前北京广泛分布有城中村,刘震云的小说中最擅长写这些角落。城中村里的人在各个不同聚集地穿梭,演绎灰扑扑的人生,躲藏在这个巨大城市的阴影里,简直是卡拉瓦乔寥寥几笔勾出的躲在画面最暗沉处的卑微生存。也说不上好坏,开个小餐馆就是生计,有河南人做烩面的,有新疆人做拉条子拌面的,也有山西人辛勤地每日刀削—那是还没有流行丑陋的刀削机器人的年代。
近年城市改造加快,北京主城区里的城中村越来越少,遍地开花的“杭州小笼包”“沙县小吃”都和原产地没什么关系,基本属于生拉硬扯的亲戚,尴尬地存在着,完全不属于城中村里散发着温燥之气的乡亲饮食系统。
去杭州那么多次,却只吃过一次小笼包,可见在当地并不流行。不过那个小笼包在杭州倒也出名,开在欢场附近,安徽人开的。每到夜间12点正是营业高峰,几个说着乡下方言的大叔奋力和面搅馅,包出龙眼大小的包子,各种穿着轻薄纱裙的小女生在寒夜里出来吃夜宵,披着假皮草,或者用羽绒服裹住自己,有种同样轻薄的滑稽感。因为太不像日常饮食,包包子的不像,食客也不像。我只记得那夜里蒸包子的腾腾热气,喧嚣的、寒薄的气体,在夜空里弥漫不去。
没有了城中村,各种乡土食物就在城市里隐藏了起来,就像穿着土气的乡亲不太好意思上街闲逛一样,只有借助各种美食节目的流行偶尔露面。最近流行的“重庆小面”就完全是《舌尖上的中国》的副产品,北京现在至少有上万家了吧?不管是不是碱水面,也不管那碗红油合格与否,都挂了牌子,就像是偶尔流行过的松糕鞋,瞬间不见,又瞬间满大街,实在是丑,但是因为流行,也昂然地抛头露面。
《浪食记》插图
近年北京忽然多了各种市场,茶叶市场、建材市场,外加服装市场,蓬勃发展,灰扑扑地开在各个奇怪的城乡接合部所在,结果那些以往消失的乡土食物,突然都有了重生土壤。上马连道逛茶叶市场,总会去那里的几家福建餐馆吃饭。全国做茶叶生意的,80%是福建人;而福建人中,又以闽东居多,所以马连道附近的餐厅,以闽东人的口味为重,装修简陋到不行,可是吃得好。
每次和朋友吹牛说,我吃过全京城最豪华的沙县小吃,大家都瞪大双眼,觉得我在痴人说梦。可是,这家沙县小吃真是豪华,近百张桌子摆在院落里,尤其是夏天,无边地蔓延开去,很多福建乡亲,说着他们的方言,旁若无人地吃着喝着,应酬了白天的生意,夜,属于他们自己。
巨大的冷菜柜台,里面有卤笋、卤豆腐和大肠,那油腻的白色猪油还附着在大肠上,一吃,却甚是美,熟稔的家常感。有荔枝肉,也有各种小海鲜,哪里像一般沙县小吃只有寥寥无几的肉饼汤和花生酱拌面,小海鲜都是当天从福建空运来的,蛏子肥美,花蛤无沙。无他,马连道茶城里面的福建人多为吃客,大家懂得什么是福建菜,自然是挑剔的,所以老板不能不地道。
每次都是冷菜数道,海鲜数道,简直像宴席,完全打破了一般沙县小吃的格局。最终基本都拿一盘福建炒米粉做主食,和在福建当地的小城餐馆吃饭的次序一致。旁边还有家“福鼎海鲜”。别的不说,有道野生紫菜鱼丸汤,每次都点。那鱼丸比起福州几家老字号的也不差,外面是经过无数次捶打的筋道的鱼肉,里面是鲜肉馅,据说也是当天用飞机从福建运来。老家人的手艺,加上野生紫菜的鲜香,小吃被衬托成了一道名贵的大菜,充满海洋的腥鲜之气的大菜。
《浪食记》插图
不过这里卖的价钱也并不贵,毕竟吃客们都是知道根底的家乡人,赚的钱也是安分守己的基本的利润。几百个人每晚在夜宵摊上,共同构成了一曲巨大的“乡愁交响曲”,但是在这里并没有人说怀念家乡的话,都是最平凡的生意人,在北京做着一点自己能做的生意,没有那么凄凉,倒是朴实无华。
市声是哄闹着、流动着的所谓时代洪流,个人命运裹挟在其中,飞得或高或低,全凭运气,是真正的大时代。
夏天天气凉爽,户外有种特殊的惬意感,来这里的人更多:北京人来点烤串拍黄瓜的,对海鲜完全置之不理;旁边一桌河南人显然是贪图便宜来吃饭的,要西红柿鸡蛋汤,我都替厨师的手艺惋惜,可是服务员还是面不改色地接单—这就是身在他乡的生存能力。
各个建材城附近,花样也多。做建材的,多福建广东人,建材店旁做玉石生意的,则为河南人,所以那附近的小餐厅,也是以他们的口味为基本诉求。北京建材城庞大,也就把周围都辐射成了自己的附属地,一个小家装中心附近,说不定就有两三家小潮汕餐馆、三四家河南小店。因为都是乡亲店,所以完全省略了一切花哨的招数,有几家都叫“潮汕餐馆”这个名字,前面连定语都没有。
常去的一家,还真地道。老板在门口支起炉灶,专门现拉肠粉,和我们在汕头街头所见的小抽屉拉肠粉没什么两样。
那年去到汕头,深夜在街上觅食,看见大批学生仔聚集在肠粉摊前,摊主忙碌到根本不想解释有什么品类的肠粉。近百个小抽屉依次拉开关上,颇有大炼钢铁时代热火朝天的气息。我非常茫然地跟随着点了—鲜香的米浆裹着少量瘦肉,那点肉,简直是魂魄,非常少,气若游丝,却让吃那米粉外皮的理由充足了许多。
《浪食记》插图
与汕头相比,北京的肠粉摊可没那么忙,无人排队。大约这里的知音不够多,我们点了两客牛肉肠粉,壮硕的潮汕人模样的老板非常开心地忙碌起来,先摊米浆到小抽屉里,然后加蛋浆加嫩牛肉,一丝不苟。这肠粉里有心意,那牛肉也是汕头街头的数倍,当然价格也贵了几番。吃客和老板,难得电光火石地瞬间对了眼,操作者就是希望你满足—当然满足,无论是米浆外皮的润滑度,还是满口嫩牛肉的饱满感。我是吃完了郑重谢谢。
这种餐馆,开在这种脏乱的地方,不是知情人,也不太会来。也是因为点菜的多是本地乡亲,大厨在后面忙碌地做普宁豆酱炒芥菜、酸梅酱蒸小海鱼,前面的戴眼镜的账房在那里悠闲地泡凤凰单枞,和在潮汕本地所见没什么不同,不过这里却是异乡,一个他们毫不了解,也似乎没有多少兴趣了解的异乡。趁年轻,在外面多闯闯,老了再做打算,尽于此。
照顾前台的是位能干的潮汕女人,染着黄发,一边切着猪尾鹅翅的卤水,一边准确地算账,对偶尔来访的北京食客的好奇心予以冷淡而礼貌的回答:对的,这是猪尾,很肥;这是番薯糖水,很甜,我们常吃。那番薯糖水熬得近乎浓稠,和潮汕当地的清淡完全两样,也不知道是他家特点,还是因为要适应北京人的重口味?
也有脱离各种茶城、建材市场的孤独的存在。有次在望京地区发现一家泸州的街边小餐馆,完全在北京的旧居民区里面,估计就是租金便宜,格局却像四川小城那些居民区的餐厅—里面是排列得十分粗糙的桌子,外面有煮面的煤球炉子,要吃燃面,或者干墩面,在餐馆外面就可以解决。寒冷的北方少见这种格局,显然是家乡的习惯在起作用。加上周围小区的陈旧,几乎怀疑自己是重回了四川的那座温暖小城。
来帮衬的不完全是老乡,有很多北京人,也可能川菜接受度高,所以流行。可是菜,居然是十分地道的、并不流行于北京的家乡川菜:麻辣兔丁里是新鲜的兔肉,真不知道怎么运来的;活水鱼嫩滑可口,似乎看得见一丝鱼肉里的血迹,没有完全烫熟,可是入口却又是完美地嫩;血皮菜炒猪肝是离开四川乡镇就难以吃到的美味,外加撒了大量花椒末和白糖的四川凉面,简直是在泸州老城,半夜时分,听江水缓慢呼吸,坐在街边吃平实川菜的享受。真不知道这小老板怎么就流落在了这里,安然地做着自己的家乡口味—完全是一个当代的传奇。
《浪食记》插图
各种人,在这里找到了自己顽固的家乡感。穿着夹克的小老板和他们形迹可疑的女人们,带着自己家的老猫出来游荡的北京老人,还有我们这种钻头觅缝寻找美味的讨厌客人,都安然地坐了下来。
我们不说驻京办的故事,固然现在它们被整顿了,可是那里面还是有官场气,那种菜肴体系里面,有表演的气质,也有造作的心,远不如这些市场附近的小餐厅,或热闹,或明媚,温暖了漂泊在京城的小商贩们的胃,也温暖了我这种饕客的心。
《张爱玲的乡愁邂逅乾隆皇帝的菜单》
张爱玲在《谈吃与画饼充饥》里说她的家乡小吃粘粘转,其实也是想象,毕竟是她从来没有去过的家乡—也是现代人才有的乡愁观念:
我姑姑有一次想吃“粘粘转”,是从前田上来人带来的青色麦粒,还没熟。我太五谷不分,无法想象,只联想到青禾,王安石的新政之一……我姑姑的话根本没听清楚,只听见下在一锅滚水里,满锅的小绿点子团团急转—因此叫“粘粘(拈拈?年年?)转”,吃起来有一股清香。
这种吃法很难想象。青麦粒甜食或者咸食?我对安徽菜很是陌生,除了对古徽州一带稍微有点明白,合肥现在的饮食完全没有好印象,就觉得咸。屡次出差,都是被熟人带着去他们以为好的馆子,只有咸和辣,包括他们总喜欢点来炫耀的臭鳜鱼,甚至比不上北京的安徽馆子。
当下的中等城市往往吃得不好,因为被外来的菜品冲击坏了,尤其是前些年流行过的粤菜川菜加湘菜,简直是颠鸾倒凤般的冲击味觉,把传统味道毁了一半。外加原材料也不好,不够新鲜,只有靠厚味来掩饰,倒不如小县城,守旧加上食材好,吃得好。
想象中的安徽菜肯定不是如此。张恨水写《春明外史》,男主角也是安徽人,爱好南味,女主角知道他的爱好,老是自家烹饪几味南方菜肴,给客居京城的他解馋。有笋的清鲜,有鱼的柔腻,也有火腿煨汤的厚味。
这本书很是滑稽,男女主角始终守身如玉,原因是女主角有隐疾,不能婚配。这个奇怪的原因简直没有说服力,不过倒是给读者很多猜测的空间—不婚,所以格外做好菜款待男主角,借助食来补充色的不足?或者仅仅是作者想念家乡的味道,借此写了出来?
张爱玲也读张恨水,可惜她没去过安徽,味道又是一个非要尝试才能知道的东西,靠文字简直说不明白。领袖说过,要知道梨子的滋味,尝。所以张爱玲的“粘粘转”终究是归于空虚,就像好天气里飘在天上的一朵小云,粘上去,小画儿一样,飘零的漂亮。
《浪食记》插图
何况她是后来在海外写的这种遥远故国的食品,更是不可说了。
现代人的乡愁,很多是形诸语言的,因为没有回过故乡,便只是个名词。名词里又衍生出名词,成为一座名词的山峦。二十世纪的中国人,动乱不停,迁移不定,关于故乡的知识,大都是建构出来的。许多大都市的人填起籍贯来,还是陕西河南广东,但是甚至一辈子无从拜访过。父母亲那辈已经移民,他们从小就一直吃着当地菜,或者说,食堂菜,粗糙的日子容不得讲究。加上从前穷,钱得算计着花,提起家乡来都是寒酸的穷亲戚,不够坦然。所以那种种乡愁,近乎影子,像是水墨画上最轻描淡写的一笔,可有可无,哪里还能有理有据地写上。
一直在某处定居的人,也无从有故乡的概念,因为一切都是贴肉的,无疼也无喜。小城市居民,本身文字好的也稀少。唯一写故乡写得好的,也就是几位“五四”文人,因为从乡下到大都市,光怪陆离之时,偶尔会想念家乡的清欢。
真是清欢,就像周作人文章里淡得几乎没有味道的豆腐干和黄酒。
说这么多,是因为翻看论文,里面有乾隆下江南时的菜单,提到真实的“粘粘转”的做法。乾隆三十年四月,下江南途中,在山东夹马营和马头营一带,皇帝吃到了“粘粘转”—据说是那个年代北方民间经常食用的食品,宫中也有进贡。这次应该是季节凑巧,下面人也凑趣逢迎。乾隆关心农事,下大雪滋润了土地,一定要写诗,碰上新麦抽穗,自然也不会放过。这种食品的做法是将新麦穗煮熟,剥去壳,然后磨成细粉,最后是一碗清香的面条,叫“粘粘转”,也叫“碾转”。应该是象形命名法则,“粘粘”,其实是磨旋转的样子。
久寒的大地出了新苗,在农业社会自然是大事。可是又不能大吃,毕竟是新粮食,吃太多有糟蹋的嫌疑,所以应该是富贵吃食。想象中那面条绿色尚未褪尽,加上红的火腿、老母鸡炖的乳白色的汤,定然美味。乾隆的菜单很是有趣,天天“肥鸡大鸭子”,看起来都很腻,没多少奇技淫巧,也没有螃蟹的影子。
去陕西驻京办吃饭,点了爽口麦仁。用麦仁拌菠菜,一大盘,新绿加重绿,陡然明白,这麦仁,大约也是冷冻的新麦,也可以做成“粘粘转”。不知道为什么调出甜酸的味型,而且有点腥,也是一道奇怪的菜。随手记下来,当是记录流年的意思。
(来源:界面文化)
 简体中文
简体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