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 20世纪60年代起,西方国家的犯罪率不断上升,人们开始质疑监禁能否有效地震慑犯罪。与此同时,监狱的人口压力、公众的失望情绪、狱政改革的缓慢、犯人的权利意识与狱警的强硬态度结合在一起,打破了监狱中本已相当脆弱的秩序。
1971年阿提卡监狱暴动引发了美国社会的巨大风波,近年来关塔那摩监狱虐囚丑闻不断传出,劫持人质事件、游行甚至全面反抗更是层出不穷,不仅是在美国,监狱暴乱等现象也时常发生于西班牙、法国、加拿大、英国、意大利等国家。对于中国而言,这类现象与相关讨论相对更为少见,但其并非与我们毫无关系。
我们通常会认为监狱的存在理所当然。对于不触犯法律的人而言,现实生活中的监狱与刑罚似乎显得微不足道。然而,当监狱一次次成为焦点,监狱背后的重重问题也逐渐暴露。
监狱将国家权力的道德性问题以最严酷的形式呈现出来。如果说,强制力是维护任何社会秩序所必需的条件,那么国家能够对反抗者合法地施以何种程度的强制?
为了检视刑罚的道德性和策略性,叶礼庭的《痛苦的正当尺度》带领读者回到18世纪的欧洲,那时约翰·霍华德、杰里米·边沁和切萨雷·贝卡里亚最先把监狱刑罚当作重要的社会问题加以探讨。与此同时,“针对心灵”的监狱管教逐渐取代了一系列“针对身体”的刑罚鞭打、烙印、枷锁和公开绞刑。这种刑罚方法上的大转型,出自哪些新的需要、哪些有关痛苦的新认识呢?出现在高墙内的新权威形式,又是如何与高墙外的阶级关系和社会策略变化互动联系的?
经出版社授权,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节选了书中部分章节以飨读者。在这个部分我们可以读到:监狱的改革者如何以规则代替权威,既控制罪犯,也控制监狱的管理者,以无处不在的督查造就全景敞视的监狱;他们又是如何诉诸负罪感和孤独感,以更加柔和方式来规训罪犯,以“爱的绳索”将心灵约束在对罪过的悔恨中。这些思想虽然诞生于18世纪的欧洲,但时至今日依然对我们的世界产生着重要影响。
爱的绳索,铁的桎梏
虽说监狱改革者总把违法乱纪者说成需要修理的机器,但矛盾的是,他们还认为这些人像汉韦说的那样,是“行动自由的人,能够向善悔恶”。杰里米·边沁有时称罪犯是有故障的机器,有时又说他们是应该得到社会保护的理性人,他在二者间交替,完全不感觉矛盾。霍华德不但坚持认为罪犯是有理性的,还认为他们是知羞耻的。换言之,罪犯可以被改造,因为他们和其他人一样,都有良知。正如一位改革者所言,在每个人心中,包括在罪犯心中,“都有一种对法律的尊重,他绝不会侮辱法律,就如他第一次犯罪后一定心怀悔恨一样,这种尊重使得他的心灵能够接受改造”。另一位改革者写道,道德律令“是刻在人们心上的”。
当改革者为良知的概念在心中寻找一席之地时,他们的关联论观念让他们遇到了一些困难。唯物主义心理学明确否认内在感官的存在。洛克坚持认为,责任并没有铭刻在人的心脏上。责任是孩子通过奖惩机制从权威那里学来的一种义务。洛克相信,人们的理性足以让他们评判善恶,但如果他们的道德教化有误,他们心中并没有良知的声音将自我从不断寻求享乐的歧途上召唤回来。
……
最先发现负罪感有社会功用的人并非18世纪80年代的改革者。洛克在《论教育》谈到了体罚,他认为教师应该尽量少用棍子,不然孩子未来在挨打时会不觉得羞耻。“唯一能算得上美德的真节制,是因犯错和受罚而感到羞耻。”“如果没有羞耻感,棍打的疼痛很快就会消失、被遗忘,棍打多次之后其震慑作用就会消失。”当扩展到师生关系之外的社会上时,这种理念意味着一种靠威慑来维持秩序的社会,它绝对不如一个自愿遵守法律的社会那样稳定。在一段亨利·菲尔丁在18世纪50年代常爱引用的布道中,蒂洛森大主教(Archbishop Tillotson)说:“对法官权力的畏惧”,只是一种“脆弱而松散的服从”,“一旦人们的反抗没有风险,而且有利可图时”,它的作用就会消失。大主教认为,统治者必须让不服从的臣民感到羞耻。“其他义务都崩溃时,良知会让人坚持下去。”
如果社会秩序有赖于让公民因受罚的风险而感到羞耻,那在公众眼中保持刑罚实施过程的道德公正性就变得至关重要。因此,对于社会秩序而言,关键就在于,在实施刑罚时,要让受刑者和观看者心中都保有对施刑者在道德上的尊重。惩罚的效力取决于其公正性。这样就出现了一个悖论:最痛苦的刑罚,那些最能激起负罪感的刑罚,是那些遵守最严格的法律和道德标准的刑罚。在这些刑罚中,人们不能再靠蔑视施刑者、宣称自己无辜或抗议刑罚残忍来寻求心理上的逃避。在刑罚实施的过程中,任何事都不会将罪犯的注意力从反思自己的罪过上转移走。一旦认定自己的判决是公正的,认定抓捕自己的人是出于好意,罪犯就只能在懊悔的恐惧中就范了。
刑罚只有在罪犯和公众尚未感到离心离德时,才能激起人们的负罪感。18世纪80年代的改革者肯定不是最先意识到这一点的人。但他们的确最先主张罪犯也有悔过的能力,这种能力可以通过精心论证和科学实施的痛苦来唤醒。举例来说,洛克对矫正罪犯表示怀疑。他怀疑罪犯是否有可供改造的良知。在《政府论下篇》中,他将罪犯贬低为奴隶,他们的过失给予社会任意剥削他们的权利。
相较之下,霍华德毫不怀疑他能靠诉诸罪犯内心善良的一面来治理他们:
如果公正的待遇能争取到罪犯的良知,滥权则会疏远良知。改革者坚持认为,像鞭刑这种体罚,以及监狱的肮脏状态,侵蚀了罪犯和普通大众对法律的尊重。由于在改革运动之前似乎不存在大规模针对监狱弊案或体罚的公众抗议,改革者似乎把自己对肉体折磨的强烈感受当成了社会整体感受的表征。
他们警告说,经常执行“严厉程度变化无常”的处决毫无必要,而且通过公开而血腥地折磨罪犯“将他们永久固定在恶行中,无法让他们改过从善”。一位作者在18世纪90年代写道:“过度的惩罚更多激起的是群众对受刑者的同情,而不是对罪行的义愤,这把法律的本意抵消掉了。”
监狱改革者对关押机构的弊病和肉体折磨的强烈感受反映了一种深刻的忧虑,他们担心在公众(特别是穷人)眼中法律体系并不公正。在辉格党18世纪70年代的激进议会改革主张中,人们能察觉到一种类似的忧虑,以及一种利用改革来增强公众守法意识的愿望。辉格党政论家喜欢详细论述公共秩序在共和政府与君主政府中的区别。理查德·普赖斯察觉到,由于人们能参与到立法过程当中,公开绞刑在马萨诸塞州很少见。在英格兰,由于公民无法通过民主参与增强自己内在的义务感,处决每天都在发生。当本杰明·拉什1787年在论述死刑是“君主制政府的必然产物”时,反映的也是这个主题。由于国王相信自己具有神授君权,他们自然也拥有了“剥夺人生命的神圣权力”。他们视臣民为自己的财产,“他们让臣民流血时表现得冷酷无情,就好像宰杀绵羊或牲畜一样”。他说,共和政府的“理念完全不同。他们珍视生命,增加了公私各方保护生命的义务”。
在为一个不平等的社会设计一种更坚实的社会秩序时,辉格党的改革者再次强调政府需要遵循人民的意愿。除了卡特赖特少校,他们都不能算民主派,但他们都坚持普赖斯所谓的“公民政府……是由人民缔造的”。伯格说,无财产者可能没有选举权,但需要使他们相信他们的统治者是在为公众谋福利,而不是在中饱私囊。
美国独立战争期间共识式的权力观复兴了,这有助于解释监狱改革者为什么坚持寻找一种让罪犯感到痛苦的同时又不使他们离心离德的惩罚方法。但是他们怎样才能将这种理论付诸实践呢?霍华德坚持认为:“温和的管教通常比酷刑更有效。”为取代“野蛮的惩罚方式”,他提出了“一种更理性的方案”来“软化心灵以使其得到改善”。正如《预防犯罪论》的作者约翰·布鲁斯特(John Brewster)那句令人胆寒的话所说:“既有爱的绳索,也有铁的桎梏。”如果“恐惧的盛怒”不能使罪犯屈服,“施加更柔和的影响”也许能把他们争取过来。爱的绳索能将心灵约束在对罪过的悔恨中,铁的桎梏只能拘束人的身体,却任由愤恨在心中发酵。
布鲁斯特所谓的“爱的绳索”就是那些改造主义和功利主义的刑罚论,这些论点能说服罪犯接受自己的苦难,面对自己的罪过。需要注意的是,这些新兴的刑罚论都是针对囚犯的。改造主义理论会告诉罪犯刑罚是“最有益于”他们的事情,而功利主义理论会将刑罚说成一种基于社会需要的公正之举。改革者希望通过放弃应报理论清除掉刑罚中的愤恨。用边沁的话来说,由于囚犯能接受其公正性,刑罚就不再是“一种愤怒和复仇的举措”,而是一种精心算计之举,受制于社会的公益和罪犯的需求。
用爱的绳索捆住囚犯的是监狱牧师。他们会说服罪犯接受自己的苦难,将其视为公正而有益的惩罚。牧师会强迫他们接受自己的罪过。牧师的任务就是把他们关到意识形态的监狱里。在18世纪90年代,囚犯能听到监狱牧师在布道台上这样说:
然而光靠讲道不能说服罪犯接受刑罚的公正性。除此之外,当然还需要关押机构的管教来确认法律体系的善意和公正。换言之,改革者的任务是让刑罚的合理性变得显而易见。
……
如何才能在监狱和工厂中建立理性的权力体系呢?在实践中如何调和“人道”“恐惧”“利润”和“善意”的不同要求呢?对于改革者而言,这些问题都转化成了另一个问题:如何控制这些机构中的监管人员?
答案是树立规则的权威。监狱改革者相信,由于施刑者享有无限的自由裁量权,刑罚在穷人中丧失了道德权威。监狱沦为培育犯罪的温床,因为治安法官没有执行明确的管教、卫生和劳动规则。由于典狱长的权威不受规则和督查的节制,监狱中腐败、后门和虐待丛生。为取代“不受管制的自由裁量权”,改革者提议用“基于规则的温和管理”来将其取代。
在霍华德心中,规则既要适用于囚犯,也要适用于工作人员。他提议的新规则中,有一半是关于禁绝工作人员倒买倒卖、言语侮辱、胡乱收费或肢体虐待的。规则中还有一组是关于看守任务、督查巡视、点名制度、睡前检查和夜晚巡逻的。看守和犯人的行为都通过正式的管制规程化了。
改革者对收费制度的攻击是专门用来限制看守人员自由裁量权的。通过取消收费,改革者希望将典狱长从独立承包商变成政府的受薪雇员。为确保典狱长认真负责,改革者提议将治安法官的季度督查强制化。
这种对自由裁量权的攻击意味着,刑罚对于实施阶级统治极端重要,不能交给私人承包商来完成。现在政府要直接监督其实施。
规则同样适用于囚犯,它定下了一个由困苦构成的精细网络,将狱中生活标准化,在孤寂的恐惧中又增添了单调的痛苦,最终抑制犯人的亚文化。这种亚文化和典狱长的自由裁量权一样,阻碍了过去公正而定量施加痛苦的尝试。这些规则的意图在于把监狱从罪犯和典狱长手中夺回来。为取代罪犯和看守之间不成文而腐败的习惯性权力分配,改革者提议将双方都置于一种由外部执行的正式规则的管理之下。
督查是这种新权威体系中的关键词。在《全景监狱》(一份出版于1791年的感化院草图)中,边沁把囚犯和看守都置于一个在中央监控塔中不断巡视的督查员的监视之下。从这个有利的角度,督查员能看清楚囚犯在牢房中的情况,以及看守在巡逻时的情况。如此一来,看守人员和囚犯一样受制于“无法违抗的控制之下”。
这种督查应该是民主的。公众能自由出入监控塔,以监视督查员。无处不在的督查,针对所有人而设,通过所有人实施,这是边沁解决谁来看管看守这个老问题的方法。
因此,规则对于改革者而言有着双重含义。它们列举出了犯人要经受的苦难,但同时也是他们的权利宪章。它们约束着关押机构中的双方,让他们都得服从一套由外部来执行的公正规范。就此而论,规则调和了政府、看管者和囚犯的利益。
单独囚禁同样调和了恐怖与人道。改革者不怀疑单独囚禁是折磨人的工具。约翰·布鲁斯特生动地描述了孤寂所能造成的痛苦:
乔纳斯·汉韦毫不含糊地承认除了死刑之外,孤寂是一个社会所能施加的“最恐怖的惩罚”。他同时坚持认为,这也是“最人道的惩罚”。罪犯没有经受任何凶狠、残暴的折磨。政府好像在打碎他们的锁链之后消失了,让他们与自己的良知独处。在牢房的寂静中,囚犯受到了一种权威的监督,这种权威条理性太强而令人无法逃避,太过理性而令人无法抗拒,他们会接受悔恨的鞭打。拉美特利说:“折磨人类的人最终会折磨自己。”
这就是伦敦和工业城市中那些支持霍华德事业的非国教医生、慈善家和法官所表述的感化院理论。他们支持感化院的理念,因为作为一种权力体系和一种重塑人类的机器,它反映了一些他们内心最深处的政治、心理和宗教理念。最关键的是,这个理念给他们一种希望,能重新树立法律体系的公正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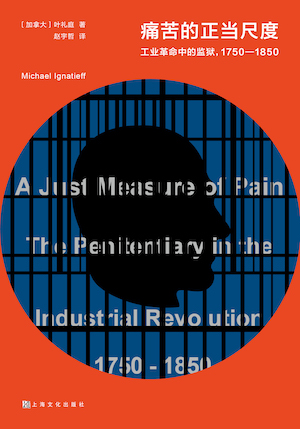
《痛苦的正当尺度:工业革命中的监狱,1750-1850》 [加拿大] 叶礼庭 著赵宇哲 译 三辉图书 | 上海文化出版社 2019年11月
(来源:界面新闻)
 简体中文
简体中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