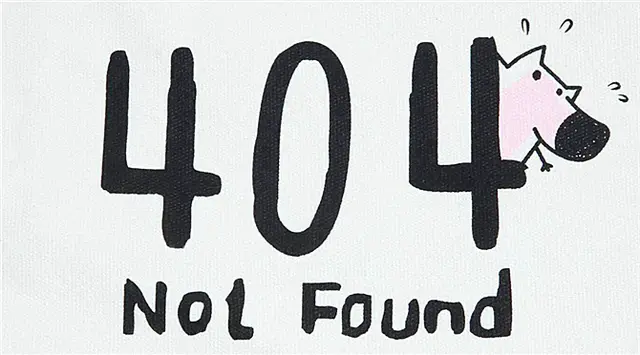文 | 李小飞
被误读的女性生存迷雾
16集的《迷雾》于昨日火爆收官,罪案真凶最终浮出水面。
《迷雾》的火爆在某种程度上与当下韩国社会中敏感的女权议题紧密相关,它不仅作为一种简单流行性文化的渗透,更深切再现了韩国在“后朴槿惠时代”下纷繁变幻的现实时局中对清明政治/绝对正义的原始想象。
在好莱坞金牌制作大佬哈维·温斯坦的性侵丑闻被媒体大肆曝光后,由女星艾丽莎·米兰诺牵头的Metoo运动狂潮瞬时在韩国社会激起浪花——
首先是韩国导演金基德被曝对女演员始终延续着不堪的性侵经历;随后目前正在统营地检就职的女检察官徐志贤在1月29日播出的JTBC新闻节目《news room》中,公开揭露自己曾被检查机关干部性骚扰的事实;当性侵事件逐渐发酵为政治形象灾难时,曾被视为有力问鼎下届韩国总统宝座的政治红人前忠清南道知事安熙正,因卷入性侵丑闻目前正在位于首尔的检查所接受调查……
如果将《迷雾》放置于当前韩国愈演愈烈的对女性权利与身体意识的聚焦潮流中来看的话,剧中所着力刻画的深谙女性生存困境同时又敢于颠覆男性权威的“高慧兰”,实质上展现出当下韩国主流社会对女性形象的一种全新想象。
在这份混杂的想象中,女性不仅“成功”从以男性为主导的权威体系中争夺到话语权(高慧兰在与报道局高层的数次对峙中成功守卫了9点新闻的主播位置),更因过于强硬的处世逻辑屡遭男性权威的无情“惩戒”(丈夫姜太昱因不满妻子冷血选择了长达7年的分局生活;公公更因其卑贱出身闭门不见)。
《迷雾》的成功,正在于将长期悬置于男性窥伺视野中心的女性想象具体化了,当满足在类型片滋养下的观众对“蛇蝎美人”的常规想象同时,也对女性自身性别困境与身份悖谬进行了深刻而细致地揭露。
在《迷雾》最初登陆国内时,高慧兰坚韧决绝的女性形象立刻燃爆了诸多舆论,诸如“吊打国产玛丽苏伪职场剧”、“狠辣的女人,为什么备受时代青睐”等舆论噱头为《迷雾》疯狂贴上了“女性独立”、“女权主义”等有色标签。
在初看剧集过程中,我也的确为该剧标新立异的女性设置所动容,然而随着剧集将近,大结局即将揭示,公众舆论所反复宣扬的“女权主义”、“女性主义”似乎走向了另一种精神复调的极端,这无疑是值得警惕的,正如诸多评论所说:
“女人凭自己的实力选择的人生,没有人有资格说三道四!”
“女人的衣帽间里,不仅装满时尚和品味,更装满了欲望和野心!”
如此粗暴直率的言辞,不仅误读了《迷雾》所试图展现的性别逻辑,更以撒狗血式廉价道德逻辑绑架“女性主义”,使“女性主义”停留在一种对男性秩序权威的反杀与仇视情绪之中,导致《迷雾》在国内公众舆论空间中再度沦为“暗黑职场”的性别指南,更成功激活了化妆服饰的消费热度。
在《迷雾》收官时刻,通过对全剧的梳理或许可以发掘更多信息——《迷雾》试图阐释的是一份潜在的主流逻辑,主流引导的核心旨在“和解”,高慧兰作为女强人的真正价值在于最终卸下强硬姿态,选择与碎裂的家庭和解,与对峙的工作环境和解,与自身的性别困境和解,当一名浑身长满锋芒的女性选择与周遭世界和解并友善融入时,真正的女性意识与身份话语才能分娩,而非借助一种反社会性的性别颠覆逻辑。
“迷雾”的所指也是失陷于性别困境中的女性如何拨开重重迷雾,皈依社会主流价值的蜕变仪式,与同期诸多盈溢着鲜血、暴力的“女性作品”相比,《迷雾》无疑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在接受、认同社会性别逻辑前提下与主流社会实现了潜在融合与同构。
即便是在同属于“大女主”韩剧的《悄悄话》、《傲骨贤妻》中也未曾突围这种“和解”性逻辑,而仅局限于一种想象性的“女性独立”姿态,超越现实空间与性别秩序的“独立”只不过是当前创作者借女性之名的一种空洞的“性别分裂”。
当然,需要指出的是,“和解”绝非妥协与媾和,而旨在宣扬一种身份角色的完整与主体意识的回归。
《迷雾》第14集中,“和解”就被表现得相当细腻生动——在面对公公/男性权威的强势逼问时,高慧兰不但敢于反问,甚至她自身在遭受现实磨难后依旧不变的进取初心首次受到了公公首肯;在面对丈夫姜太昱时,她不再选择“性别分裂”,而是尝试相信丈夫、依赖丈夫,夫妻同心取得了审判最终的胜利,这其间所展示的高慧兰对“儿媳”、“妻子”身份的回归与对女性未来命运的自主掌控意识无疑达成了一种微妙平衡,《迷雾》的成功也意味着韩国社会传统的家庭伦理道德逻辑与现代女性意识间最终达成了一份完满性答案——
真正成功的女性角色是回归于主流秩序,在家庭/职场/生活中成功建构主体存在感与身份意识,也只有当女性主动融入现实性社会空间后,女性才能在遵循秩序时完成自我身份的最终整合。
在谈起《迷雾》时 我们如何重读女性困境?
事实上,“高慧兰”式强权女性走红的原因源于很大程度上改写了我们对现代职场女性的认识局限。在21世纪当下,伴随着女性主体意识的不断崛起以及各式各样女性角色屡屡介入主流媒介空间呼唤一个性别平权时代的降临,如何在影视文化中去重新改写、整合直至最终定义女性形象与我们最终认知当代社会紧密关联。
我们暂且不论以《恋爱先生》、《一路繁花相送》、《谈判官》为首的“伪女性意识”暴露出当下国内文化空间中对女性形象的表述是何等地羸弱与贫瘠,即便在相关女性文化的阐释与延展中也不同程度地陷入了失语困境。
知名女性学者戴锦华在探讨当代中国电影中的女性形象时,曾指出过延伸至现实中的女性生存的三重困境——花木兰式境遇、空洞的能指与欲望凝视的客体,三重困境精准而透彻地辨认出当代女性在遭遇男性秩序宰割后的复杂现状,实质上也宣告了一则令人绝望的事实:女性抗争男权文化的无效,即女性难以在“男权文化的苍穹下创造出另一种语言系统来”。
因此,当性别改写冲动宣告失效后,对男权文化的臣服与无限度地颂扬也就成为当前国内影视创作的主导,我们也就看到了《恋爱先生》里的中产精英程皓所谓的“恋爱专家”的名号,实质上是对女性身体编码排序的一种变相消费,即便《谈判官》中的童薇在职场上与高慧兰一样拥有着果敢决断的主体意识,但富家公子哥谢飞依旧可以仰仗强大资本优势随时侵入童薇的工作时间,甚至左右童薇未来的工作规划。
颇为怪诞的悖谬是,即便《恋爱先生》、《谈判官》此类隐性宣告男性权威的伪女性影像暴露出千疮百孔的叙事逻辑,但观众仍对其抱有高额期待直至将此类作品捧入年度热播剧的“精品”行列。
事实上我们很难将其归咎于观众自身素质与文化水准等问题,毕竟我们现在所依赖的大环境正是一个以男性文化为主流的威权世界,所以由《迷雾》所触发的众多网络评论,由于过度聚焦我国影视文化本身而忽略对现实的精准把握从而失去了批评的真正意义,这也导致了另一重荒诞的文化怪圈:当我们不惜以最大热情去歌颂“高慧兰”这样一个全新女性形象诞生时,我们仍乐此不疲期待《如懿传》、《巴清传》此类为男性权威立传的伪女性之作。
当然,有评论认为,伪女性作品之所以能够在市场上持续热销源于现代社会对女性身体过度消费的热情,影视文化产业的内在逻辑正是基于对身体消费、景观消费的欲望冲动上,这也就解释了为何每当伪女性作品充斥银幕时,女性身体会往往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江疏影的腿、杨幂的发际线),但这也无法完全解释《迷雾》的火爆:
剧中的高慧兰基本上都以男性化的职业套装示人,甚至连青春时代的情欲戏都未曾真正成为我们关注《迷雾》的核心焦点。
所以,当我们在谈起《迷雾》时,国内荧屏所建构起的女性审美经验往往难以奏效,“高慧兰”代表了一种怎样的女性文化?
让我们不妨先回归电视剧本身。在剧中,高慧兰与国内荧屏空间中的职场女性同样遭遇三重困境:
花木兰式境遇——高慧兰作为9点新闻的王牌主持人,面对自始至终的职务危机,她始终以一副强硬的“女汉子”式形象示人,这种对女性自身性别身份的自觉改写正是另一重男性形象的变身,即“女性要获得社会的显现,必须将自己扮演成一个男性才能成功”,而成功的代价即“作为一个女性生命的永远的缺失”;
由此导致高慧兰陷入另一重困境——空洞的能指,在由男性权威主导的复杂的家庭空间中,高慧兰不可避免扮演着一个失语者角色,“妻子”仅仅是一种增殖的身份符号,不仅是创作者本身,连我们观众都必须承认高慧兰的魅力恰恰来源其变身后的男性力量,而非她自身的女性身份。
当然,抛开性别身份去探讨“高慧兰”这一形象显然会重新落入性别陷阱,全剧中高慧兰作为女性身份的现实在于不断沦为街头巷尾公众猎奇、窥视与意淫的焦点,作为女性自身的困境在剧中被反复呈现,甚至成为最终导致凶案爆发的导火索。身为丈夫的姜太昱一旦身处公众空间中,就不断承受各方男性目光对妻子的窥伺与渴求,高慧兰最终沦为“欲望凝视的客体”,夫妻关系持续不和。
在阐释当代女性身份困境的命题上,《迷雾》不仅相当写实与完整,甚至由此探讨出性别困境所导致的身份角色的混乱与失控。
需要指出的是,在很大程度上,《迷雾》中的高慧兰的困境源于其自身角色的失衡与断裂,对主持人社会身份的过度追求导致了妻子/儿媳/母亲角色的必然性牺牲,女性身份的失控不仅加重了性别困境,更加剧了女性身份角色的分裂,女性主体意识遭受瓦解。
所以,在避免对女性意识绝对性赞扬的底线下,《迷雾》实现了当下女性题材新的探索与突破,在13-14集中,高慧兰在家庭/法庭空间中的“弱者”姿态实则完成了双重意义传递:
一方面高慧兰式女性强权角色的诞生对男权文化的秩序压迫进行了强烈批判;
另一方面高慧兰的困境也源于自身身份角色平衡的失控,对任何一种角色的绝对追求都会加剧女性生存危机,所以高慧兰对家庭的回归不仅意味着《迷雾》在峰回路转的权力游戏后对家庭主流价值的回归,更是对当代职场女性的一份深刻洞见与良性警示——所谓的“独立”绝非社会角色追求的最大化,而在于女性对自身多重社会角色的认同与平衡,只有如此,才能真正整合起一份完整的女性独立主体经验,“高慧兰”才能真正脱离困境,实现家庭情感与性别经验的完满融合。
唯物主义女性主义学者艾琳·戴尔蒙德认为,社会性别也是一种实践行为的结果,并不执着于绝对性的女性主体,女性主义的关键在于一种变革性模仿——女性对男性法则的“臣服”并非是一种被同化的性别扭曲过程,而是在模仿男性过程中去等级化、有所突破、并改变原有特征。
变革性模仿理论的提出不仅一举突破了21世纪以来女性主义自我设置的悖论与困局,更为当下我们重新看待“高慧兰”式的强权女性角色提供了一份新的视野:女性身份权力的获得不再局限于单一性抗拒男权社会,或者顺从男权法则,而是在参与男权社会秩序同时最大化地释放女性主体的能动性。
而高慧兰最终对家庭/职场角色的双重回归恰恰验证了女性“变革性模仿”的可能,她完满的回归姿态也成为职场内其他女性的楷模——年轻的主播韩智苑在接过9点新闻接力棒同时,也接受了高慧兰在职场内敢于挑战权威的职业精神,《迷雾》成功激活了当下社会对于职业女性群体的鲜活想象。
新闻的群像 “不变”类型中的“视角”之变
在韩国社会,新闻舆论一直相当活跃且拥有着引导社会主流的隐形权力,但这种权力的获得往往会遭受来自政治、经济多方面的宰制与镇压,甚至为此付出严重的生命代价。因此在韩国,“新闻”不仅仅意味着一份常规性的资讯渠道,更代表着一种决绝的正义精神与质询理念。
所以,除了正面突围当代职场女性的性别困境外,《迷雾》还实现了一种社会学意义上的升级——“高慧兰”所象征的绝对新闻价值的坚守与捍卫,“高慧兰”所代表的也是韩国社会庞大的新闻舆论群体,而她所承载的绝对正义想象也与当下韩国舆论现状紧密相关。
对社会现实的共时捕捉与深刻自反一直是韩国影视文化的“现实主义传统”,对现实的艺术化再现不仅源于长期根植于韩国文化基因中的左翼批判传统,更与80年代金斗焕军事独裁政府逐步走向没落、“民主革命”所带来的舆论解禁潮流具有一脉相承的历史内在联系。
2015年的大尺度现实力作《局内人》直接将批判的背景架构于现实/虚幻叠合的暧昧空间中,片中通过“直露”的隐喻强势攻击了韩国政商勾结的腐朽社会体制——“未来汽车”直指韩国现代汽车集团,随意掌控社会舆论、企图掩饰真相的《祖国日报》对应韩国最大的报业集团《朝鲜日报》,影片上映后不仅迅速刷新了韩国19禁片单的票房纪录,更重新带动了韩国政治电影的观影热潮。
从类型脉络来看,《迷雾》只不过是韩影政治类型题材在小荧屏上的一次延伸与重述,而被众多国内舆论所追捧的“职业感”也源自韩国文化“悠久”的政治传统。当然,这并不能说明中国国内的观众对政治题材不敏感或是排斥,2017年被誉为“十年一剧”的《人民的名义》的超高收视率已然验证了国内对政治题材的强大热情。
当然,受限于国内主流意识空间的长期滤化与紧缩,如何在弹性的政治底线下完成艺术与现实的巧妙平衡在未来仍是亟待国内现实主义题材解答的命题。从题材视野来看,《迷雾》的成功不仅旨在改写了一种全新的女性形象,更关键是韩国创作者实现了“女性意识+政治批判”类型视角的成功嫁接,《迷雾》在本质上仍从属于韩国现实主义题材谱系下的一员,只不过它激活了新一轮的类型期待:
当女性闯入一向以男性权威为主导的社会体系中时,女性身份又将遭遇怎样的删减与改写?在韩国这样一个极其重视性别秩序的传统国家,《迷雾》中试图探讨的“女性参政”议题不仅凸显了当下正处于重组中的女性地位,在更广阔的意义上也为“后朴槿惠时代”历经政治高压后的韩国社会提供了一份清明世界的希望,随着大结局来临,我相信观众已不仅为高慧兰一人所动容,更是为其背后苦苦挣扎的新闻群体所震撼,“迷雾”的真正谜底在于以求真精神拨开腐朽雾障,实现韩国社会的清明政局。
有意思的是,在《迷雾》收官时刻,韩国检方已于19日提请法院批准逮捕前总统李明博,这也再度重蹈了从李承晚到卢武铉永恒萦绕于韩国总统们的“宿命梦魇”,在文在寅政府主政的当下,韩朝两国实现半岛政治的历史性突破,国内政治遗债开始大规模清算,这是否又是“迷雾”驱散、“绝对正义”重启的开始?
(来源:界面新闻)
 简体中文
简体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