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3年,拿破仑三世刚刚登基称帝,他把一个名叫乔治-欧仁·奥斯曼(Georges-Eugène Haussmann)的地方官员拉进了自己的办公室,并在此人面前展开了一张巴黎地图,命其美化法国这个熙熙攘攘的首都各个行政区中污秽邋遢的角落。在接下来的17年间,奥斯曼这个自封的男爵及“艺术家兼破坏家”在密集的手工坊和住宅之间大胆地开辟了一条条道路,让这座城市拥有了工业化帝国的辉煌。
但奥斯曼著名的城市规划方案的核心不仅限于修复市容,他把“人口控制”也放在了重要的位置。由于居住空间狭小,而且总与老鼠和垃圾污水为伴,巴黎人心底的不满和反叛情绪一直在骚动:1789年法国大革命后的数次暴乱、1830的七月革命(奥斯曼本人在打斗中被俘,并发现自己对下层社会充满厌恶)都可为此佐证。1848年2月,巴黎爆发革命,七月王朝覆灭,拿破仑三世上台。居住在破败、拥挤街区人们的积怨和不满愈发高涨。这些人比邻而居,一同忍受着狭小的空间,而且都穷困潦倒,这就是暴乱的种子。在耳边响起的警铃更能让人留心,同理,在狭窄的街道上建筑壁垒更加容易。
奥斯曼监督了这些街区的拆除过程,当地的居民被暂时迁居外围。如果叛乱再度爆发(比如1871年的巴黎公社运动),那么新的巴黎街道和广场可以为镇压军队的集合和调动提供完美的场地。

巴黎俯视图。中心区域源于奥斯曼的重新设计。图片来源:DigitalGlobe/Rex
无论是否出于有意,从那以后,相同的操作一次又一次地上演:郊区城市化和都市生活的社会原子化(social atomization,指由于人类社会中间组织的解体或缺失而产生的个体孤独、道德解组、人际疏离、社会失范的社会危机)不断推进,人与人之间也从惯常的亲密向保持距离稳步转变。西方世界(东半球和南半球后来也快步跟上)的一家家旅店拔地而起,但同时人们得通过要么荒无人烟,要么堵得水泄不通的交通要道,才能到达一座大都市及其卫星城的其他角落。仓储式商店和各色连锁店把人们熟悉的家庭经营小店和工作坊挤出了主要街道。科技取代了工厂里的工人,或者把他们赶到了我们视线范围之外的地方;办公室里的隔板被拆除,员工由此变得容易分心和偏执,而不是像某些人自诩的“这样有益于创新”。就连我们贫乏的娱乐活动,也大多在手提电脑的微光下进行,光顾大剧院和惬意的电影院的人少之又少。
某种层面上,当前的疫情加速了一直以来的一些趋势:人们越来越倾向于与人群隔离,越来越安于藏在防风玻璃和口罩、窗帘后面的隐居生活。这些改变不需要来自奥斯曼或者权力机关的指示,社会观念的转变和社会压力就足以使之形成。想想以前办公室员工视若珍宝的一小时午间休息时间吧,今天的他们每时每刻都得待在办公桌前,为着二十或三十分钟的休息时间讨价还价。
“社区”(这个“术语”老被专家滥用)不再作为环境的一种有机产品而存在。市政厅、理发店、咖啡厅、清真寺、集市等等——这些曾经的整个街坊的中心已经变成了仅仅供人们聚集的场所。在这样的世界里,传统已经分崩离析。我们加入联盟、出席家长会、参加宗教集会、与家人同居一室的热情越来越低。最可悲的是,我们性生活的频率甚至也在降低。
在前厅、合租公寓、操场护栏和安静的地铁通勤之外,当代生活的本质让人感到愈发无情和由内而外的空虚。这对我们来说不是什么生死攸关的灾难,只是一种不断扩散的、弥漫在四周的焦虑情绪。这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作家巴拉德、德里罗、大卫·米切尔和库尔特·冯内古特近几十年来都表达过对这种现象的忧虑——但现在的情况更糟了。最后,我们生活在了奥斯曼已隐约干涸的美好理想中。人已经变成了一座岛屿,一片孤独的群岛。正如明智的诺瑞娜·赫兹在她的新书《孤独的世纪:在一个正在分崩离析的世界中聚集在一起》( The Lonely Century: Coming Together in a World that’s Pulling Apart )标题中所说,我们生活在一个孤独的世纪。
赫兹的前几个章节笔法巧妙地探讨了大量的研究、试验、调查和实验,它们都指向了同一个方向:感到被爱、拥有目标、与世界相联能让我们更健康、更高效、更能抵御疾病和衰老的侵袭。
可是,在日本,越来越多的老年女性故意犯下微不足道的罪行,以跟同龄人成为狱友。机器人市场已呈井喷之势,当代约会市场雷区遍布,人们有许多欲望无法得到满足,因此能够满足这些愿望的机器人尤其受到青睐。在纽约,你可以雇佣一个大学生做你的朋友——价格是40美元/小时。互联网集聚和加剧了社会失范(anomie)现象,尤其是对于某些青少年而言——他们很容易因为自己的生活远比不上偶像明星的晶莹纯粹而忧思过度。Facebook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公共健康问题。单人份即食食品的销量近年一飞冲天——这对那些每天在家进行“吃播”的网红而言可谓再好不过。
更重要的是,在一次盖洛普民意调查中,来自155个国家的85%的员工认为,自己与公司和所做的工作是脱节的。这个信息跟舆观调查网(YouGov)的一次民意测验结论相互呼应——已逝的人类学家大卫·格雷伯曾把这个结论作为理论支撑放在了他的犀利作品《狗屁工作》中:50%的英国工作者不知道自己的工作对世界有没有价值,而37%的人“非常肯定没有价值”。
但《孤独的世纪》这本书并没有结合大量数据和史实来说明“孤独”变得越来越普遍的过程:书名中的“世纪”指的是过去二十年,而不是一百年。赫兹依然做着许多走“第三条道路”(Third Way,指调和右翼和左翼的政治,类似于中间主义的政治哲学和政治立场)和身处政治研究所的知识分子兼政策研究者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开始做的事情(而且已经小有成效):他们的语调平易近人、亲切友好,他们做出了凌驾于“党派政治”之上的尝试,他们还居高临下地提出了能想到的一切能解决“问题”的“方法”,这些方法通常跟试图拯救资本主义本身相关。
赫兹笔下的恶人、这个不安时代的罪魁祸首是充斥着利己主义、竞争主义和自相残杀冲动的新自由主义。赫兹认为,这种新自由主义大约40年前就开始从企业向人群渗透。这使得她可以呼吁政府或市场来减轻人们孤独的症状,而并不考虑危机的根源。“是时候作出扭转局势的激进决定了,”她宣布,但她的结语既没有扭转局势之意,也毫不激进。“是时候贯彻一种更有爱心、更加仁慈的资本主义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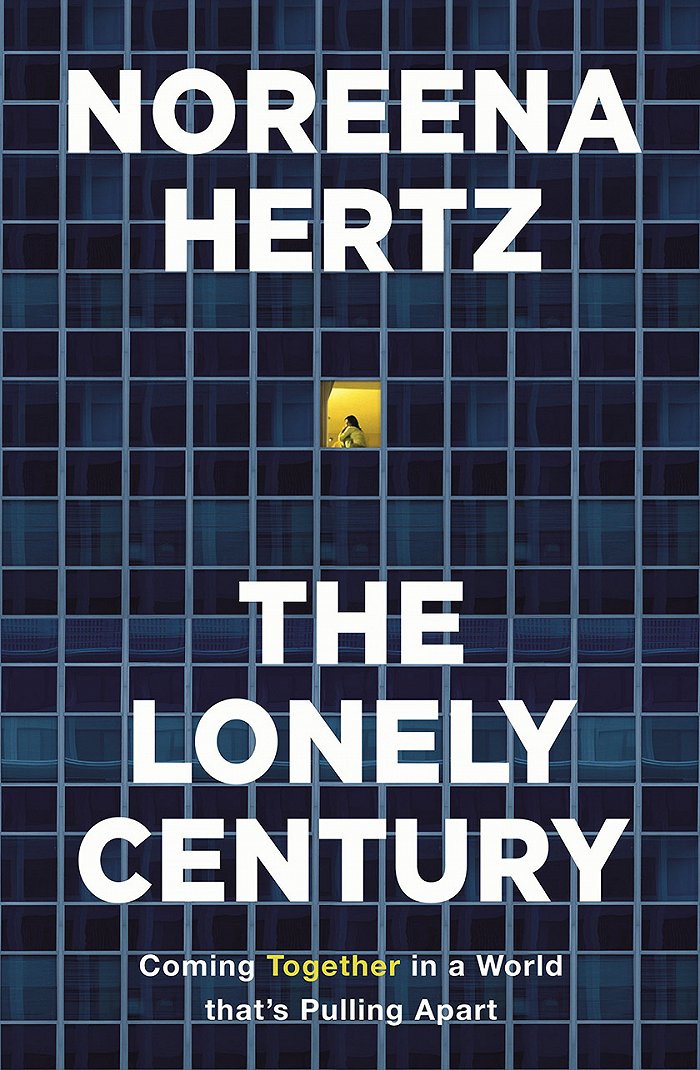
《孤独的世纪:在一个正在分崩离析的世界中聚集在一起》
诺瑞娜·赫兹 著
如果我们无动于衷,长期孤独的人将会有爆发的倾向,赫兹说。她笔下的右翼民粹主义和种族主义思想之所以在欧洲和美国愈演愈烈,本质上是在试图从这个越来越不友善的社会中挽回一些意义。想想右翼人士利用社会主义和工会的老策略来创造社区美好愿景的方式吧:西班牙极右翼政党Vox主办仅限年轻人参加的啤酒之夜;特朗普的集会是带有威权色彩的野餐;意大利的北方联盟政党(Lega Nord)会举办强调地域传统的晚宴和派对——这些集会产生的情感共鸣会被他们写到社交媒体的宣传语中。当然,这些团体已经无数次证明,他们擅长把真实的目的隐藏在与家庭和关怀相关的口号背后。汇丰银行自称“世界的本土银行”(world's local bank);美国保险公司巨头State Farm渴望成为“你的好邻居”(a good neighbour);英国John Lewis百货商店每年的温情风圣诞广告再怎么精彩,本质上也不过只是个百货商店的广告而已。
不管怎么说,在描述这些政治后果时,赫兹尝试指出的根本不是孤独,而是一种更深层次的痛苦。这个词在她的书中只出现了寥寥几次,但它也背负着深重的历史:疏离感(alienation)。
“孤独”指的是我们与他人之间保持实际距离的一种状态,而“疏离感”的意思则是,对整个世界而言,我们的存在似乎是毫无意义的。它是一种心理上的隔绝,是一种把我们的自我价值感跟我们继承的贫乏资产分离开来的心理状态。流行文化不再吸引我们,政治对话离我们的日常生活也越来越远。工作中,很少人能真正有产出。于是,我们转而投向服务业:做酒保、做快餐店店员,做网约车司机、做电话销售员、做公关宣传员,或是官僚政治的走卒。通往更加绚烂的未来的大门已经关闭,而“疏离感”源于这种能力的缺失——我们一同把手指放在公平的天平上的能力。
当然,这也不是新鲜事了。今天的我们虽然在向可与维多利亚时期相“媲美”的不平等社会迈进,但不妨想想数百年前通过反抗运动来冲破“疏离感”牢笼的巴黎人(以及其他地区的反叛者),后来奥斯曼被召入宫,缓解了叛军的问题,同时,一大批哲学家也投身于研究(甚至是试着减轻)这大片弥漫的死气沉沉和同质化的情绪——包括克尔凯郭尔(Kierkegaard)和费尔巴哈在内的众多哲学家都认为,人道主义一直是这个问题的一条出路,是通往解脱的一种尝试。
《孤独的世纪》这本书中并没有提到上述姓名。但是,赫兹欣喜地提出建议,呼吁我们为老年人购买机器人以辅助他们看电视消遣娱乐,而不是只知道想象一个老年人不必孤独度过生命最后时日的社会。我们被告知应该从赫兹这样的聪明人身上汲取智慧,但却发现他们打开的可能性窗口如此狭小,还忍受着如此匮乏的想象力,这也许才是最让人疏离感顿生的事情。
(翻译:黄婧思)
 简体中文
简体中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