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可能少读文学评论,”里尔克提醒19岁的军校学员弗朗茨·夏弗·卡卜斯(Franz Xaver Kappus),卡卜斯是《给青年诗人的信》的收信人。“艺术作品是无限的孤独,”里尔克接着说,“没有什么方法比批评更无用了。”里尔克用自己的真名给作品署名,不像埃琳娜·费兰特(Elena Ferrante)在匿名的情况下,试图把她本人从作家的形象中解脱出来——她正是里尔克所说的,在“无限孤独”中工作的天才。当《巴黎评论》问她“保持低调的原因”时,费兰特解释说,她想摆脱公众(以及媒体)对作家作为单一创作声音的迷恋。“文学作品,”她强调,“都是传统、多种技能和集体智慧的结晶。”
埃琳娜·费兰特的小说,特别是“那不勒斯四部曲”(《我的天才女友》《新名字的故事》《离开的,留下的》以及《失踪的孩子》)正反映了这种集体能力。四部曲记录了莉拉和埃莱娜之间激烈竞争而又相互依存的友谊,这两个出生于战后那不勒斯的女孩在贫穷和暴力中长大,却在彼此身上找到了避难所。二人的纠葛故事由埃莱娜讲述,在她们的一生中,两名女性的思想和印象重叠、融合在一起,尽管她们的性格截然不同(莉拉扮演无畏的、渴望生活的角色,成为埃莱娜教科书般的内敛的陪衬),但我们不清楚一个声音在哪里结束,另一个声音在哪里开始。成长为小说家的埃莱娜意识到,她写的每一件事,她所有作为作者的作品,都源于她与莉拉的关系和莉拉灌输给她的创作本能。她忧心忡忡地想:“如果没有她,我知道怎么想象那些事情吗?我还会知道如何赋予每一个物体生命,让它们与我自己保持统一吗?
一本名为《费兰特书信:集体批评实验》的新书,试图抓住费兰特作品中的这一元素,对文学批评采取类似的集体批评方式。四位年轻的学者、评论家:萨拉·奇哈亚、默维·埃姆雷、凯瑟琳·希尔和吉尔·理查兹集体汇编了她们关于“那不勒斯四部曲”的书信往来。这也是一项与费兰特的目的一致的调查,为了研究如何最好地表现写作中关于文化的“集体智慧”。正如他们在共同撰写的导言《集体批评》中所解释的,四人希望将其与朋友、家人和同事之间关于文学、电视和电影的非正式对话放上台面:“我们的目标是将‘团结’写作的内容正规化,这与一个词一个词写作一样,同样是一种写作的劳动输出。”
在针对应该关注哪位作家进行了一番争论之后,奇哈亚、埃姆雷、希尔和理查兹选择了费兰特,因为这位意大利作家致力于展示女性之间的智力交流。在《离开的,留下的》一书中,埃莱娜说:“女性心灵的孤独是令人遗憾的。”《费兰特书信》引用了这句话,并将其作为贯穿全书的主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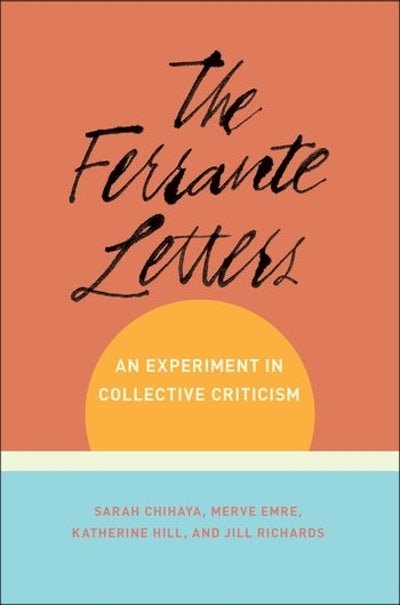
《费兰特书信》
这些作者们习惯了独自创作,也表达了对这种合作的一些担忧:“如果我们得出的想法完全一致怎么办?我们要如何区分我们作为作者的声音?”她们提出这些问题,但意识到这正是费兰特在她对埃莱娜和莉拉关系的描述中所探索的。“埃莱娜和莉拉用不同的方式表达了同样的恐惧:任何一种亲密关系都不可避免地伴随着对伤害和相互依赖的恐惧。”如何让他人影响你、塑造你的想法,同时保持你的自主权,是费兰特笔下的小说和《费兰特书信》的中心主题之一。这四位评论家都是学术界的年轻女性,而集体写作面临着职业贬值的风险:“那种会让我们分割成一个个单一实体的合作,不能保持活跃的差异感和个性,似乎既不自然也无成效。”她们想知道,既然女性的声音经常被淹没或是完全沉默,那么女性是否可以集体分享舞台?或者在这种情况下,集体分享一个署名?
埃莱娜思考自己在文学上对莱拉的亏欠时,同样关注这些问题。虽然“那不勒斯四部曲”是从成长为作家的埃莱娜的角度来讲述的,但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了解到,她可以接触到莉拉在笔记本中写下的同样的故事。吉尔·理查兹写道,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那不勒斯四部曲“是关于困惑”的。她解释说,四部曲“一直在戏剧化地阅读和撰写他者故事的场景”。埃莱娜把莉拉的笔记本扔进河里,而随后,她痴迷地用自己的语言记录那些被毁掉的文字。虽然埃莱娜是职业作家,但莉拉是第一个尝试小说创作的人,她在小学时写了一本名为《蓝色仙女》的小书。成年后,埃莱娜很高兴地看到了莉拉的原版故事,但她怀旧的喜悦是短暂的。“从第一页开始,”她写道,“我就开始觉得胃不舒服,很快就满身是汗。然而直到最后我才承认,我刚读几行后就理解了一件事,莱拉幼稚的文字是我作品的秘密核心。”
对才能互相影响的恐惧和担忧萦绕在《费兰特书信》中,使得书中的批评罕见地以惊人的准确性反映了它的原材料。

《我的天才女友》
[意]埃莱娜·费兰特 著 陈英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7-1
虽然《费兰特书信》的作者们一开始就解释说,他们的集体批评项目是为了让“团结的写作”发自内心,但在阅读信件(和其他文章)的过程中,我们才意识到这种写作是多么粗糙和不舒服,特别是对于那些希望在世界上留下自己独特印记的雄心勃勃的女性来说。萨拉·奇哈亚写道:
事实上,这四位作家都提到了费兰特小说中反复出现的一个主题,那就是莉拉对人与物之间界线消散的焦虑。费兰特写道,在这些类似攻击的场景中,莱拉会变得恶心,她心跳加速,“人物和事物的轮廓突然消失了。”如果《费兰特书信》是一场实验,让我们看到文学批评的边界、形式和形状消失、批评家的观点相互模糊的结果,那么作者们认为这种可能性既令人兴奋,也令人恐惧。奇哈亚问道,有没有“一种方法既能消除边界,又不会屈服于疯狂或自我毁灭的诱惑”?
然而,作者们并不完全同意自我毁灭的吸引力。这在他们对“那不勒斯四部曲”故事框架的看法上表现得最明显。《我的天才女友》以现年66岁的莉拉失踪开场。当其他人担心悲剧发生时,埃莱娜意识到,她的朋友终于实现了一个长期的愿望——消失,甚至没有留下任何她曾经存在的痕迹。埃莱娜对莉拉的遗弃感到愤怒,为了报复,她决定写下莉拉的故事:“我们看看这次谁会赢。”这种通过书面文字记录、保存和致敬的冲动,无疑吸引了《费兰特书信》的作者们,这一点对埃姆雷、希尔和理查兹来说尤其明显。然而,奇哈亚发现“从未经历过”的想法很诱人:“我从来没有读过如此清楚地表达这种奇怪而独特的欲望的文字。”奇哈亚做出这样的评价有一丝讽刺的意味,因为她在《费兰特书信》里分享了最多关于自己的信息,包括费兰特的小说迫使她面对过去的创伤(包括试图自杀造成的身体创伤)。读到她认同莱拉的欲望后,我想知道,(通过合作或其他方式)消失的愿望是不是世界上那些最活在当下的人,能够更强烈地感受到的。
在传统的纸质媒体中几乎很少见到联合撰写的评论,尽管像播客这样的新形式已经出现了不少致力于基于讨论的文化批评节目:《纽约时报》的“Still Processing”、NPR的“Pop Culture Happy Hour”、“The Read”、Slate的“Culture Gabfest”等等。然而,评论家们仍然没有什么地方来以书面形式记录下构成我们观点的无数对话、短信、笑话、私信、偷听、推特上看到的信息。《费兰特书信》虽然聚焦于一位作家,但通过这种方式,这本书也提出了关于批评的更广泛的问题,并对我们是否可以独自完成所有工作提出了疑问……也许只有大学教授才能真正做到这一点。
(翻译:李思璟)
 简体中文
简体中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