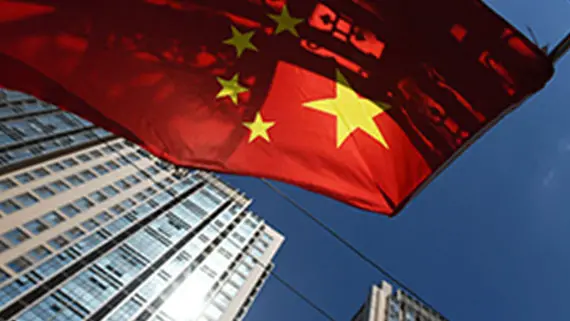按:“海有许多许多声音,海有许多许多种。”T.S.艾略特的诗句激发了世人对于大海的无穷想象。人类的世界毗邻着大海,可是我们又往往对其知之甚少。
美国作家乔纳森·怀特 (Jonathan White),同时又是一位航海家、冲浪运动员、海洋环境保护者。他成长于南加州海滩,对海洋有着异乎寻常的热爱,曾自己造船扬帆远航11年,在太平洋与大西洋航行里程超过几十万公里。
在与大海朝夕相处的时光里,怀特对这个庞然大物逐渐有了更多了解。在《潮汐》一书里,他爬梳了人类文明与海洋律动相依相存的历史演进,呈现了引人深思的科学研究。
牛顿的死亡面具、钱塘江奔涌的大潮、阿拉斯加搁浅的帆船、在海浪中伫立千年的圣米歇尔山修道院、被急流延滞的地球转速、让人心跳的世界级冲浪、潜力巨大的潮汐能……通过丰富的旅行记事,怀特用诗意的笔调,探索着海洋研究中神学向科学的嬗变、天文对水文的牵引、物理与地理的叠加。
从《潮汐》中节选了部分章节,与大家分享大海的诗意浪漫。
深海执迷(节选)
**文
| 【美】乔纳森·怀特
译 | 丁莉**
直到牛顿引入万有引力及完整的天体运行原理,过去的人们基本上是根据传说、占星术、实地观察和宗教信仰而提出潮汐理论的。他们就着所能掌握的理论工具来解释这个世界,这一点和今天的我们并无二致。
新西兰的原住民毛利人相信,月亮里住着一位女神,而潮汐的涨落皆在其一念之间。中国人视银河为一架巨型水车,水轮翻转间,便填满或抽干海洋。许多不同文化中的人都能感知到潮汐与人类生活之间有种“神秘的协奏”——潮涨而生机勃勃、欣欣向荣,是孕育和出生的季节,是制造黄油、播种三叶草的时机;潮落则忧郁感伤,是收割和凋敝的日子。女子的经期循环好似潮汐在其体内的起落。
钱塘涌潮向上游推进
潮汐悠长而平缓的吞吐是生命体的象征。有人说潮汐是大地女神盖亚的呼吸,也有人怀疑它是头巨兽。列奥纳多·达·芬奇尤其相信第二种,并为此而竭力去测量这头巨兽的肺活量。
无论人们如何揣测潮汐的起因,或是它与人类生活有怎样的神秘协奏,早期沿海居民必然积累了大量关于潮汐每日、每周、每月及每年涨退模型的知识经验。这些经验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关键,是判断何时何地在潮间带捡贻贝、摘海草,何时出海,以及如何巧用潮水的依据。你可以试试不按照潮水规律行事,但绝不会有下次。就现实角度而言,无论潮汐是由水车引起的,还是什么巨兽或女神,这些都无所谓。重点是,只要你观察潮汐并对之合理利用而不是反其道而行,你的生活就会容易很多你了解得越多越好。
所有沿海居民都深谙此道,那些位于极端环境中的独木舟文明尤其如此——比如南美洲南端的火地岛、北极地区,或者北美洲北部沿海地区。这些地区多的是高涌的潮水、凶猛的浪涛、寒冷的海水,冷酷而无情。满载着鱼贝的独木舟稍有行差踏错,便可能酿成悲剧。几千年来,人们通过故事,还有手把手的教导将这些经验一代代流传下来。其中许多,今日已无文字可考。
几年前,我和卢卡斯·奈帕卢克(Lukasi Nappaaluk)一起打猎时,初次领略到这种口耳相传的经验的精妙——卢卡斯是加拿大魁北克北部努纳维克(Nunavik)地区一位因纽特长老。我们徒步穿过了苔原,准备前往哈德孙海峡,然后在那里行船。快到海岸时,我猜测潮水大概处于半潮位。
“在涨潮。”卢卡斯说。
海滩很平静,我完全看不出任何涨潮或退潮的迹象。
“你怎么知道?”我问道。
“雾气。”他说。
他没打算多说,但我继续追问道,“什么雾气?”
“涨潮时,潮水从海滩带走灰尘、花粉和幼虫,它们会漂浮于水面上,像毯子一样。但退潮时,就不会这样。”
对于卢卡斯而言,雾气会告诉他潮水的移动方向、移动速度和时长;告诉他什么时候可以出船,该走哪条航道;告诉他是应该绕过芳堤娜角去猎取海豹,还是去海王星角捕捉鲑鱼。
今天,我开车的时候注意到我所住的海岛周边雾气萦绕。夕阳之下,它仿佛天鹅绒一样。
格雷格•朗恩挑战托多斯桑托斯巨浪时的浪底转向
不分昼夜地,潮汐起伏于世界各地的海岸线——将近60万千米的海岸线。有些地方潮差较小,如地中海地区、墨西哥湾和南太平洋群岛;有些地方潮差较大,如澳大利亚西北部、巴塔哥尼亚地区、英国和加拿大东北部。无论大小,潮汐始终处于运动之中,向某个海岸涌涨而于另一个海岸回落。无始无终。
落笔间,我不禁想象世界各地的潮汐此刻会是什么模样。在我的驻地,潮水正处于低位,牡蛎养殖者尼克·琼斯和他的团队正在潮滩上忙碌,修补牡蛎苗床、放置牡蛎卵以及收获牡蛎以供出售。他从潮间带拽起麻布袋的同时,苏里南的栖息地里,一只大苍鹭正抬起它蓝黑色的身体,尖叫着向海岸飞去。它的目的地在视线所及的几千米之外,但内置生物钟告诉它潮位正低,贻贝、海胆和螃蟹都在等着它去美餐一顿。海藻覆盖的石头上,苍鹭刚落脚,大卫·普伦科特就围上了白色围裙,打开了伊灵潮汐磨坊(Eling Tide Mill)的水闸——它位于伦敦南部。不一会儿,这座16世纪的、世上最古老的磨坊,在嘎吱声中开始运转,暖黄色的面粉从砂轮间飞撒而出。之后,潮位变低,砂轮复归平静,全麦面粉也即将被运送至托顿和比特内的面包房,然后做成饼干和面包。
烤箱内烤着饼干的当头,卢卡斯·奈帕卢克或许刚在北极的冰上凿出了一个口,正准备跳进子宫一样的窟窿里——某个最低潮所留下的窟窿。在那冰块覆盖的黑窟窿里,他可以捕获到新鲜的紫贻贝当晚餐。
千万里之外,意大利的威尼斯,一对年轻夫妇正坐在一张小桌旁,十指紧扣。暮光渐弱,圣马可广场的夜空慢慢升起了一轮明月,他们彼此含情脉脉。这种浪漫场景并不值得大惊小怪,只是这对夫妇所坐的椅子有40厘米没入海水里。在威尼斯,这是“涨水”现象。高潮跃过了防波堤,淹没了圣马可广场。这种现象几百年来间或发生,但近年来随着海平面的上升而更为频繁——2015年就涨水了100次左右。尽管这些涨水带来了严重的威胁,威尼斯人却早已习以为常。游客们在架高的木板上行走,或穿着橡胶靴子购物。年轻夫妇还可以点一杯卡布奇诺,但服务员送餐时可能就是穿着下水裤了。
游人行走在威尼斯圣马可广场的栈道上
涨水现象或许不能为威尼斯的浪漫增光添色,但一轮圆月绝对可以。月色如此明媚,凝视之下,谁不为此浮想联翩?难怪我们的先祖视之为母亲、父亲、神、死亡和新生。在科学揭开其神秘面纱之前,他们深知月亮与潮汐紧密相连,彼此牵引着升与降、盈与亏、消亡与重生。
在不久的过去,一些文化通过音乐演奏和对月而舞来庆祝生育、成熟和爱。今日的月亮和那时并无二致,它提醒着我们所经历的过往。一百年前,叶芝写道:
你到底藏着什么,月亮!
竟如此撼动我的心房?
今日的月亮或许会拨动我们的心弦,但她最初的爱人是海洋,是几百万年之前就开始的牵挂。它们之间的引力随着时间时弱时强,但这份爱却从未终结。如同所有的恋情,它也是坎坷遍布、错综复杂。月亮以重力的形式向地球的海洋发出召唤,海洋回应着,涌动的脉搏将月亮拉近的同时又将其推远。这是宇宙的舞蹈,只是舞者彼此间隔着千万里的距离。它赋予远异地恋新的含义,而且,以人类的视角来看,这舞蹈无起始,亦无终了。
《潮汐:宇宙星辰掀起的波澜与奇观》【美】乔纳森·怀特 著 丁莉 译
新桐·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8年1月
(来源:界面新闻)
 简体中文
简体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