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姆·奥利弗是雷丁大学教授,在那里他带领着一个生态学与演化研究团队。他是一名杰出的系统思想家,同时为英国政府与欧洲环境署提供建议。《自我的错觉》(The Self Delusion)是他的第一本著作。
为什么你会认为,自洽的个体自我这种观念是一种幻觉?
汤姆·奥利弗: 关于自我身份的幻觉首次出现在史前时代,因为对作为种群的我们来说,这种观念是有益的:它使我们有连贯的记忆,便于我们寻找食物,或者保持群体内的社交。在那个时候,一个典型的族群大概会有10-50人。这就意味着,过度的个体主义可能会有问题,这可能会导致他被驱逐出族群,甚至会威胁到个体生存,所以在集体合作中存在着制衡。
到了现代世界,发生了什么变化呢?
汤姆·奥利弗: 我们现在有一种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我们的经济已经变得全球化,但我们的道德和法律框架却还没有跟上步伐。我们的文化以个人主义行为为傲,这种自私导致了环境恶化、气候变暖以及一大堆社会与环境问题。
声称个体并不存在,这不会显得太绝望吗?
汤姆·奥利弗: 事实上,我发现它反而更能予人力量:特别是这一点——你并不是小小城堡内的孤独个体。你可以从多种角度来看待。首先,从宗教的角度说:我们是比我们伟大得多的某个存在的一部分。这就是合一性与泛神论的观念。
其次还有心理学的角度:我们的文化是与每个人共享的,我们是在几个世纪以来积累的大量共享知识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最后则是物质主义的角度:细胞是由环境中的物质构成的。比如说,我们的DNA指导着身体的构成,但这个DNA却是从我们祖先那里借来的。

汤姆·奥利弗
你探讨进化血缘,并质疑线性的达尔文理论。
汤姆·奥利弗: 有个词叫“演化树”。这是一个非常强有力的类比——但是“树”的尖端却使人联想到分离,标示出不同的种群。然而,有大量证据表明,在水平方向上,存在着横跨演化树各个枝节的联结,正如垂直方向的联结那样。这就在演化树的尖端创造了相互连接。比如,就拿关于细菌的种类这一观念来说,这种观念其实并没有真正的意义,因为细菌一直以不同的方式共享着它们的基因。所以,不管你在树的何处,这些联结都会形成网络,而不是树状。
你同样认为“自我”是一种幻觉。
汤姆·奥利弗: 很多宗教论证这一点已经几个世代了。但是我所提出的,是一种基于证据的证明途径。神经科学研究显示,我们的神经系统是非常有活力的:它总是根据我们身处的物理和社会环境而不断变化。每当我们与某人交谈,我们接收的每个字句、每次触摸,都在改变我们大脑中的神经网络。神经科学现在可以得知人类每分钟获取或失去的突触连接的数量,以及大脑是如何改变自己以适应环境的。当我们互动时,我们确实是在字面意义上“改变他人的心智”。这与那种认为自我是严谨的自治实体的观念相冲突。许多这类影响都是潜意识的。因此,对你所处的环境保持知觉,对于影响你的思维是比较有帮助的。
那你如何看待使用致幻剂(例如LSD或者墨司卡林)消解自我意识的现象呢?
汤姆·奥利弗: 大脑会被固定在模式之中。一旦发生,大脑就很难从思维定式中挣脱出来,因为它的路径是被物理编码的。那些药物能帮助大脑暂时打破常规,并提高我们改变思维定式的能力。思考自我也存在不同的方式。当你回到那种状态时,你会意识到你思考的方式也是一种选择,它并不是强加于你的。当你服药时,你会短暂地发现存在其他思考的方式,然后你就可以做出改变。
在你的理论中,意识处于什么位置?
汤姆·奥利弗: 我并不定义意识的存在。我们所拥有的主观感受存在于大脑中的物理结构,它们并不是幻觉,它们有着物理基础,并且是有价值的。我并不是主张我们脑袋里所有的想法都不存在。但是那种观念:我们分离并独立于世界上的其他事物,是一种幻觉。当我们开始承认这种连接,我们会发现我们的意识是有渗透性的,并且与我们的身体有着实体性的连接。这就揭示出一种与地球万物以及宇宙的合一性。打破这种幻觉,可以解锁创造性。当我们感觉孤立的时候,我们就将自己封闭在这些灵感源泉之外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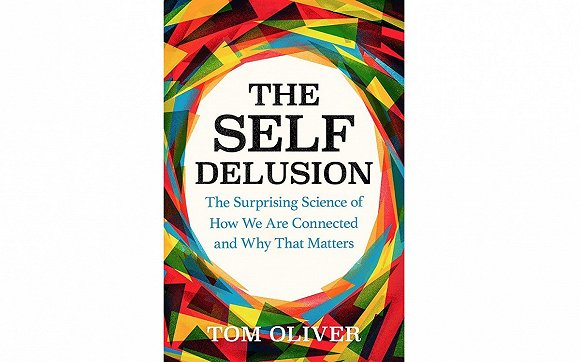
《自我的幻觉》
那自由意志呢,你相信它存在吗?
汤姆·奥利弗: 自由意志问题比较棘手。最合乎逻辑的论证是,我们并没有自由意志。但是我们感觉我们有。我在哲学论证中并没有找到十分有用的东西。很多时候只是把人绕进圈子里。
我们来举一个极端的例子吧:有人朝着人群开枪射击。凶手有自由意志吗?
汤姆·奥利弗: 大多数人的第一反应是,把凶手关进监狱。但是当你解构这种暴力行为时,或许你会看见某种物理原因。大脑中的肿瘤会导致暴力行为,可能凶手在童年期遭受过虐待——这会导致大脑的物理性改变。接下来你一定会问:凶手该承担多少罪责?如果你相信他是自治的,那么谴责个人的结论就很容易得出。但是当你意识到他们是一个更庞大的网络的一部分,你会看到他们的行动是由多种因素导致的。理解了因果关系的全部复杂性,就抛却了追责问题。
你的著作关注个人与社会集体之间的关系。
汤姆·奥利弗: 看看我们面临的巨大的全球性问题吧,例如生物多样性与气候变化。它们的根源是选择与身份:我们选择购买什么东西,或者我们选择如何出行。但当人们与大过自身的东西相连接时,他们会产生一种强烈的身份感。因此机构、经济体、司法系统构成了我们共同的世界观。要改变这一切,我们就需要改变这些思维定式。这也向我们提示了,解决方法就在我们之中,社会变革也会很快发生。
在新冠疫情之后,人们是会转向集体呢,还是更加偏向个人利益?
汤姆·奥利弗: 英国和全球社会正处于一个十字路口。这场危机对每一个人的影响并不平等。一方面,我们会变得更合作、更具集体性。因为人们已经看到,当社会没有照顾好最弱势的群体时,个人主义真的已经走得太远了。但还有一种担忧的倾向,就是这场疫情会因为更加威权的政府,将我们推入个人主义的路途。
当社会受到环境或变化的冲击时往往会退缩,并在内部群体中变得更加紧密。当每个人都说“我们要照顾好自己”时候,问题就来了。这基本行不通,因为从根本上来说,我们是与环境紧密相连的。我们已经在气候变化导致的难民事件中见识到这一点了,而这只是更大趋势的一个开始:我们可能会目睹数以百万计人口的全球大迁移,我们没法简单地封锁边境。这会成为一个伦理定时炸弹。
我们可以将疫情视作一场有创造性的破坏,指出我们在物理和社会层面相互连接的程度,以及建立一个总体更加进步的社会,融合这两种方式,我们就有机会恢复。
(翻译:马元西)
 简体中文
简体中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