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克兰大学荣誉退休教授巴里·瑞(Barry Reay)致力于研究性与性别的历史。他的新书《跨性别美国:反历史》( Trans America:A Counter History )探讨了跨性别者的过去和现在,从19世纪的前史、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属于跨性别者的时刻,到90年代的跨性别转变,再到当前文化的所谓转折点,内容丰富而多样。
跨性别历史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巴里·瑞: 1949年,跨性别者首次被命名为Transexualis。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transsexuality一词变得更加广为人知。20世纪90年代使用的是transgender一词,最近更流行的是trans或trans*。
从表面上看,这是一段短暂的历史。但是,跨性别者无疑也有前史。显然,过去有一些人对他们指定的性别(出生时指定的性别)感到不安,并努力适应我们今天所说的“真正的自我”。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之前,人们确实在思考他们的身体结构以及改变(或调和)他们身体结构的可能性。有些人致力于以“另一个”性别的身份出现或生活,或者实际上他们觉得/知道自己是该性别的成员。使这一切复杂化的是,这些早期的跨性别倾向,至少在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通常被认定为同性欲望,是同性恋的一种。
我从19世纪开始写我的故事,以展示和探索这一前史时期。不过,我其实可以从更早的时代写起。我的主要观点是,这段历史的存在,是跨性别者被命名之前的感觉和倾向的存在,不能真正描述为身份或完全形成的主体性,但无论如何,它们是跨性别者历史的一部分。
在你所说的前史中,“仙女”(fairy)的角色是什么?
巴里·瑞: 写《跨性别美国》时我突然想到,在跨性别者被称为跨性别者之前,一些东西已经被纳入了同性恋史。一提到“仙女”,人们就会想起它是同性恋历史的一部分,乔治·昌西(George Chauncey)出色的著作《同性恋纽约》( Gay New York )立即浮现在我的脑海——我的书《纽约浪子》(New York Hustler)也同样难辞其咎。在20世纪20、30年代和40年代美国的大城市里,女性化的“仙女”和变装者(两者不同)随处可见。他们的出现表明,跨性别者的存在并没有被隐藏起来,而是充满活力的城市文化的一部分。仙女(和变装者)在整个跨性别历史之中的重要性在于,他们展示了跨性别者在被命名之前的那个时期的多样性。

20世纪20年代曼哈顿韦伯斯特音乐厅的变装舞会
这本书中的主要人物是谁?他们的故事值得更广泛的认可吗?
巴里·瑞: 卢·沙利文(Lou Sullivan)是一名同性恋跨性别者,在同性恋跨性别者很少的时期,他相当出名,但他的跨性别者叙述和日记值得更多的认可。这让我一开始就对跨性别者的历史产生了兴趣。
还有其他一些人的故事和观察交织在《跨性别美国》的框架中,这些内容应该被更多人了解。例如朱丽叶·雅克(Juliet Jacques)、雷·斯彭(Rae Spoon)和CN·莱斯特(CN Lester)。有一些重要的跨性别者人物,比如苏珊·斯特莱克(Susan Stryker)——她作为一名研究者、理论家和核心参与者,对跨性别史的贡献比任何人都大。
书中有许多次要人物的故事也值得更广泛的认可:圣昆廷的囚犯阿蒂(Artie)、俄勒冈州跨性别男子艾伦·哈特(Alan Hart)、自称“没有阴道的女孩”的“仙女”珍妮·琼(Jennie June)、男扮女装的卡克特( Cockettes)、相当顽固的早期跨性别患者帕特里夏·摩根(Patricia Morgan)、卡萨苏珊娜地区的变装者、新奥尔良露珠酒店的女性模仿者。跨性别者的故事实在太多了。
你在书中写到,黑人工人阶级文化“特别容易接受”性和性的灵活性,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呢?
巴里·瑞: 我不确定为什么会这样,但这肯定是存在的,无论是在拉丁裔文化还是黑人社区都是如此。比如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哈莱姆俱乐部和地下酒吧、同一时期华盛顿特区和巴尔的摩的黑人女性模仿者、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变装皇后、变装舞会和女性模仿、80年代和90年代的俱乐部表演者,以及同一年代的纽约跨性别者街头文化,这些都是在摄影师杰夫·考恩(Jeff Cowan)、内藤胜(Katsu Naito)以及电影制片人苏珊娜·艾肯(Susanna Aiken)的摄影、大卫·瓦伦丁(David Valentine)的人类学作品《肉菜市场女孩》( Meat Market Girls )中捕捉到的。20世纪80年代、90年代和21世纪头10年,家族 [house,一般由一位较年长的同性恋/跨性别者担任母亲的角色,收留无家可归的同性恋/跨性别者,以家族的形式参与变装舞会]/舞会文化在美国多个城市盛行,包括著名纪录片《巴黎正在燃烧》记录的世界、丹尼尔·波德尔(Daniel Peddle)的电影《勇敢者》(The Aggressives)中黑人和波多黎各女性的男子气概、21世纪洛杉矶的Studs影院等等。这是一幅丰富多彩的画面,表明跨性别者的历史比跨性别的历史要漫长而广泛得多。

《勇敢者》,这部纪录片探索了女同性恋者的亚文化
如今我们可以从60年代和70年代初对跨性别者能见度增加的强烈反对中学到什么?
巴里·瑞: 这是一个令人沮丧但重要的跨性别史时期,除了我的这本书,还没有人真正写过。一个更重要的信息是,即使是在能见度较高的时期(我考虑的是我们目前的情况,即所谓的跨性别转折点),也可能会出现反应和反弹——没有什么是理所当然的。另一个教训涉及到那一时期人们对待跨性别者的态度和做法,在美国医学史和精神病学史上,都是一个相当黑暗的时期。可悲的是,其中一些态度至今仍伴随着我们。让人们知道跨性别者历史上的这段黑暗时期是很重要的。
手术的发展如何与更广泛的历史交错?
巴里·瑞: 这是一个很有洞察力的问题,我不敢肯定三言两语就能回答。手术只是跨性别者的一种治疗方法,它在跨性别者的历史中曾反复出现:从20世纪初零星的身体改造尝试,到跨性别者时期相当粗糙的手术特权,再到更复杂但提供选择的手术解决方案(包括复杂的面部手术)。手术是跨性别者的核心,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即使他们想要这种形式的治疗,也很少有跨性别者能够负担得起手术。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手术不再被认为是跨性别的关键,这一点已被载入医疗保健专业人员指南。尽管如此,各种形式的外科手术(包括自我手术和未注册医生的手术)在跨性别史上仍然很重要。我认为埃里克·普莱蒙斯(Eric Plemons)说得很好:“虽然手术不能定义跨性别者,但在他们许多人的生活中,手术是很重要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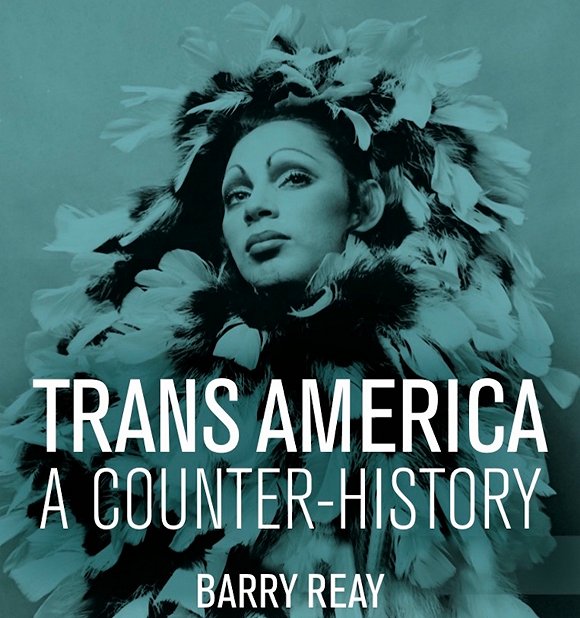
《跨性别美国:反历史》
你所说的“医学模式”是什么意思?这本书是如何抵制这种做法的?
巴里·瑞: 医学模式指的是由医生和心理医生定义和确定的跨性别者,医生决定谁适合治疗、如何治疗,甚至决定了他们所谓的病症的定义。医学模式不仅决定了跨性别者(至少是那些寻求医疗帮助的人)的现实情况,而且还会影响他们的历史(从他们的经历如何被记录的意义上讲)。
如果历史学家、其他评论家和研究人员都依赖于来自医生、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学家的资料,包括大量医学和心理学文献,那么,他们就有可能被资料来源和医学模式所俘获。绕过这一点的方法,要么是忽视医学文献(这将适得其反),要么是批判性地与主导范式的脉络背道而驰。至关重要的是,也有由跨性别者自己撰写的文献,往往是对医学模式的批判,但并非全部如此。
当然,《跨性别美国》讲述的是那些生活中几乎对医学模式视而不见的人,或者那些有意识地创造出不遵循性别和性行为、不遵循跨性别和跨性别者的主导类别的存在和观察方式的人。街上的跨性别者的数量,与在诊疗室和手术室的人数一样多。
为什么跨性别者的历史会被抹去?
巴里·瑞: 我希望我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在阅读跨性别者的回忆录和评论时,我印象最深的(我在书中举了例子),要么是没有任何历史感,要么是觉得回忆录或评论家对之前存在的其他跨性别者视而不见。关于历史被抹去的答案可能存在于更广泛的文化和社会中,但似乎有这么多年轻的跨性别者在探索和发现自己的性别,渴望榜样或其他可能解释他们感受的例子,却忽视了自己的文化或过去中的例子,这似乎是个悲剧。毫无疑问,现在的互联网提供了他们自己文化中的例子,但我不确定它是否足以说明过去的可能性。
你的书是如何应对这一趋势的?
巴里·瑞: 我希望在书中传达跨时代历史的深度和多样性。我认为这部作品可以为那些认为自己孤身一人的人,提供CN·莱斯特所说的“陪伴带来的安慰”。当然,人们必须先读一读这本书。
(翻译:李思璟)
 简体中文
简体中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