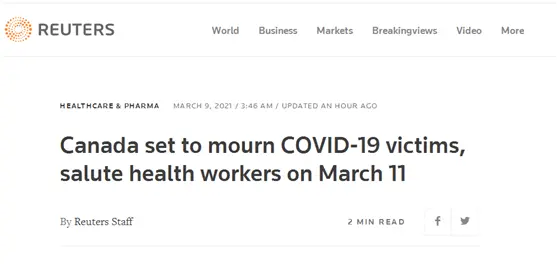蔡成杰导演的《北方一片苍茫》,属于典型的独立电影处女作。穿透其「一个萝卜一个坑」式甚少艺术变化的质朴镜头,电影沉重的黑色内核「跃然纸上」。
它以河北平泉为故事场域,在丘陵、树林、河流、低矮平房之间,借白雪皑皑的深寒气候,赋予粗糙的人性以思辨特征。田天饰演的寡妇二好,以正面而苍凉的角色,勾连出北方郊寒地区狭窄而反复的伪善群像。
而在这过程中,每当格外节制的配乐响起,一些在画面开始之前就已经「领了便当」的人物,则在主角的往事回忆里,为电影浸入独特的柔情力量。
导演曾在采访中许给观众「走神的自由」——当电影角色的形象或行为在镜头中被缩小,而镜头本身并未被移动,观众得以观看其它信息:家具、年画、门帘、枯树瘦枝,甚至雪雾流过银幕,这些环境信息将观众吞噬进故事之中——随电影音乐而起的柔情,提供了另一种走神方式:以情绪将观众裹成雪球,抛出故事之外,但雪球却始终滚动在寡妇的北方地区。
正是这样的时刻,令人放弃对电影质感与技术水准的苛责。《北方一片苍茫》是一部「慢电影」,但剧作对人性的推演却清晰而迅速。
寡妇二好的表情与语言,并未精准咬合在「普度众生苦,仙女下凡尘。冷雨凄凉尽,浴火塑金身」这样的命运锯齿中,但她的行为与台词本身,却立竿见影地令她与电影中其它「凡夫俗子」,在命运上水乳交融,精神上壁垒分明。
对主角这种「悲苦而强势」的塑形,具有一目了然的东方式「供奉」意味,恰与电影原片名《小寡妇成仙记》直白的指代性吻合,也证明电影似乎不志于深掘「一念成佛、一念成魔」的人性灰色地带,而专注于一种纯净的批判。我们能看到一个意图相当明显的设计。
寡妇站队错误,村长便使人以「百家尿」冲走寡妇仙气,之后村人进山开矿,矿塌,村中妇人又央求寡妇再请其他的神。一冲,一请,寡妇不过容器与工具,而寡妇等于仙,实则仙神乃是工具而已。信仰在烟火熏香之中,化身为一个分量尽失的假命题。
此次《北方一片苍茫》的北影节版,为109分钟,相对于最初版本的170分钟,以及First青年影展版本的140分钟,这种「压缩」,无疑会使故事场域更为凝练,令影片主打的批判性,能更锐利地命中靶心,使电影独立的影像与文本,充分释放一种独属于处女作的野蛮生命力。
独立电影或处女作电影,因为较少受商业性或制片人中心制操纵,使其相比成熟的大制作,更容易在一个浓缩的格局内,迸发出极具参差感的原始艺术力,令人如见新芽破土。可能导演在现场对道具、演员、灯光等控制都相当精准、严格,但当所有元素最终楔在一起,却会使电影呈现出一种坚韧而全然的自由主义。
毕赣《路边野餐》与张大磊《八月》的诗性、马凯《中邪》的邪性,便是一种低成本自由主义的体现。这些新导演以镜头为笔,创造出独特的写作风格。在《北方一片苍茫》中,蔡成杰导演的笔力,则兼具生涩之新鲜与遒劲之熟练。
影片虽采用关于萨满巫术的通俗叙事,但它对叙事的创造性发挥,却强调了「作者电影」的文学性。
片中,群众演员有时会将台词讲到断裂或重复,在一部圆润的作品里,这些「失误」理应被剪辑,但它们却被完整保留于北方村庄的冰天雪地与村民群众的一呼一吸之中,这种「刺儿」,恰好呼应影片粗粝的质感,予人一种难以名状的亲切。
具体到台词内容,剧作则时见「机杼」。寡妇与聋四爷的第一场对话,影片先以较重篇幅呈现两人的自说自话,这与鲁迅在《而已集·小杂感》中那段著名判断异曲同工:
楼下一个男人病得要死,那间隔壁的一家唱着留声机,对面是弄孩子。楼上有两人狂笑;还有打牌声。河中的船上有女人哭着她死去的母亲。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
电影中,寡妇急于倾述自身遭遇,聋四爷则未意识到与之对话的是寡妇,前者代表情感输出的失效,后者代表命运的某种围剿,此处不相通的悲欢,便更添一种斑驳之味,这种斑驳散发的魅力,已经远超影像本身的动人程度。
当然,电影也在影像层面具有完全的创作自觉性,令人无法忽视的,便是画面色彩。全黑白的复古画面,在如今的「作者电影」领域,似乎已经落伍,因此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色彩切换:黑白与彩色各代表一种意蕴,切换将使电影的层次感更为清晰。
《北方一片苍茫》则以一种极为独特的方式,对画面色彩进行「偶然性」切换(当然是经过了精心设计的「偶然性」)。
黄信尧《大佛普拉斯》中,色彩在贫富差距与生活区隔间进行切换,弗朗索瓦·欧容《弗兰兹》中,色彩则在惨淡现实与美好臆想间进行切换,张大磊《八月》中,色彩切换则如昙花绽放之一瞬与这一瞬前后的等待与落寞,自如、隐约、令人心悸,《北方一片苍茫》却摒弃所有明显的意义,在以色彩区分某些隐性意蕴的同时,又再度模糊色彩之间的界限。
我们甚至看到彩色画面与黑白画面在同一个镜头中自洽相处:炭火黑红,在铁盆中兀自燃烧,即使将铁盆边缘烧出黑痕,这唯一的彩色仍被圈定于盆中,无法爬出并烧满整个电影画面,从中不难体味命运挣扎的无力,暗合电影角色宿命论与巫神论的命运基调。
异于多数电影的色彩切换,这部影片用黑白画面囚禁彩色画面。彩色偶然露满整块银幕,却在下一个镜头中被黑白瞬间吞没,或如上,在黑白主色中,银幕角落里的彩色探头呼吸。
在文学作品中,这种处理类似于某种诡异而充满力量的文句,而整部作品的「题眼」,导演很可能通过一块镜子令观众感知。这块镜子被不相干的路人甲摔破,丢在雪地中,寡妇自雪中走过,裂痕镜像出她破碎的身影。
重要的是,虽则破成一块一块,但镜子仍映出一个相连的整体。这精神的完整与命运的破碎,以及横布其间的裂痕式拉扯,也是电影约略呈现的「公路片气质」写照。
而随着一辆作为居所的小客车在北方苍茫大地走走停停,我们时会看见一些高于现实想象的元素点缀于寡妇的命运之中。插了天使翅膀的摩托车男人、仿佛《鬼影》般趴在赖账者背上的鬼魂、狐狸之子、堕井自杀者的还魂身影……大约囿于成本,电影直接将这些元素并入现实环境,几乎未做区隔式的特效处理,然而这反将现实与魔幻完全融合在一起,使魔幻成为现实的筋骨血肉,完成一种虽则粗糙、但却具有真义的魔幻现实。
对于独立电影,成本与拍摄时间近乎苛刻的限制,有时反而容易激发作品令人惊讶的表现力。7万拍摄成本的《中邪》,弃用对于恐怖片而言至关重要的音效,完全依靠叙事推动惊悚情节,以环境音渲染恐怖氛围,结果强调出了叙事力量与浸入体验,颇有奇效,而《北方一片苍茫》的拍摄时间仅有九天(正月初八开机,正月十七杀青),却最终呈现出一种挥洒式的自由创作才情。
在成熟制作屡屡令观众疲惫的电影世界,能精选这样一部「初生牛犊」的巫野之作,电影的生命力或许也能于焉蓬勃。
(来源:幕味儿)
 简体中文
简体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