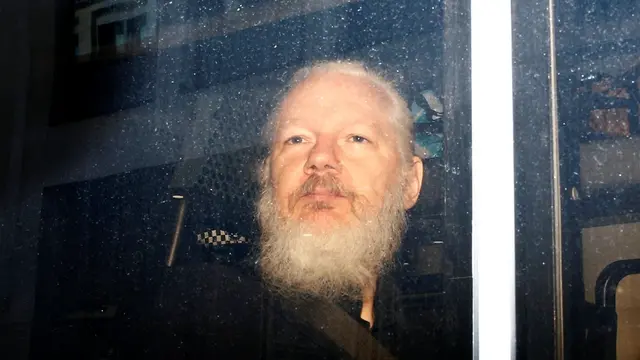史上最古老的马来王国在公元10世纪时,已经控制了沿海港口城市,其中以吉打州的龙牙修国(及布秧谷)最为古老。14世纪伊斯兰教传入东南亚,产生广泛影响,拜里米苏拉于15世纪创立马六甲王朝(满剌加)。1511年之后,葡萄牙、荷兰与英国相继控制了马六甲海峡。200年后,法兰西斯·莱特再造一个繁华的槟城,但好景不长,槟城很快被斯坦福·莱佛士爵士在1819年开拓的新加坡所取代。
我的旅行源自一次偶然的机票折扣,但内心对这个半岛的好奇由来已久。三年前,在走完中南半岛五国,昔日法属印度支那地区之后,我曾抵达马来半岛的北端。遥望边境以南的广袤大地,忍不住揣想,地缘文明将产生如何强大的辐射作用?这个昔日同样受印度和中华文明影响的半岛,是怎样在伊斯兰教进入后,消化并理顺了一切,实现了多元文化的融汇和发展?
我为时半月的旅程将从半岛最南端的新加坡开始。
新加坡市内阿拉伯风情街即景。本文图片除特殊署名外均为 雅狼 图
“坡县”
经由香港转机,搭乘的红眼航班在凌晨5点多降落。新加坡潮热的空气让人昏昏欲睡,窗外一片璀璨灯火却点燃了我的兴奋。
在马来半岛的最南端,这是一处耀眼的目的地。这里是老一辈华侨记忆里的星洲、狮城,互联网新一代口中的“坡县”。
如果说机场是一个国家向旅客打开的第一扇窗,樟宜机场这扇显然明亮异常。
推着简易行李车在这个并不袖珍、甚至有点庞大的机场里穿行,来往的人行色匆匆,我却意外地感觉放松,甚至想停留下来坐一坐。说起来,充分的绿化和设置在航站楼中央区的漂亮花园并不少见,Xbox游戏室、幼儿滑雪区、24小时免费放映电影的大屏幕和舒服躺椅也不算新鲜,打动我的是更为人性化的微小细节——科学的残疾人通道和完善的母婴设施,尤其是后者。在亚洲大多数机场,母婴室和女厕所是连在一起,气味不会太好。这里却将二者在有限的空间里做了巧妙的区隔,不愧为世界上唯一的五星级机场,在厕所边上,还能看到各种语言的新加坡地图和旅游资料。
搭乘地铁旅行是“性价比至上”派的最优选,四通八达且人性化的地铁也是城市化的一个衡量标准。从机场到中心区的乌节路,打车需要40新币左右,搭地铁却只要3个新币。选择东西线(地铁图示为绿线),坐到EW13的“政府大厦”站,然后转南北线(地铁图示为红线),三站,到NS22的“乌节路”站下,十分方便。被北京地铁或纽约地铁的拥挤和嘈杂充分惊吓过的人们,在这里会体验到一种“东方现代化”的舒适和平静。空调的温度不太冷也不太热,到处可以看到拿着纸质书阅读的乘客,身体和身体偶然接触,会立刻退到一个安全的位置,相比其他吵闹又充满世俗人情味的东南亚国家,新加坡人处处显得热心而克制,接人待物方面更像同为“亚洲四小龙”的日本,自带一种习惯性的礼貌,却不动太多感情。
甘榜格南是新加坡穆斯林的主要聚集地之一,著名的苏丹清真寺屹立于此。
此刻我从地表之下钻出乌节路,一下就进入了国家资本主义的繁华世界。
乌节路的名字,据说来自于肉豆蔻和辣椒,难怪两旁的名店橱窗也如此“辣眼睛”——亚洲最大路易威登旗舰店之一,干脆是一个充满未来感的建筑实验;地铁可以直达此地著名的IONOrchard购物中心。当然,对购物不大感冒的我,只当此地是散步和偷拍路人的场所,真正的目的地是向北半小时脚程的金沙饭店。
在滨海湾的水边,一座露天的奇迹坐落于此。耗资1亿美元,形如冲浪板,又像一艘建在三座大楼头顶的方舟。金沙顾名思义,首先就是金贵,2500人民币一晚的房价只能买到15层的景观房,这比文华东方和四季酒店的价格还要贵出许多。大多数慕名而来的客人是为了楼顶上的无边游泳池,不过,在我看来,金沙饭店的最大魅力,是在它的制高点可以尽览新加坡最贵、最高、最现代化的建筑群。外行人看见的或许是这个国家的富裕或者铺陈,内行人却可以看到创造力、环保意识、现代理念和技术崇拜。
我决定用脚和眼睛验证一下这种魅力。从金沙饭店步行十分钟不到,抵达滨海湾花园,这里生长着18颗“参天大树”,钢铁树形结构上攀附着热带攀缘植物、附生植物和蕨类植物,寄托着新加坡政府对绿色环保的期许。世界上首座双螺旋人行桥——新加坡双螺旋桥,也在滨海湾一带,据说同时可容纳1.6万人。DNA造型的创意,代表“生命与延续、更新与成长”,体现了现代化的新加坡对生命的尊重;在42层大楼的高度,你会一眼注意到新加坡摩天轮,165米的海拔名列世界第一,它有28个安装了空调的座舱,每个都大得像一辆客车。站在这种高度上,人的胸臆顿时也宽大了起来,你会发现,整个马来半岛地理上完全是一体的,因为在天气晴好的日子里,能远眺印度尼西亚的巴淡岛、民丹岛,以及马来西亚的柔佛州。
让来客充分感受到这种一体感的,还有鱼尾狮狮头,城市最重要的标志。据《马来纪年》记载,公元11世纪时,一位来自苏门答腊的王子在前往马六甲的途中登陆新加坡,看到一只神奇的野兽,狮子,于是为新加坡取名“新加坡拉”,梵文意为“狮子城”。这一标志,仿似带人回到了古早的马来半岛风云中,在这片大陆上,古代的新加坡无论地理还是行政上,长期属于马来西亚,唇齿相依、文化共享。到了1965年,在脱离英国殖民统治、短暂并入马来西亚联邦之后,新加坡选择了独立,为了构建它的国家认同,它经历了1980年代的“儒家伦理”和1990年代的“亚洲价值观”阶段,正在经历2002年提出的“再造新加坡”阶段。
新加坡设计博物馆
这种“再造”,弥散在我身边的环境里,年深日久,积少成多。比如国家美术馆。这是我短暂的新加坡之旅的最后一站,它原本就是“再造”的产物,在城市两座深具代表性的重要历史建筑,政府大厦和前最高法院基础上,改建成为创意产业空间。馆内典藏的泛东南亚地区的艺术作品,与马来半岛、东南亚和世界各地的艺术接轨,展示呈现了19世纪至今新加坡和马来半岛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历史。
在藏品中,可以看到大量新加坡华人生活史的片段,那些历历在目的南洋老故事和旧场景,像推广了30多年的“讲华语运动”,讲诉从不间断。经由这些消逝已久的时代印记,身处展馆之中的我,仿佛闻到了肉骨茶飘香,渗入骨髓的东方气质和中草药的味道,抵制了热带的瘴疠之气,治愈了东方的胃,也抚慰了东方的魂。
斋月节的吉隆坡
出发前往吉隆坡前一天,身在吉打的Agne姐姐给我发来了出行路线的建议。她建议我在吉隆坡的数个机场,KLIA、KLIA2、梳邦机场以及亚航专用机场当中,择定一个目的地,预订机票,顺便买好从机场去往市中心的KLIA Ekspres车票。
对于我这种喜欢长途旅行的背包客来说,马来西亚联邦的首都吉隆坡是个身份微妙的存在。
相比世界文化遗产城市槟城和马六甲,吉隆坡显得过于现代化、缺乏特色。然而,吉隆坡又是绕不过的一段,因为世界最大的廉价航空——亚航_的总部就设在吉隆坡。所以,旅行者往往选择在这里转机,前往马来西亚各地和世界各国,很少将这里作为目的地。
2014年马航事件发生后,吉隆坡的游客进出量受到了一定程度影响,外国客人们宁愿通过转机的形式,搭乘他国航空公司的航班前往吉隆坡。然而我还是决定来看看,因为开斋节即将开始,Agne姐姐告诉我,在马来西亚感受清真文化,除了前往亚罗士达,还一定不能错过吉隆坡。
落地后,发现紫色妆点的KLIA2机场小而美,颇为温馨,便利性上不输给樟宜机场。只是明显看不到什么中文标识,机场里有伊斯兰专用的祷告室,人群中闪现出越来越多的马来穆斯林,像是紫色森林里的深色花朵。
KLIA Ekspres带我飞速驶离机场,沿途的热带植被与东南亚其他地方无二,但建筑的颜色显然更为冷静低调,属于“清真的色彩”。在路边的广告牌上,我甚至瞥到了一则戒酒广告,一切都在提醒我,已经正式进入了一个清真的伊斯兰国家。伊斯兰教在10世纪传至马来西亚,对马来人产生了深远影响,成为国教。
吉隆坡街头有许多涂鸦和彩绘,这是在独立广场附近的一件著名作品
开斋节将在两天后举行。醒在吉隆坡的清晨,唤醒我的不是鸟鸣,不是闹钟,更不是手机微信的推送声,而是市区中不知何处传来的清真寺里的唱颂声,那声音飘渺而纯净,煞是动人,有一种自灵魂深处发声的感染力。搭着地铁或徒步闲逛时,在现代化的建筑丛林里,时不时与这些属灵的感性的城市风景相遇。
这一天,我来到了独立广场附近。这个满是绿茵的广场是为了纪念1957年马来西亚脱离英国殖民而设立。有趣的是,市中心最具建筑价值的地标苏丹阿都沙末大厦就位于广场对面,这栋综合了摩尔、莫卧儿和英国殖民地古典建筑风格的大厦,恰恰是当年英国殖民政府的几个重要部门所在地。这组对应的建筑,越发让我觉得,历史的书写,有时候不靠文字,而是靠一种空间想象。
更大的空间想象,来自于广场周围的国家清真寺和佳密清真寺。顺着广场通往铁道的走向,在转角处,发现屋顶如一把折叠大伞、73公尺尖塔刺入天空的国家清真寺。它通体洁白,是东南亚最大的清真寺,在马来西亚独立后第八年修建而成。若非资料提醒,我不会想到,这个圆顶带尖角的造型寄予着一个独立自治国家的尊严。寺庙共有18个角,象征马来西亚的13个州和伊斯兰教的5大规条。带着国家之名,寺后自然只能安葬国家英雄,按规定只有任过总理或在职去世的副总理能葬在这里。也是在广场附近,另一座佳密清真寺坐落在巴生河和鹅麦河汇流处,这是马来西亚最古老的清真寺,落成于1909年,它的造型看上去很像麦加的那一座。这一殖民时代的产物,却激发了我的好感,也许是它的纯粹,不需要背负“国家”的重担。可惜的是,我穿着短裤,还没接近清真寺的大门,已经被几名穆斯林男子用犀利的眼神阻止了。于是,我爬上了高架中的地铁站走廊,踮着脚留下了一张俯瞰清真寺的照片。
吉隆坡的最后一晚,开斋节的欢乐气氛正浓,我一个人散步去了吉隆坡双子塔下面。起初
我只是想拍一张清晰而完整的夜景,却因为满城茂盛的榕树自始至终遮挡视野,不得不继续向前移动,以寻找最佳的拍摄角度。
就这样,穿越了四条横街,一条主干道,三个过街天桥,又绕过了一组高楼大厦以及无数路障,终于在30分钟后走到了双子塔下的人工湖前。
吉隆坡双子塔在树影的遮蔽下,依然有明亮的轮廓,它与点着红灯笼的传统中式建筑相映成趣
双子塔是无可辩驳的马来西亚象征物。它曾经是世界最高的摩天大楼,高452米,地上88层,其中一座是马来西亚国家石油公司办公用,另一座是出租的写字楼,在第40与41层之间有一座天桥,长58.4米、距地面170米高,方便楼与楼之间的来往。
无疑,这里已经被喜欢自拍的时尚男女站满了,各种肤色的年轻人加上双子塔脚下的现代商场,使得这个区域充满了国际化的氛围。我也掏出手机,有点不好意思地请一个香港口音的亚洲脸帮我完成与双子塔的合影。
透过照片,我发现了它的另一个秘密。原来在这座灯火通明、年轻又现代化的建筑中,依然采用了伊斯兰元素作为设计主轴。它的格局里有传统回教建筑常见的几何造型,包含了四方形和圆形,虽然不能用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外圆内方”强加给它,但也可以理解为某些可贵的品质。“双”是另一种“在我之外,可以有他”的接纳,正对应着吉隆坡融合多元的文化。
吉隆坡坚持了它的信仰传统,又将新的发展设计融入进来,使得建筑获得一种生生不息的活力。或许,这就是吉隆坡与众不同的魅力。猛然想起,马来西亚是世界上伊斯兰教世俗化搞得最好的国家之一,这个世俗化的表现,自然体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此刻活生生地在我眼前展现。幸好,我懂得不算太晚。
三宝山下
从其位于半岛的地理位置来看,马六甲州的首府马六甲处在新加坡和吉隆坡之间,完全可以采取从新加坡出境、过柔佛大桥、上高速公路的陆路方式抵达。但是更多客人会和我一样,先在吉隆坡停留,然后坐三个小时的大巴,再向南前往马六甲。
经过沿途绿野的洗心洗肺洗眼,踩到马六甲地面的第一秒,眼前“哗”一下实现了升华,从节奏匆忙的21世纪现代都市,倒流回15世纪慵懒宜居的老旧小城。反差越大,幸福感越强烈。
马六甲是一座非常小的世界文化遗产城市,小到从我住的旅馆走路十五分钟就到了城市中心,荷兰红屋广场。在这里,车辆都像是摆设,双腿是最合适的交通工具。
马六甲河游船服务自2006 年启动,游客可自海洋博物馆旁边的Muara码头和Spice Garden 码头登船游览
这一切让人无法立刻联想起它辉煌而浓缩的历史:曾经的马六甲王国都城,郑和下西洋有六次在此停靠,它濒临的马六甲海峡处于太平洋与印度洋之间,又是北太平洋与南亚、中东和非洲各国之间的交通要塞,而作为深水良港的马六甲,聚满了中国、印度、荷兰、葡萄牙和阿拉伯的商船,至今是这条海上生命线的咽喉所在。葡萄牙外交官托梅·皮莱斯曾这样形容它的重要性,“马六甲的主人扼住了威尼斯的喉咙。”更不要说,这里还是著名的博物馆之城,光荷兰红屋周围方圆100米不到,就分布着10个著名的博物馆。
让我再沿着蜿蜒而过的马六甲河,从南到北走完整个城市,在河流的西端与印度洋相遇。马六甲海峡日夜吹拂着海风,吹拂着600年的发现史、探索史和战争史。
一种近代史观认为,从15世纪大航海时代开始,一直到20世纪,马六甲不停地沦为葡萄牙、荷兰、英国和日本的殖民地,一次次地被新进入的文化清洗,近乎全数丧失了自己的地域特色。作家毛姆如此描写这座城市:“这座古城充满着怀旧的忧伤,这种忧伤存在于所有昔日重要的城市中,而如今,它们只能生活在对逝去荣耀的追忆中。”
事实如此,但如果换个角度看问题呢?会不会少一些伤感。
由于地理大发现,世界连成一个整体。海洋文明延续了人类文明进程。这里成为亚洲文化最多元的城市之一。马六甲正是发现的产物。
我的发现之旅也在继续中,来到城市中心的三宝山下。这座山目测不过几十米,却是城中最显眼的地方。近代,一位叫李伟庆的中国船商买下了这座山,并划出26亩地作为墓园。如今,这里共有 12500 名中国人在此长眠,历史最早可追溯到明代。
三宝山纪念的是三宝太监郑和。如果说1396年是马六甲官方史书记录的建国时间。早在1409年,郑和第一次远航时,就曾在山上扎营;郑和船队每次前来,都选择在这里休整,进行物资补给。船队常常以此为据点,前往各地进行访问和贸易,又齐聚此地,等待5月的季风,顺风返回祖国。
圣方济教堂紧邻红屋广场,顶部哥特式的尖塔十分引人注目
由于双方充分的交流,马六甲王朝有3个国王和26批使臣去过中国明朝。山上还流传着曼苏尔沙苏丹为中国来的汉丽宝公主修建宫殿的故事。1641 年荷兰人攻下马六甲,将这座山改成了墓地。但道教庙宇的三宝庙和三宝井、三宝亭都留了下来。这里可谓中国痕迹最多的地方。
荷兰人留下了荷兰红屋(现为马六甲博物馆)和史达特斯教堂 (现为市政厅),荷兰红屋是城中最大的博物馆,原建于马来王朝,历经葡萄牙、荷兰、英国等殖民时代,由六个博物馆构成,博物馆内部的展品通常配有英文和马来文的解说词。1511年,葡萄牙人的战船打进了马六甲海峡,占领了此地的马六甲王朝,在城中留下了很多教堂,现存完好的圣地亚哥古城门和圣保罗教堂。
各国留下的文化遗产,如今皆是著名的旅游景点。对历史爱好者来说,这条短短的、博物馆林立的荷兰街堪比“通天塔图书馆”,浓缩了600年的智慧。
出门在外,解决了求知的问题,接下来就是肚子的问题。还没出国之前,就听朋友提过多春茶室海南鸡饭的大名。离开荷兰街,跟着一辆载满中国客人的三轮花车,走不了多远,就抵达了另一条沿着河流走向的老街——华人聚集的鸡场街,此处有当地最著名的夜市。这种花车和这条老街可谓相得益彰,充满浓浓的南洋复古风,车上装饰着彩色的塑料花和彩灯,满是俗世的热闹劲儿,车上最常放的就是邓丽君之类的老歌。
进入街口的第一眼,抬头看到巨大的郑和船队模型,面前的建筑上还悬挂着“纪念中国和马来西亚建交四十年整”横幅,右手边的多春茶社挤满了排着长队的华人,这家餐馆几乎24小时都有人队,看样子我肯定挤不进去了,为了尽快填饱肚子,只得找了一家潮汕小馆,再次喝到了新加坡的肉骨茶,还吃了六粒鸡米饭,一时间饱得心满意足。
在马六甲马来人聚集区可以品尝到地道的马来美食
这时候,我才有心思打量眼前这条名副其实的“中国街”,一水儿的骑楼长廊和宽街窄巷,陶瓷瓦和木板墙,水泥和石板交替出现。本地建筑多数是南洋风格,坡形的屋顶,是广东、福建一带华侨常采用的样式。虽然其中不少建筑被改成了商用的饭馆、咖啡馆和店铺,但在建筑造型、门楣和屋顶上,依然盖不住浓郁的古味。古老的庙宇、民居和会馆,隐藏在它们中间。到了中午时分,街摊也热热闹闹地摆了出来,大多是一些娘惹风味的马来特产。榴莲饼和粿条,都是我百吃不厌的小食。
说到娘惹文化,不得不提到这条街上的巴巴娘惹博物馆。这家豪宅原本是私人的,后来捐出,用作文化展示。巴巴和娘惹,分别用来指代早期移民到马来半岛的华人男女。他们是关于马六甲的海洋故事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甚至更加璀璨。巴巴娘惹博物馆里记载了这段华侨史。在多个世纪之前,巴巴和娘惹的祖先,陆续由中国福建或其他南部沿海地区向马来半岛迁移,他们多半因贸易致富,和当地人通婚,男的被称为巴巴,女的被称为娘惹。马六甲是他们最早的迁移地。
到了19世纪末,被称为“白色黄金”的三叶橡胶树引来了大批淘金者,让很多“马六甲巴巴”一夜暴富。鸡场街的街道上至今留有这些早期海洋拓荒者的府邸。勤勉的南洋华侨落地生根,占据了马来半岛各处绝对的贸易先机。富可敌国的巴巴按照广东福建的传统,盖起中西合璧、富丽堂皇的高宅大院,以安放他们的子女和财富。而大户人家出身的娘惹则被锁在深闺里受教育,按照传统方式婚配,直到近现代才说服她们的父母,赴海外留学并自由恋爱。
当我经过那些红木八仙桌,金银打造的梳妆镜和首饰,落满灰尘的黑胶唱片和绸缎改良版旗袍,心里默默在想,这里藏了多少南洋摩登梦啊。
槟榔屿
带有强烈粤闽移民特色的南洋梦,对于我这种在东南内陆长大的人来说,多少有点莫可名状,但无碍于我对槟城的思念。在我心里,槟城是马来西亚最特殊的城市,老老旧旧,干干净净,一半岛屿,一半内陆,人们按部就班地生活,几百年不改人间烟火味儿,比马六甲更有生活气息。每次抵达,都会被它的气定神闲所感动,仿佛置身于一个远房亲戚的家中。
早期南洋华侨最先定居在马六甲,但大规模聚居形成华埠,却是在槟城。槟城是马来西亚第二大城市,由威省和槟榔屿共同构成,人口70万中的一半以上是华人。槟榔屿是个岛,因为岛上种满槟榔树,所以被叫作槟榔屿,它的椰林树影,水清沙白,保存完好的古建筑群落,原汁原味的生活风貌,使得这里既有印度洋绿宝石、东方明珠之称,又有世界文化遗产城市的名衔。
槟城老城区华人会馆林立,大门上也会有中国传统文化符号
大巴跨越槟威大桥,从威省抵达槟榔屿上的乔治镇,到终点站光大广场下车。乔治镇是一座人口众多的贸易大港,拥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槟城划定的大多数遗产。
这是我第二次来槟城。放下背包第一件事,就迫不及待地打车去汕头街夜市,先来一盘蚵仔煎,一碗鱼蛋粉,再来一个椰子。伸着脖子看老板在灶台上大力烹煮,热出一身汗,饭毕,还要打包走一袋凤梨,一份辣炒花蛤,仿佛这样,这个夜晚才过瘾,关于美食天堂槟城,味觉的记忆是最诚实的。
尽管近年来,出于国家旅游的战略考虑,美食之都的称号给了吉隆坡,但是马来西亚人都知道,槟城的美食才是马来西亚最具特色,真正具有家常味道的。而道地的槟城华人文化,反映在庶民的柴米油盐里,在乔治镇的住家生活里。
新街广场的中华茶室会在早上6点开门,长长的队伍很可能从5点开始排,等人在露天的小桌子前坐下时,已经6点半了。须发皆白的老板不怎么正眼看人,但是端上来的菠萝包总是香喷喷的,甜豆浆里的冰块温度刚好,最受人欢迎的是一种油纸包住的硬米饭,折成小小的三角形,又香又辣,很容易饱腹,还是免费送的。
接下来的一整天会充满幸福感,你可以和我一样,选择骑着单车在古城区慢悠悠地按图索骥,寻找孙中山在槟城的痕迹,在大大小小的会馆里,听听华人的老故事,古城区50多个古迹点通常需要看上两三天,也可以和本地人去槟城最大的巴刹(菜市场)买菜,品尝最新鲜的猫山王榴莲,随手捎带买一袋槟城白咖啡。还可以搭乘游览车,先去参观槟城的涂鸦,一路抵达海边的炮台。街心花园有很多人躺在长长的石台上发呆,有的干脆睡着了,手边书直接盖在脸上。
在小贩手里买下冰镇西瓜或啤酒,听着海浪的拍岸声,漫不经心地打发这座岛上仿佛“永恒的夏天”,遥望马来半岛。
槟榔屿形如小龟,游弋在半岛之外,在《马来纪年》一书里,这里就叫作Polo Pinang,而Pinang的名字沿用至今。在明代永乐年间成书的《郑和航海图》中,也出现过槟榔屿的记载。另一个重要的文献记录是在15世纪中期,在中国舟师使用的《顺风相送》中,纪录了从马来半岛的昆仑岛到槟榔屿的航行指南,这足可证,早在15世纪,槟榔屿就已经和中国通商。
由于和威省之间只有3公里宽的海域,战略位置十分重要,槟榔屿更像是一个扼守马六甲海峡的神龟。1786年,英国在这里设立了马六甲海峡第一个殖民地,弗朗西斯·莱特上尉在槟榔屿大兴基础建设,想把这里建设为连接欧亚两洲的贸易要地。槟城自此成为自由港,以豆蔻等香料贸易为主,为东印度公司提供了较大的助益。上百年的海运和贸易史令这里的繁华经久不衰。
自开埠之后,占尽地利之便的华人和印度人就纷纷移民至此。渐渐形成了我们今日所见的大大小小的会馆和生意红火的小印度区。在著名的印度蛇庙前,我听到一位在中国留学的印度小伙子提起了辜鸿铭。
槟城是这位民国大师的故乡,他的祖父辜礼欢是槟榔屿第一任华人甲必丹。据说,弗朗西斯·莱特第一次登陆槟城,便发现有一个华人乘着小舟打鱼归来,还送了他一面鱼网。这个华人就是辜礼欢。自此形成了一个不成文的传统,在马来西亚十三个州内,政治由马来人绝对掌控,只有在槟城州是由华人担任州长。
有华人的地方除了有会馆,自然还有餐馆,想着想着我就又饿了,直奔著名的古城鸡饭粒,就着拉茶大快朵颐。当然,炒粿条也是必不可少的美味,在槟城的每一个角落都能见到它。只是吃多了会有点涨腹,需要来一杯豆蔻马蹄水解腻。两百多年过去了,英国殖民者来了又走,华人始终生活在这里,炒粿条和马蹄水也一直在这里。正如一位槟城作者所言:“社会总要在老百姓的吃穿住行中来运行。”
在姓氏桥,木屋子高架在水面上,屋旁静静泊着小船,它们依然是渔家维持日常生计的必需工具。
吃穿住行的日常历史,到了姓氏桥后,变得更加有趣和丰富。绕过著名的情人巷,在海边一片片高脚屋里,你会发现清一色的华人,他们大多来自中国福建省,原本是渔民,移民到这里后,继续延续老家的本行,世代靠海吃海。由于他们多为同乡,聚在一起相互照应,安土重迁的中国人,通常要盖了房子才叫安定下来,他们盖了房子,在这里繁衍生息,只是依然吃福建鸭饭、说闽南话、喝盖碗功夫茶。
随着华侨人数越来越多,陆地上已经没有地可盖房子,于是槟城的社区逐渐向海里延伸。他们盖的房子,都是先在海中立下木桩,然后盖上模板,房子就盖在甲板上,好像一座可以住人的
桥。现在这种木桩,都换成了水泥桩。屋子和屋子相连,形成了桥一样的屋舍巷道。这种水中的高脚屋,在东南亚并不少见,但是华人却赋予了它们社群一样的特点,街巷相连,邻里相闻,有的像个小四合院,现在,都成为历史遗产,负载着几百年的人间烟火。
在这里的水边发呆,比在海边发呆的感觉又是不同。我看见水边的道观,桌上满是信众送来的红蜡烛,烛光就着蓝幽幽的水面一晃一晃的。脚下拴着的小船,已经很少用来出海打鱼了,就安安静静地泊在乡愁一般的意境里,被前来写生的孩子留在画布上。
某位不知名的艺术家来到码头工人居住的木屋前作画,这是槟城姓氏桥的常见风景。
资料图
闽粤人在国内重视血缘关系,喜欢修祠堂、修族谱,在国外也不例外。槟城姓氏桥是以姓氏来划分,同姓的相互为邻居。于是就有了姓王桥、姓李桥、姓刘桥、姓杨桥、姓林桥、杂姓桥等一个个如村落般的聚集地。其中,姓周桥的规模最大,它的长度300余米。共79户人家,如今,大部分建筑改成了旅社、餐馆和商店。
姓氏桥属于世界文化遗产保护范围,也是著名的旅游景点,很多游客都前来拍照游览,也有人住下来体验生活。街头涂鸦十分常见,大多与渔家生活有关,电影《初恋红豆冰》在这里取景后,姓氏桥的名声更大了,槟城的明信片上也出现了它的样子。
可喜的是,居民们并未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几百年来依旧临水而居,在我的镜头前,一个老人坐在躺椅上睡着了,不管他何时醒来,又梦见了什么,在槟城醒来总是最好的。
米乡
来到吉打州首府亚罗士打,十几天的旅程已近尾声。搭乘大巴是最合适的旅行方式,从槟城出发,需要五小时左右的车程,马来西亚本国的旅游长途车非常规范化,除了空调有些冷之外,舒适度和人性化的程度很高,还有随车TV播放轻音乐。很多客人就这样舒服地睡着了。
我睡不着,正好可以好好看看一路的水田美景。快门也摁得很畅快。
从威省开始,已是一派田园风光,即使时值旱季,空气里仍然有温和湿润的味道,绿油油的水稻长得半人高,美貌程度堪比越南中部,只是缺一个戴着斗笠的少女。用一句流行语形容,沿途有37.2℃一般的温暖舒适感。
手边有一张摄影照片,显示的是距离亚罗士打20分钟车程的象屿山,这是我所见过的最和谐的照片之一,如果大象真的爱吃草的话,再没有比一片青绿色水田中站着一只青绿色的大象更恰如其分了。
象屿山是吉打州的标志之一,吉打州始终位于在这样的水田深处,《孤独星球》形容它:“鱼米之乡、一望无际的水稻田、数百万年的巨大石灰岩、辽阔的田野、苍翠的热带雨林和烟雾弥漫的山脉……”
来吉打州之前,我从未听说过它,无论槟城州、马六甲州,又或是吉隆坡所在的雪兰莪州,都已经获得了充分的旅游开发,并产生了国际品牌美誉度。吉打却默默无闻,直到Agne姐姐骄傲地向我提起它。这里不仅有最早的马来王朝,还向马来西亚贡献了两任首相,时任马来西亚苏丹就是吉打州的苏丹。关键是,这里有最家常、最马来西亚的生活。与南方的几个州又有很大不同。
我能看见什么呢,我很好奇。
亚罗士打因为一棵树得名,进入市区就赶上一场大雨。这个城外是稻田、城里是树的城市被洗得很清新,连路中间的花草也纷纷在雨中招展,在凤凰花树的遮掩下,差点连建筑都要看不见了。能够看到的建筑,除了南洋骑楼以外,还有泰国风格的小楼,第一印象,绿化真的不错。
亚罗士打皇宫博物馆内有许多皇家藏品,这是某任苏丹留下的配饰和勋章。
此刻,我莫名生一种亲切的好感。并不介意它老旧朴素的样子,更不要说吉打街头随处可见的王室画像,就像我在泰国看到的一样。看上去这里的人民很爱他们的领袖,所以他们要么很狂热,要么很平和,根据过去的经验,我先做了一个假设。事实证明,亚罗士打的情况属于后者。
Agne姐姐是本地华人,穿着一身带着金银绣线的本地服装接到了我,这种又像旗袍又像越南奥黛的服装是马来特色。她说,时值开斋节期间,这里的王室有一系列活动。
午饭时间,我品尝了本地的炒粿条,这是我在大马旅行一路走到哪儿都必吃的食物,厨师给我搬了五种炒粿条出来,口味的丰富多变,超出意料,而且米的清香口感,让美食之都槟城都要汗颜了。
本地大米好吃,并不奇怪,因为亚罗士打是马来西亚大米的主要产地之一,和邻近的玻璃市并称米乡。这里的大米远销世界各地。因为先入为主的关系,中国人都知道泰国大米好吃,却不知道吉打和泰国北部接壤,气候环境也一样,论起大米的好吃程度,只有过之而无不及。
种植稻米是马来西亚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人们在劳作时会编稻作歌,有时候开心了还要舞蹈。稻子丰收时,本地热闹得像过节。
如果拿中国的城市和乡村来类比,吉打显然是中国广大的南方地区,像我的家乡,以农为本,工业化不彻底。而这可口的稻米孕育了我们,我们成年以后便远离故乡,远赴更为现代化的北上广,或者更为现代化的吉隆坡、槟城。故乡就这样被遗忘了,只有稻米的清香偶尔会提醒我们的来处,是在水田深处。
“这里也是第一次绿色革命的试验区呢。”Agne姐姐把我拉回了现实。亚罗士打成为米乡,不仅仅在于水土。1960年代至80年代,广大发展中国家还是传统农业经济,世界银行用了十年时间,在吉打和玻璃市投入了数百万美元的发展资金,将其打造成绿色革命样本,无数专家来此进行调研指导。
这一实验在当时是卓有成效的,吉打和玻璃市的大米单位产量,远超南亚地区、东盟地区和马来西亚其他稻产地区。而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也正是马来西亚从亚洲崛起,与邻国泰国共同位列东南亚四小虎的过程。
说起马来西亚与邻国泰国的渊源,一直是斩不断理还乱。吉打州因为靠近泰国北部,这种渊源就更深了。可具体是什么关系呢?在本地的皇宫博物馆里,我从一堆富丽堂皇的藏品中,找到了泰王国的记录。于是,拉着眼睛弯弯的讲解员问个不停。
他用流畅的英语和简单的汉语向我做了说明。马来西亚历史上最古老的吉打王朝,是从吉打州源起,追溯到公元6世纪的布秧山谷。然而,这里最早的文明痕迹和泰国一样,也是印度教及佛教文明。在公元7-8世纪之间,统治吉打的苏门答腊亚齐皇朝没落,吉打一度纳入暹罗(泰国)治下。直到公元10世纪,吉打王朝的统治范围才扩大到海港城市,包括现在的兰卡威岛在内。
查希清真寺是吉打州的国立教堂,也是马来西亚最美轮美奂的清真寺之一,享有“世界十大最美清真寺”的美誉。
公元15世纪,马六甲王朝出现,吉打被建立为伊斯兰教王国。然后,在17世纪时吉打又饱受葡萄牙人和亚齐人的骚扰,最后于1821年再次落入暹罗人手中。1909年,暹罗将吉打的主权交给英国。几经辗转,在日本殖民结束后,吉打在1948年纳入“马来亚联邦”。
可以说,亚罗士打见证着泰国与吉打州分分合合的关系,也见证着马来西亚的王朝政治更迭。遗憾的是,吉打王朝的大部分史料都是马来文写就,藏于王室,鲜为人知。世人或许知道马六甲王朝,却基本不知道吉打王朝。在距离亚罗士打几十公里的布央谷,有一个大规模的考古遗址正在发掘中,这个古城遗址约50平方公里,这是海上丝绸之路文明的证据。其中的考古发现,将坐实本地流传的唐朝义净法师的故事,而这个故事,则能够坐实早期吉打王朝的存在。
义净所在的大唐王朝,经历了季羡林口中“几千年中印交通史”交通最频繁、来往最密切的时代。而义净是其中的翘楚,他曾经三下南洋弘法。在义净亲撰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中,记载了唐初40余年间去往东南亚和印度游历求法的61位僧人,除了大唐僧人之外,还包括朝鲜、越南、日本等地的僧人,其中有30人走的是海路,亦即早期的海上丝绸之路。
海路漫长而艰苦,义净经历了“长截洪溟,似山之涛横海;斜通巨壑,如云之浪滔天”的惊心动魄:从广州乘船出发,一路向西南航行,过爪哇,20天后到达苏门答腊岛上的室利佛逝国。该国是一个佛教中心,义净受到了厚礼相待,“布金华散金粟,四事供养,五对呈心,见从大唐天子处来倍加钦上。”他待了6个月,研习梵文和佛教典籍,接下来前往羯荼。
在《根本说一切有部百一羯磨》卷五中,义净提到,从印度返回的船只一般要在羯荼停留到冬季才续航。羯荼就是今日马来半岛的吉打州,是义净前往印度的第三站,当时吉打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贸易港口、前往印度的中转站。在公元7世纪时,羯茶同样是一个佛教中心,据史料记载,义净法师在此弘法讲经4个月,深受当地华侨爱戴。
我曾路过据说是义净登陆的海滩边,如今只剩下山崖耸立,山崖下是稀疏的树影和驳杂的白沙,在我的背后是无边的水稻田。先人的足迹如鸿爪雪泥,杳然不可辨。而吉打人的生活却借着这作为生存根本的水稻,一代代一世世延续了下来。
(来源:澎湃新闻)
 简体中文
简体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