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瑟琳·瓦伊纳: 你好,娜欧米。你在居家隔离这段时间过得如何?
娜欧米·克莱因: 对于那些像我一样通过Zoom教学生的人来说——在家上课,做各种各样的事情,研究烘焙,我们真的很轻松。现在我回到加拿大和家人一起过暑假。在加拿大,如果你来自美国,将会被严格隔离。我差不多有两个星期没出门了,如今其实对结束隔离有些恐惧。
凯瑟琳·瓦伊纳: 在你最近的一篇文章中,有句来自科技公司首席执行官的名言:“人类才是生物危害,机器不是。”这句话让我毛骨悚然,对未来感到恐惧。你那篇关于“屏幕新政”(Screen New Deal)的文章很有趣。
娜欧米·克莱因: 早在新冠病毒之前,硅谷就已经有了这样的计划,设想通过科学技术替代人与人之间的接触。
因此,在科技尚未完全替代的人与人接触的某些领域,有一个计划——用远程学习代替面对面教学,用远程医疗代替面对面医疗,用机器人代替面对面分娩。在后新冠时代,所有这些计划都作为一种技术被重新包装,来解决人与人接触的问题。
然而,在个人层面,我们最怀念的反而是人与人的接触。所以我们需要扩大与新冠共处的选择范围,但我们还没有疫苗。即使有了突破,也需要很多很多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才能达到我们需要的规模。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面对这一切呢?如果无法维持我们的人际关系,我们会接受前新冠时代的“正常生活”到如今的改变吗?我们会允许孩子通过远程科技来学习吗?还是我们要更加注重投资于人?
与其把我们所有的钱都投入到“屏幕新政”中,并试图用降低我们生活质量的方式来解决问题,我们为什么不能聘请更多教师呢?为什么我们的教师人数不能增加一倍,教室规模缩小一半?为什么我们不能想办法进行户外教育呢?
我们可以从很多方面来思考如何应对这场危机,但并不能接受这样的观点,即我们必须回到前新冠时代的生活。这样只会更糟,只会有更多的监控、更多的屏幕和更少的人际交往。

2019年,在利兹市的一场抗议活动中,环保运动反抗灭绝的支持者们在进行抗议活动。图片来源:Photograph: Ian Forsyth/Getty Images
凯瑟琳·瓦伊纳: 你认为政府会支持这种说法吗?
娜欧米·克莱因: 我最近听说新西兰总理杰辛达·阿德恩倡导每周工作四天,以重建新冠肺炎后的新西兰。新西兰是一个非常依赖旅游业的国家,但新西兰的新冠死亡率与其他国家相比却要低得多。新西兰不能像过去那样对游客敞开大门,所以有人认为新西兰人应该少工作,少拿工资,多享受休闲时间,在自己的国家安全地享受。
我们应该如何放慢脚步?这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感觉就像每次我们踩下标有“一切正常”或“恢复正常”的加速器,病毒就会卷土重来,让我们“慢下来”。
凯瑟琳·瓦伊纳: 我们都喜欢慢下来的时刻,但不管发生什么,英国政府都坚决要回归正常生活。所有的店铺都开张了,酒吧都开张了,我们迫不及待地想去度假。我们迫切需要的不是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而是回到以前的生活方式。
娜欧米·克莱因: 这太疯狂了。想要敞开大门的人只占人口的很小一部分。事实上,大多数人更关心的是在一切安全之后重返工作岗位,在安全之后送孩子上学。政府有时框定给人们想要的东西,但这不是民众真正想要的。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处理方式与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的处理方式有相似之处。他们正在把对抗病毒变成一种测试男子气概的游戏,即便在鲍里斯感染了新冠病毒之后依然如此。巴西总统雅伊尔·博索纳罗谈到,他是一名运动员,所以他知道如何应对新冠(巴西总统在接受采访后不久就透露自己感染了新冠病毒),而特朗普则说他靠的是自己的好基因。
凯瑟琳·瓦伊纳: 在乔治·弗洛伊德死后爆发了反种族主义抗议活动,你对此有什么看法呢?这件事相当新奇,在新冠病毒的危机中,世界各地都在爆发反对种族主义的大游行。
娜欧米·克莱因: 这种反对种族主义的抗议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但我认为这一次的抗议在某些方面是独特的,因为在芝加哥这样的大城市,新冠病毒对非裔美国人的影响巨大。据统计,在美国70%死于新冠病毒的是非裔美国人。
无论是因为非裔美国人从事危险工作、没有得到保护,还是因为遗留下来的社区环境污染、压力、创伤、不安全的工作场所和歧视性的医疗保健。黑人社区正承受着高额的病毒致死风险,这与我们同甘共苦的想法背道而驰。阿哈迈德·阿贝里、乔治·弗洛伊德、布伦娜·泰勒等人的遇害,在这一深刻创伤的时刻,更让人受到极大触动。
但还有一个问题很多人都在问,那些黑人之外的人在抗议活动中做什么?当然对于这种抗议规模而言,很多东西都是新的。许多这样的示威是多种族的,黑人领导的多种族示威。但为什么这次会有所不同?
我有一些想法。一是新冠病毒流行给我们的文化注入了一些温和的思考——当你慢下来的时候,才能真正地感受事物;而当你处于持续的激烈竞争中,你就没有多少时间去移情思考了。从一开始,病毒就迫使我们思考人与人之间相互依赖的关系。你首先想到的是,我和别人共同触摸的东西是什么?是我吃的食物,是刚送到的包裹,是货架上的食物——但资本主义恰恰让我们忽略了这些联系。
我认为,强迫我们以相互关联的方式思考,可能促使我们中更多的人开始思考这些种族主义暴行,而不会单纯认为这是别人的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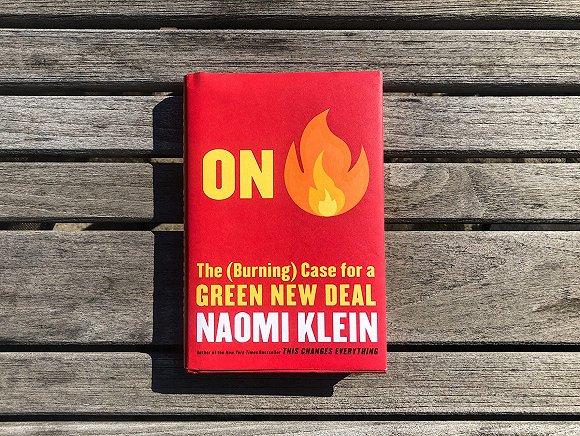
《着火》
凯瑟琳·瓦伊纳: 在你的新书《着火》( On Fire )的新序言中有一句话我很喜欢,你说,“当灾祸升级到无法忍受之前,一切都是糟糕的。”而警察对待黑人的方式就是一种无法忍受的情况。
娜欧米·克莱因: 每当灾难袭来时,总会有这样的言论:“气候变化不会歧视我们,流行病也不会歧视我们,我们都身处其中。”但事实并非如此。灾难往往有着放大镜的作用。如果你之前在亚马逊的仓库染上了病,或者如果你长期接受护理和看护,生活已经失去价值,这些东西如今都会被放大到难以忍受的程度。如果你之前只是可以替代的,那么现在就是可以被牺牲的。
当然我们现在讨论的只是我们可以看到的暴力。其实还有很多隐藏的暴力,那就是家庭暴力。说白了,当男人有压力的时候,女人和孩子都会有压力。这种隔离会让人压力很大,因为即使是最亲密的家人往往也需要一些相对独立的空间。还有裁员导致的经济压力。现如今,种种压力之下的女性处境真的非常糟糕。
本文采访者凯瑟琳·瓦伊纳是《卫报》总编辑。
(来源:界面新闻)
 简体中文
简体中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