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希腊戏剧诞生起,诗人与戏剧就结下了不解之缘。很长一段时间里,以诗歌形式创作的戏剧,即诗剧,是欧洲戏剧的主要形式。莎士比亚、本·琼森、让·拉辛的戏剧都是用诗歌写就的,歌德的《浮士德》和易卜生的早期戏剧也是诗剧。虽然过去的诗人并不都从事戏剧创作,但剧作家却往往兼具诗人的盛名。被公认为世界最伟大的英语作家和剧作家的莎士比亚就是典型的例子,他现存的作品包括37部戏剧、两首长篇叙事诗和上百首十四行诗,其中最为知名的四大悲剧经过不同时代人们的研究、翻译和改编,至今仍活跃在世界舞台。莎士比亚更成为了英国的文化符号,被英国人奉为民族诗人。
事实上,莎士比亚在世时并不受人欢迎,直到18世纪后期,他的剧作才开始受到广泛的认可。浪漫主义诗人们试图复兴莎士比亚的诗剧,其中就包括著名诗人丁尼生、文学评论家柯勒律治以及批评家施莱格尔。进入19世纪后,随着以易卜生为代表的剧作家尝试用散文体创作的戏剧日益流行,进而被乔治·萧伯纳改编成英语,古典诗剧渐渐走向衰落。尽管如此,诗人们并没有停止将触角伸向戏剧舞台。20世纪的诗人兼批评家T·S·艾略特就在他的戏剧作品中延续了莎士比亚的诗剧传统;德国诗人、剧作家贝托尔·布莱希特还独创出一套强调叙事性的“史诗剧”体系。
然而,也有人指出,几百年来这些剧作家虽有优秀的作品登上舞台,但其文学地位却与莎士比亚相差甚远。文学评论家乔治·斯坦纳就曾将柯勒律治到丁尼生的所有英国诗剧都形容为“对莎士比亚主题的拙劣变奏”。美国自白派诗人罗伯特·洛威尔则在一次访谈中表示,大部分现代剧都不值一提,他也不认为剧本可以被当作文学,即便是莎士比亚,他的多数剧本也是服务于舞台表演,而不是拿来坐在扶手椅上阅读的。
有趣的是,罗伯特·洛威尔虽不看好戏剧,他本人却未能抵御戏剧的诱惑。他曾于1960年代将霍桑和梅尔维尔的小说改编成戏剧剧本,在其随笔集《臭鼬的时光》的一篇文章中,他甚至承认那几年他“对戏剧比对诗歌更有兴趣”。他将诗人对戏剧既不屑又渴望的复杂心态比喻为“一段郁郁寡欢、痴迷追求的恋情”,因为“它很少超越追求再进一步,得到的只有伤疤和屈辱,从来没有婚姻。”在洛威尔看来,诗歌与戏剧的关系不是亲密,而是对立——前者被认为是高深的艺术,后者则是大众流行文化;前者很少被阅读,后者却能轻易享有喧嚣和掌声——这或许正是诗人们无法不被戏剧吸引,又难以征服对方的原因。
经出版社授权,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从近日译介出版的《臭鼬的时光》一书中摘选“诗人与戏剧”一章,以飨读者。

《臭鼬的时光:罗伯特·洛威尔文集》
[美] 罗伯特·洛威尔 著程佳 译
广西人民出版社 2020-06
《诗人与戏剧》
**文 |罗伯特·洛威尔 **译 | 程佳
最令英国戏剧舞台痛苦的人,不是弥尔顿——它的敌人,而是莎士比亚——它的朋友。我在这里有所迟疑,是因为批评的麻烦在于总是要提出观点。莎士比亚对他同时代的年轻剧作家福特和韦伯斯特,或者德国浪漫主义剧作家克莱斯特和毕希纳,或者其他形式的艺术家,比如威尔第和他的歌剧、陀思妥耶夫斯基和他的小说,都没有造成伤害。优秀的诗人写过无数糟糕的英雄体剧本,他们模仿莎士比亚,但这个莎士比亚却蒙蔽了我们。他以某种隐秘的方式阻止我们上演新的戏剧。易卜生和后易卜生时代的那些模仿,堪称是最好的舞台表演剧,但似乎从未达到过伟大文学应该具有的那种启示高度。我觉得,莎士比亚甚至强迫了他最著名的挑战者——萧伯纳,我们最有天赋的现代剧作家——进入复辟喜剧那种次要模式。
柯勒律治也许是第一个认为莎士比亚太过伟大、不适合任何舞台的评论家。他喜欢读莎士比亚的戏剧胜过看那些戏剧的演出。如今没有人接受这个观点。我们都知道,莎士比亚是一个演员和剧院老板,他太实际、太不浪漫了,不可能不去为市场写作。然而奇怪的是,柯勒律治占了上风,一百年来,没有一个严肃的批评家试图反驳他。《李尔王》《安东尼和克利奥帕特拉》依然不受欢迎。A.C.布拉德利把莎士比亚笔下的人物说成是真实的人物,现在遭人嘲笑,但他可能还没有他的对手——格兰维尔巴克和E.E.斯托尔——那样迂腐过时,后两者解释那些戏剧就是戏剧。当然,对莎士比亚的意象、节奏和生动的语言进行研究,跟表演并没有太大关系。艾略特写过一篇关于莎士比亚的最具启发性的评论文章,阐明莎士比亚的诗歌可以改编成《枯叟》风格的戏剧独白。作为莎士比亚的译者和一名艺术家,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比任何现代作家都更接近莎士比亚,他把莎士比亚看作是未能如愿以偿的福楼拜或托尔斯泰,他认为莎士比亚已被他那个时代所裹挟,不得不去写剧本而砍掉了诗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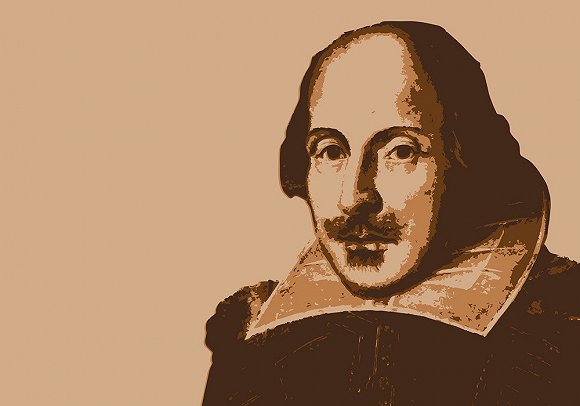
威廉·莎士比亚 图片来源:图虫
我们的戏剧舞台一半是鱼,一半是人;一半是大众文化,一半是高深艺术。也许它拥有这两个世界最好的东西,但有时,人们会用一种带有偏见的眼光来看待它,想知道是否有人真的感到愉悦。尽管它很受欢迎,但也并不是普遍流行。那些自然喜欢电视、电影、棒球和其他体育运动的广大观众很少去剧院看戏。即使他们去看了,离开的时候也会觉得自己被兜售了一些人造的、昂贵的、小圈子的、“高尚的”高雅之物。一百五十年来,戏剧既把诗人迷得欲罢不能又让他们恨得咬牙切齿。通常只有愤恨,比如伊沃·温特斯就曾说过:“总的来讲,我认为这个世界根本不需要演员。他们的本领不外乎三种——让粗俗不堪看起来是可以接受的平庸,让可以接受的平庸看起来仍然平庸,让高贵显赫看起来是可以接受的平庸。”温特斯还说过更过火的话。意识到如果不喜欢演员就不可能喜欢戏剧,于是他把后者描述为“一个杂种形式……如果读剧本,大部分都很无聊。如果演出来,可以肯定很多都会被处理得很糟糕”。对他来说,散文写的戏剧近乎于情节的拼凑,即使是《麦克白》,似乎也常常是莎士比亚与中士手枪(Sergeant Pistol)的合作之物。
在这里,我对温特斯的理论并不感兴趣,我感兴趣的是他的激情和偏见,他感觉戏剧舞台体现的是道德虚无主义。这当然是一种荒谬的故意不正经的态度,但又是我们大多数人有时都会持有的态度,尤其是诗人,他们很难平静地看待戏剧。没有哪两种艺术比我们的诗歌和戏剧更具有对立性。与诗歌相比,戏剧,即便不在百老汇上演,即便是个赔本的生意,也是一种非常流行的媒介。尽管剧作家在取得成就方面要比其他作家困难得多,尽管他失败之后一无是处,可是,一旦他成功了,喧嚣的赞美声就会不绝于耳、难以置信,他的热门作品在国内几乎人尽皆知。然而,我们戏剧的文学声望却是摇摆不定的。即使是伟大的奥尼尔,甚至是威廉姆斯,似乎更多是处于我们高级文化的边缘,成不了它的一分子。他们是被观看的而不是被阅读的,把他们归为作家都是勉为其难的事。
另一个极端是我们的诗人。他们很少被阅读,也引不起什么轰动,靠补助津贴过日子。然而,一旦有作品得以出版,即使销量不存在,奖励却很多,而且诗人享有平静的、毋庸置疑的、稳固的声誉。我们的诗歌可能不关注自己的国家,甚至不涉及人类,但至少诗人所写的是文学。

罗伯特·洛威尔 图片来源:Tony Evans/Getty Images
商业化的乡村道德家的声音,想必是我们这个社会最廉价的声音。抨击纽约很容易,但是,当戏剧界人士预言百老汇正处于严重的财政危机时,人们又高兴不起来了。有时候,人们会得到这样一种印象:每一部美国戏剧的创作、制作、导演、表演和宣传,都是由一台机器,由一个城市的一整套机器系统来完成的。人们不敢承认,纽约的这种资源和精密程度已经不复存在了。
诚然,我一直对这个戏剧舞台感到困惑,对它知之甚少,而且一听到要我为它写作的建议,我就浑身直打哆嗦。这些建议通常来自戏剧界人士,他们设法暗示我,说我的诗是私人随笔,是一种次要的专业形式。也许是我那颗阴暗的心被曲解了,也许是我暗示过他们,说现在所有上演的热剧,都不过是装腔作势的表演。然而,两年前,我在翻译拉辛的《费德尔》时,我发现我对戏剧比对诗歌更有兴趣。然后,去年夏天,我就写了一个自己的剧本(此指他对麦尔维尔的中篇小说《贝尼托·塞雷诺》的改编。——原注。)我现在觉得自己是个两面派,看待戏剧就像一个野蛮的高卢人或哥特人第一次看见罗马一样,蓬乱的脑袋里既充满了道德上的厌恶,心里又想要掠夺和适应这座城市。
很久以来,诗人,尤其是英国诗人,跟戏剧有一段郁郁寡欢、痴迷追求的恋情。它很少超越追求再进一步,得到的只有伤疤和屈辱,从来没有婚姻——因此,诗人的优越论调中掺杂着一些嫉妒、空洞和好辩之物。我希望能在《力士参孙》的序言中找到这方面的恰当例子,证明弥尔顿写这部剧,是出于对希腊悲剧的热爱和对现实英语戏剧舞台的憎恨。毕竟,是他的清教徒同胞在弑杀查理一世之后,又用长铁钩弄倒了伦敦和地方剧院的围墙。但我在他的序言中找不到可以佐证的东西。弥尔顿一心只想把自己的编剧方法和标准讲清楚,没有时间对没落的戏剧冷嘲热讽。弥尔顿在证明自己的观点时不同于其他诗人,《力士参孙》在戏剧上有三点无人能及:它是最后一部伟大的英国诗剧,它是最后一部任何形式的伟大的英国悲剧,它是唯一不能演出的伟大的英国戏剧。弥尔顿就跟他自己笔下的主人公一样,执而不化,充满英雄气概,把这座圣殿推倒,压在了每个人身上,特别是诗人,而这个诗人可能还想用英语戏剧进行一些尝试。
这就让人想起弗吉尼亚·伍尔夫的一个故事,她在写《奥兰多》的时候,艾略特突然闯进来,以一种非比寻常的热情说道:“我刚刚读了乔伊斯的《尤利西斯》。我恐怕小说在我们的有生之年已经终结了。”《力士参孙》本应该让每个人都停下来,但它从未做到,《尤利西斯》也没有终结包括《奥兰多》在内的小说写作。专业散文剧作家继续创作令人愉快的喜剧和有瑕疵的悲剧。诗人们继续在文学的墓地里写满夸张的诗剧,演起来很困难,读起来也要命。
1963—1964年
本文书摘部分选自《臭鼬的时光:罗伯特·洛威尔文集》一书,经出版社授权发布。
 简体中文
简体中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