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警察跟踪和搜查佩戴医用外科口罩的黑人男青年,以免自己染上新冠病毒。一名被甩掉的男青年坐在电脑前发布和前任伴侣的性生活照片。一名法官命令小偷站在商店外面手持标语高喊:“我是个肮脏的窃贼。”一名教师让不服管教的男生当众出丑。2005-2019年间播出3300余次的节目《杰里米·凯尔秀》对机能不全的家庭、未婚青年和“爱情骗子”大加嘲讽。一名嘉宾在一场(不靠谱的)向爱人证明自己“忠贞不渝”的真心话大冒险游戏中落败后自杀,而独立电视台(ITV)的对策只是停播这档节目。
这些事例有一个共性:它们都涉及蓄意羞辱他人。“羞辱(humiliation)”一词来自拉丁语humus,有地面(ground)之意:羞辱某个人,就是将其推倒在地,矮化其自尊,或曰奚落。
羞辱的有效性在于它可以激起痛苦的感觉。犯人被狱友性侵后所体验到的羞耻,可能会令其患上创伤后应激综合征。一名失业的父亲会因买不起运动装备、致使女儿无法加入球队而倍感难堪。一名低收入移民宁可挨饿,也不愿意去本地的赈济机构求助。
羞辱总是在某种程度上与他人相关。与羞耻类似,它从根本上讲是一种社会性情感:要有观众才会起作用。羞辱由某人或某一群体加诸于权势更弱的他人或其它群体身上。羞辱行为的目击者通常会感到自己在道德上比被羞辱者更优越。不过,很重要的一点是,虽然它是一种社会性情感,但一个人也可能在无人在场的情况下感到被羞辱,原因在于受害者业已内化了一系列对自身有攻击性的社会价值,他们会在想象中认定自己已经被“打倒在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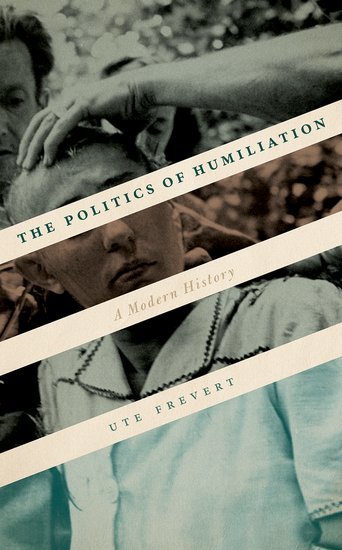
《羞辱的政治学》
羞辱行为并不“仅仅是”符号性的暴力,其效果是实实在在的。羞辱可以激发沮丧、焦虑或是自我仇视。它可以引发破坏性的行为,包括性与社会机能的失常、吸毒、酗酒以及自残。它令人陷入极度孤立,因为它蕴涵着对他人评判的承认:我是不合格的、肮脏的以及有污点的。以此观之,羞辱既是一种社会性情感,也具有某种孤立作用。
羞辱某个人也是一种政治行为。说到底,诸如此类的做法有失公正:其灌输乃是透过各种权力关系来完成的——包括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势利眼或阶级间的鄙夷。最近几十年来,电视及其它大众媒体上所谓“穷人色情(poverty porn)”的发达就是一例。诸如《杰瑞·斯普林格秀》和第五频道的《吉普赛人论益处与骄傲》(Gypsies on Benefits & Proud)等节目完全就是围绕羞辱来编排的,这些节目让观众可以嘲讽本就处于弱势地位的人。此类节目助长了诸如“白垃圾(white trash)”、“叫花子(scroungers)”和“废青(chavs)”等贬抑性词汇的使用。其后果不可小觑。羞辱会模糊贫困的结构性成因,领受福利的人感到羞耻,继而认为问题出在自己身上,而非不公平的就业市场。通过将穷人形象漫画化,羞辱表演也让削减福利额度或社会住房的做法显得有理了。
乌特·弗雷沃特(Ute Frevert)的新书《羞辱的政治学》( The Politics of Humiliation )旨在帮我们更好地认识这一复杂且经常具有破坏性的情感。这本书三年前曾以德语出版,如今因亚当·布雷斯纳汉(Adam Bresnahan)出色的译笔而有了英文本。
弗雷沃特深入考察了18世纪至今欧洲各种有关羞辱的实践和符号。身为历史学家,她著述颇丰,另外对人类学、政治学、哲学和社会学也均有涉猎,兴趣极为广泛。羞辱在国家司法系统和国际政治中的角色以及在学校和学生群体中的社会化功能,都是她的关注点。针对军中和媒体上的羞辱行为,她也下了不少功夫。自始至终,她都对问题的语境十分敏感。

乌特·弗雷沃特
过去几十年来兴起了一场运动,旨在揭示情感更多是历史建构的,而非“自然”或普遍的,她的书也属于该运动的一分子。实际上,身为柏林马克斯·普朗克人类发展学会情感史研究中心的负责人,她已经是这个领域的带头人了。
情感史家有一条公理,那就是感受具有可变性(mutable),它们有社会性和政治性的生命。这些学者认为,透过考察特定社会中与情感表达相关的一系列规则,我们就能在相当程度上了解这个社会的组织。探索这些规则随时间而变迁的方式,可以帮助我们洞察相应社会的价值观、意识形态、制度结构和身份认同的构造。
弗雷沃特认为,虽然人们总是会受到多种形式的羞辱,但引发此种情绪的源头以及回应它的方式则会随着时间而变化。简言之:人们学会了何时受辱。如果一个人生在极左派或者传统的长老会家庭里,这一点就不无意义;如果一个人是女性或者少数族群,它就更非无关紧要。权力决定了一切。
语境也一样。18世纪的羞辱实践不同于20世纪或21世纪。例如,在早期现代,违反社会风俗的人会在市场或教堂广场上遭到公开羞辱,并可能蒙受不同程度的暴力。婚外生子的女性可能会被强迫戴上“干草皇冠”站在教堂外;更具危险性的羞辱形式包括上枷锁或者关禁闭;犯了事的人会被投掷粪便、腐坏的食品甚至于石头。1780年4月11日,英国就发生了一桩臭名昭著的羞辱,马车夫威廉·史密斯和粉刷匠西奥多修斯·里德被控在伦敦的莫德林咖啡馆有“鸡奸行为”。他们被迫戴上枷锁,于圣玛格丽特山( 非真正的山脉,为18世纪伦敦的一处公共场所——译注 )示众。他们的罪行被认为极其严重(也许足以被绞死),围观群众达到了两万人。当时的一家报纸称,“史密斯站了大约半小时后,一块石头打在了他的右耳下方。(他)满脸黢黑,血从耳朵里喷涌而出,”不久后即死去。第二天,埃德蒙·伯克在议会里“历数枷刑的残酷性”,他敦促政府“废除这种原本只是为了公开地让某人领受羞耻和责备,但却被愤怒的暴民或无知的官僚用来滥施刑罚的东西”——羞辱是可以杀人的。
借助于史密斯和里德的悲剧性故事,弗雷沃特的分析触及到了某些个人化的羞辱经验,但她也表示,羞辱通常而言是政府行为。在纳粹德国,它导致了非人化和谋杀。在二战刚结束的那段时间里,新解放国家的女性通敌者会被公开剃光头,目的在于将她们驱逐出道德共同体。这种形式的羞辱因罗伯特·卡帕而闻名,他拍下了23岁的西蒙尼·图索(Simone Touseau)在沙特尔(Chartres, 巴黎西南小城——译注 )街头抱着三岁大的孩子和爱人——一名德国兵——一同被众人追着嘲弄的瞬间。
给女人剃光头如今依旧被视为是一种极端的羞辱。2015年,在华盛顿州的塔科马,年仅13岁的依琪·拉克萨玛娜就被父亲剃了光头。她当时正把一张自己身着运动内衣和紧身裤的照片发给一个男孩,不料被父亲发现,其父随后剃光了她的头发并将过程拍成了视频。该视频传了出去,使她遭到学校里朋友的讥笑,最终导致她自杀。与战后对欧洲女性的公开羞辱不同,拉克萨玛娜所蒙受的羞辱是被社交媒体塑造并强化的。互联网一方面令鄙夷姿态能够以极不对等的方式展现出来,另一方面,其提供的匿名性也让人有了借虐待行为取乐的空间。

在二战刚结束的那段时间里,新解放国家的女性通敌者会被公开剃光头
拉克萨玛娜的悲剧还提醒我们,儿童和青年面对羞辱是尤其脆弱的。从历史上看,学校运用羞辱来规训学生的例子比比皆是。学生如果违反了某些武断的规则,就会被迫戴上蠢人帽或在角落里罚站。女生可能会当着众人的面被打手掌心,男生则会受光胯之辱。这类做法存在了相当长一段时间:英国虽然在1960至1970年代就在公立学校中禁止了体罚,但正式禁止则要等到1987年,私立学校中的体罚直到1990年代末期都还是合法的。时至今日,美国某些学校里的老师依旧有打学生的权力。
弗雷沃特提醒我们注意两个颇为出人意料的事实。第一,羞辱有时是一种弱者可加以运用或代表弱者的武器。例如,在19世纪的英格兰,打老婆的男人会被拉到村里游街并接受人们的嘘声和倒彩;举行罢工的德国工人会把“脓疮”们的名字贴在灯柱和工厂门口;直到1970年,意大利的工人还会用“粗俗音乐”——一种嘲讽用的小曲——来羞辱剥削他们的雇主。
第二个人们不曾预期的变数,是某些受辱的人本身就有意寻求羞辱。共识性的羞辱在某些军队单位、小团体或者闺蜜圈子里是重要的仪式。“戏弄(Hazing,也称入会式)”仪式通常会包括一系列贬低性的或者讨人厌的行为,例如参与者可能会被要求食用或饮用一些恶心的食物或液体。他们被有意置于无价值的境地,被迫穿着傻气的服装或者被命令唱一些无意义的小调。许多仪式还有性别上的羞辱意味。然而,许多被羞辱者依旧会维护这样的实践,理由是它可以让个体成员产生一种归属感,有利于塑造一种稳固的、共享的认同。痛苦的仪式在“新人”看来可能是融入某个原本具有排斥性的“俱乐部”这一神秘过程的关键所在——当然,你入会之后就可以羞辱别的新人了。
弗雷沃特的书讨论了两个紧迫的问题。具体说,她敦促我们更为深入地思考为什么宣称追求尊严和尊重的人会持续地以羞辱他人为乐。网络羞辱——包括“扒皮”(恶意披露某人身份)和“取消文化”(因意见不合而将某人贬为被弃绝者)——对有些人几乎具有难以抵抗的吸引力。另一方面,学者玛丽·比尔德(Mary Beard)对推特喷子们充满同情之理解的回应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从中我们可以学到互联网礼仪如何改变了人生。此外,人们也会有意运用羞辱来彰显有关人类尊严的理想。种族主义者、厌女者、反犹者和恐跨(跨性别者)者不时会被羞辱到(暂时)噤声,哪怕这些人并未真正改变看法。
弗雷沃特并非悲观主义者。她提醒我们,羞辱之所以有效,全在于有一群和加害者共享同一道德规范的观众。一旦相应的道德规范遭到拒斥,羞辱的极端残酷性也就不复存在了。“同性恋骄傲”就是一种解放主义的意识形态,它鼓励人们蔑视羞辱。在美国,同性恋群体及其盟友的标语和服装上都写着鼓励人们去追问及诉说的话语,军中的“不要问,不要说”政策也因此而渐渐松绑。
然而,尽管有不少这样激动人心的击退羞辱的故事,羞辱的效力依旧没有丧失。弗雷沃特提醒我们,有一个颇为矛盾的现象是,越是强调人性尊严,与之相违背的做法就越是令人难以忍受。但她的书的核心意旨仍在于表明,我们仍然可以做出自己的选择——例如,维护社会中边缘群体的尊严就是一项正确的选择。
(翻译:林达)
 简体中文
简体中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