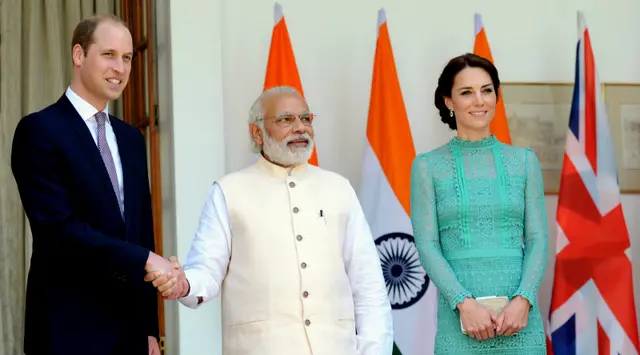读书虽然是职业书评家与职业编辑之所好,他们所最伤脑筋的便是每日邮差所带来书籍邮包的众多。
作为书评编辑,常常最被身边爱书的友人们“羡慕”的,大概就是三不五时收到的大包小包的新书了。但是他们要如何从这些包裹以及长长的书单里选出值得推荐的新书呢?这才是对书评编辑的眼力和判断力的一大考验。1982年,旅美作家董鼎山曾经写过一篇文章,专门谈书评编辑的工作方法。如果三十余年过去,翻出这篇旧文,很多其中的场景读来却也并不过时,反而有许多趣味在其中。
《书评编辑怎样工作》
友人们往往好奇地问我,美国每年所出新书数目既这么多,书评家究竟怎样挑选新书作评论?书评杂志编辑又怎样邀约某个作家写书评?
读书虽然是职业书评家与职业编辑之所好,他们所最伤脑筋的便是每日邮差所带来书籍邮包的众多。新书高高堆积,来不及打发。
每一书局通常都备有一个详细名单,列出全国各地凡有书评栏的刊物与编辑的名字。这个名单里也包括著名评论家的地址。一有新书出版,书局就按照它的性质内容,寄与各有关的杂志与书评家。邮寄的日期必须先于出版的日期,使新书在正式出售前可获得最高限度的义务宣传。所谓“义务宣传”,当然是相对性的。书评如果认为此书不好,这类“义务宣传”就成了“义务反宣传”。
书评编辑每天进了办公室,便被大堆新书所包围,随便翻阅一下,充其量只能挑出几本来加以特别注意。女作家陶丽斯·葛仑巴克(Doris Grumbach)在《新共和》周刊当了二年书评编辑后即叫苦连天的告辞。她说在这二年内,她共读了约四百五十本新书,另又挑选了五百本分发给书评家们。除此之外,她还要编辑数百篇书评,看大样等等。可见当书评编辑并不是一件易事。
陶丽斯·葛仑巴克
书评编辑如何挑书作评,也是一种艺术。由于新书的众多,重要作家的作品当然不能错过,较为次等的作家们的作品有时就只能放弃。美国的书评编辑挑书时根据下列各项条件:一、出版界内部对此书的传闻;二、出书以前的宣传;三、书局所供应的材料;四、编辑本人对新书的审阅。
书局方面当然要尽量促成新书的受注意。书局编辑或宣传部门人员会约见重要报章杂志编辑,请用午餐,宣传某一新书的重要性。书局编辑有时也会直接与书评家联络。好在这些人士都有相同的兴趣范围,经常见面谈论。问题是新书太多,因此,对新书评论之挑选,好似政治上的投票选举。书局方面的活动,等于候选政客们在选民间的活动。而新书作家们自己往往也很活跃。书局编辑、书评编辑、书评家、作家、文学代理人、出版商之间的互相交往因此不但是职业性商业性的,也是社交性的。
且让我们回到原来的话题上:书评编辑将一大堆新书翻阅了以后,已大概地挑定了几本书作评论,第二步便是决定请哪一位作家作哪一本书的评论。在这方面,各杂志的编辑方针各有不同。有的编辑认为读者并不注意书评者的名字,新书不如派给年轻书评家评论,比老书评家有更新鲜的意见。可是另有编辑却认为名家作书评很重要,有了名家的书评可以增加杂志的销路。
《新共和》创刊号(1914)
在美国这样的社会里,既要名家写,便要出重酬。以《新共和》那类杂志而论,就没有资金出大笔稿费。好在它的声望甚高,不少学术界人士就愿意写稿。因为文章登在《新共和》上,要比登在《美国社会学学刊》那类学术性杂志有效得多了,不但读者多,而且书评者自己声誉也提高。学术性杂志好似大学出版社,非商业性,销路低,因此常被读书界忽视。
写书评的除了学术界的专家教授之外,也有诗人、小说家、新闻记者等。专门以写书评为生的却很少。事实是,会写文章的都可写书评,会写书评的当然也想要写作其他永久性的文学形式。
书评编辑应怎样挑选他的书评家呢?著名文学评论家卡洛斯·裴格(Carlos Baker,也是研究海明威的专家)曾指出书评家的七个“罪恶”,要书评编辑注意:
一
“觊觎的罪恶”——妄图借用所评论的新书来替自己扬名。
二
“妒忌的罪恶”——妒忌心引致书评者抹杀他人的作品来提高自己。
三
“贪婪的罪恶”——一手垄断大批新书作评论,自己没有时间消化,却剥夺了他人的机会。
四
“越权的罪恶”——过分滥用身为书评家的权力。
五
“发怒的罪恶”——在因意见不同而引起争论时,轻易发怒而失去镇静沉着的气度。
六
“懒散的罪恶”——随意攻击作者,没有根据,在事先不化功夫作些调查工作做证明。
七
“自大的罪恶”——自己高高在上地作批评,好像自己决无过失,向作家任意挑剔。
一个公正不偏的好书评家不但必须避免上述七个“罪恶”,而且必须能够适应书评与杂志的风格。例如,把书评写成一篇严正而枯燥无味的论文,就不适用于一般的杂志。举美国两个最重要的书评杂志而言,《纽约书评》半月刊与《纽约时报书评》周刊间的风格就大有不同。前者常有长篇大论较为深刻的文学批评,后者的书评则是比较具有新闻性的短文。风格既不同,取稿标准也不同,书评家的适应能力便很重要。
我历年来在《读书》曾多次提及《纽约时报》。《纽约时报》既是美国第一号报纸,它的星期日书评附刊便也成为在美国出版界与读书界最受重视的书评杂志。我替《读书》创刊号所写的一篇就是介绍时报的书评的。这里不妨把它的编务情况解剖一下。
《纽约时报》的书评栏是双重性的。日报也每天载一二篇,由本报书评记者所写,编务完全独立于周刊。一本新书如能被日报与周刊都评论到,作者与出版者受宠若惊,兴奋异常,因为无论书评是正是反,被评的书至少引起了广大读者的注意。
《纽约时报》每年所收到的新书约一万五千至二万本,其中只有十分之一受到评论。各地书店与图书馆都依靠时报的书评作指针购书。甚至连其他杂志的书评编辑也利用时报的书评来作挑书的准绳。作家们与出版家们虽指责时报的书评太苛刻,但不少文学界人士仍以为时报的书评标准太低。不过近十年来,由于编辑人员的变换及外界的批评,时报书评的质量已大为提高。美国的报纸既靠广告收入立足,在时报书评中,文化与商业间冲突的气氛往往很浓厚。
哈维·夏皮罗
《纽约时报书评》周刊的书评大部分都是约请外界人士写。重要的书评往往出之于名家之笔。目前的书评主编是哈维·夏皮罗(Harvey Shapiro),本是一个精工细笔的文人,在文学圈中相识者众多。一般而言,周刊的内容标准往往随主编人的变换而转变。目前书评周刊质量之高,与主编人的口味不无关系。由于时报的声望,虽然稿酬不高(每篇约二三百元),应邀写书评的名家很少有拒绝的。重要的新书邀请名家评论,字数可达一千以上。较次的新书,常请其他同类的作家作评(小说家评小说,历史学家评历史,传记家评传记等),因篇幅有限,每篇书评的字数限定四百至八百字。书评家有的难免犯了上述七个“罪恶”之一。《纽约时报书评》周刊因此也辟有读者来书栏,有时成为笔战场。
时报在日报上的书评,则由本报专有的几位书评记者所写,所评之书每年约三百五十本,因此作家与出版商认为若被选中,已属荣幸,这些书评记者将新书的出版当作新闻看待,在评介时,也着重于书的新闻价值,例如:退休总统或基辛格之类达官的回忆录;读书会出了重价购买的选书;向平装本出版社出售了价值好几百万元重印权的小说等等。日报的书评字数每篇限七百五十字(美国报章杂志的一般文章着重短小精悍,避免渲染与唠叨,所以字数虽少,也还说出了要说的话)。
《纽约时报书评》封面(2015、2016,designed by SHIH CHING TU)
在美国好几千家日报中,经常刊载书评的报纸屈指可数,都是比较有名的大报,例如《华盛顿邮报》《波士顿环球报》《洛杉矶时报》《芝加哥论坛报》《迈阿密先锋报》《纽约长岛新闻日报》等。
我以前也曾在本刊替美国知识界最重要的书评刊物《纽约书评》半月刊作过介绍。这里再将它的近况补述一下。《纽约书评》是于六十年代因纽约各报大罢工而出世,暂时补填了《纽约时报书评》周刊的空缺。开首时是言论激烈的左倾刊物,现在亦因政治时势的转变而渐渐倾向保守。它的读者几乎都是学术文化界的高级知识分子,因此每期销路只不过十二万份左右。
《纽约书评》既不必迎合广大群众的较为通俗的口味,它的选书的标准也要比《纽约时报书评》为严格。它所着重者是历史与文学。书评家态度严肃,书评达到了美国文学批评的高峰。从销书的角度看,它的影响力远低于《纽约时报书评》。可是较为正经的书店及大学图书馆甚多依靠它的书评来做批发与购书的准绳。
除了这两个最重要的书评杂志外,其他辟有书评栏的刊物我已在本刊五月号的《书评与书评家》一文中论及。在过去三四十年间,书评与出版商业之间的关系颇因时势而有所变迁。大概而论,下列诸点值得有兴趣者注意:
一、由于新书出版的众多及刊载书评篇幅之少,不少新书,甚至畅销书,已不能获得重要刊物的评述,因此有人以为,也许书评与销路间并无直接关系。但在同时,迎合广大群众口味的刊物也在慢慢地对严肃认真的新书加以注意。
二、书评的影响大小与书的类别及书评刊物有关。由于近来专门性杂志兴盛,书评的影响也有变化。例如,一本科学新书的书评如在《科学》杂志刊载,效果要大于《纽约时报书评》。
三、出版商在宣传技术方面不断改进,有时感到用不着依靠书评刊物作“义务宣传”。
四、地方性的日报与杂志也逐渐开辟书评栏,因此书评的势力已不集中于少数著名刊物。
五、原版的平装书过去难得受到书评的待遇。但是此惯例也已被逐渐打破,美联社已在发行一个专评平装书的专栏,供全国各地报纸登载。
六、原版平装书出版数增多,使书评界不得不加以注意。由于书价日高,读书界与图书馆为了省钱,改变了它们购书的趋向。例如,公共图书馆与学校图书馆原以购置精装本为原则,因精装本装订与纸张均较好,可以耐久。但现在由于购书经费的缺乏及书价的增涨,不得不转而购置平装书。精装书一般价目在十五元至二十元之间。平装书有二种,一种质量高、纸张好,每本售价约七八元;一种是大众化畅销书再版的平装本,纸张较劣,每本约售三四元,但不能长久保存。
一九八二年五月十四日于纽约
(来源:界面文化)
 简体中文
简体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