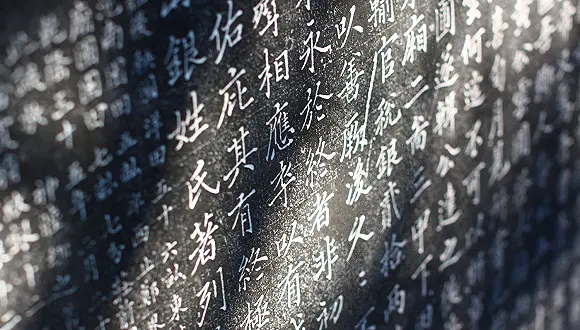近日,短视频博主Papi酱被推上热搜,让她处于风口浪尖的起因,是她在分享育儿日常时,称呼自己的孩子为“小小胡”,而她一直称呼自己的丈夫为“老胡”,孩子随父姓这一事实,使得许多女性表示不满,认为与Papi酱的独立自主的人设不符,甚至有人恶言相向,称她向男权低头沦为“婚驴”。
或许,退一万步来说,谁也没有以女权的名义去迫害女性的资格,无论是“男权”还是“女权”都有以理杀人的可能,Papi酱首先有着自由选择的权力。父权文化作为长年累月、根深蒂固的存在,也不可能指望靠着个别精英女性就能破除。要么是女权要么是女奴的二元对立思维,是否也在不自觉之间内化了“胜者为王”“各安其位”的男权逻辑?
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的思考和讨论。而作为理解这个问题的大背景,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苏力在《大国宪制:历史中国的制度构成》中有过系统分析,为何在古代中国会形成“从夫居从父姓”这种制度,是什么因素在起作用?只有充分了解了这些,对于这一问题的讨论,才不至于沦为毫无意义的口水战。
一、同姓不婚防范乱伦
在历史中国,定居中原的农耕者很早就发现近亲结婚不利于繁衍,会导致后代在智力和体能上的衰退。中国古人的长期实践表明他们完全理解这一点,因此建立了一套制度,尽可能避免血缘关系太近的人结婚和生育。
首先是用来“别婚姻”的姓氏制度。其中也包括,为落实“同姓不婚”,展开的日常教育和严格规训,因为中国古人清楚知道“非教不知生之族也”。姓氏制度以父系为中心,儿女随父姓——借此展示父系的血缘;除社会中鲜见的“入赘”外,后世全然无视母系的血缘。
若严格按照现代生物学逻辑,这种防止近亲结婚的制度不尽合理。“同姓不婚”,一刀切,会禁止血缘关系极稀薄的同姓男女结婚,甚至会禁止完全没有血缘关系的同姓男女结婚。更不合理的是,这种“同姓不婚”完全无视母系近亲,如禁止姑表兄妹/姐弟结婚,却允许姨表兄妹/姐弟结婚。
从生物学和社会学角度看不尽合理的这个一刀切,从社会实践层面看,却是更务实可行的制度。关键因素是搜寻费用。若在社会实践层面全面追溯男女双方父母的血缘谱系,一定会急剧减少潜在可婚配对象的总量。在交通不便的农耕区域内,这种实践有时甚至会令婚配不可能。
二、为什么是从夫居从父姓?
外婚制要求农耕村落所有成员都一律同他姓村落的成员成婚。除“合两姓之好”外,这一规则可确保某些父系近亲不结婚。但在农耕中国,与外婚制紧密联系的还有普遍的女性从夫居,即除非因没有兄弟不得已招婿入赘外,女性婚后一律移居丈夫的村庄,仅携带作为嫁妆的个人动产同行。
农耕中国普遍采纳从夫居的外婚制,不是偶然,更不可能仅仅因为男权。最简单的理由在于,如果男性真的如同女权指控的那么恣意、任性和霸道,那么农耕社会中的婚姻格局反倒应当是既有从夫居也有从妻居。
始终如一的大范围内的从夫居制,当然是没考虑女性的居住意愿。但光看这一点是偏颇的,因为从夫居不仅约束了女性,其实也令男性在居住上别无选择。因此,更合理的解释会是,一定有其他什么重大约束条件或制度考量,迫使农耕社会在权衡了长期利弊后,最终选择了从成本收益上看更为理性的从夫居制。
从夫居毫无疑问对女性有种种不利。她们得孤身一人进入陌生村庄,要适应陌生村庄的一切,她们一定为这一制度支付了更多代价。但就稳定农耕时代人们必需的村落社区制度而言,从夫居制确实比从妻居制,或比走婚制,从整体来看对所有人都有更大制度收益;这些收益也是,或会部分转化为,从夫居女性的收益。
理由是,在历史上各种生产/再生产关系下,年轻女性的一些特点(即所谓的社会性别,gender)令她们通常比年轻男性更能适应陌生社会环境。陌生社会或社区通常也更愿意接纳女性,而不是男性。最简单直接但很野蛮的证据是,在野蛮残酷的村落、部落或文明冲突中,胜利者会屠杀失败方的所有成年男性,通常却会接纳失败方的全部年轻女性。
从夫居制度的优势更可能在于,至少从理论分析上看,从夫居的村落会比从妻居的村落更少可能因外人进入,冲击、改变甚至颠覆本社区原有组织结构。如采取从妻居制,村落就只能按母女姊妹这两个维度组织并治理。
由于因从妻居加入该村落的男子相互间没有任何血缘关系,他们之间竞争一定会比从夫居村落中的妯娌间竞争更激烈。他们相互间不仅很难建立领导和服从关系,而且也不大可能以“妻为夫纲”原则按妻子在村落中的血缘关系位置来界定其丈夫在该村落中的坐标位置。
尤其得考虑到,在两性关系上,男子天性比女性“花心”,即有追逐更多女性繁衍更多后代的自然倾向和生物能力,更主动,更进取,也更多性冲动。这意味着这些男性更少可能接受“妻为夫纲”的制度约束和规训,更少可能恪守或能守住制度为他们规定的“本分”。
换言之,在从妻居制度下,男性更可能趋向广义的即社会文化层面的乱伦,他们不但可能追求妻子的同辈姊妹,也完全可能追求妻子的有生育能力的女性长辈或晚辈。这都趋于激发男性间更亢奋激烈的冲突。
从逻辑上看,结果会摧毁一夫一妻制,导致部分强壮男性的一夫多妻制。更重要的是,在这种激烈竞争下,农耕村落就无以构成,集体行动的成本会急剧增加乃至不可能有集体行动。从繁衍后代角度来看,这也趋于减少人类繁衍上的基因多样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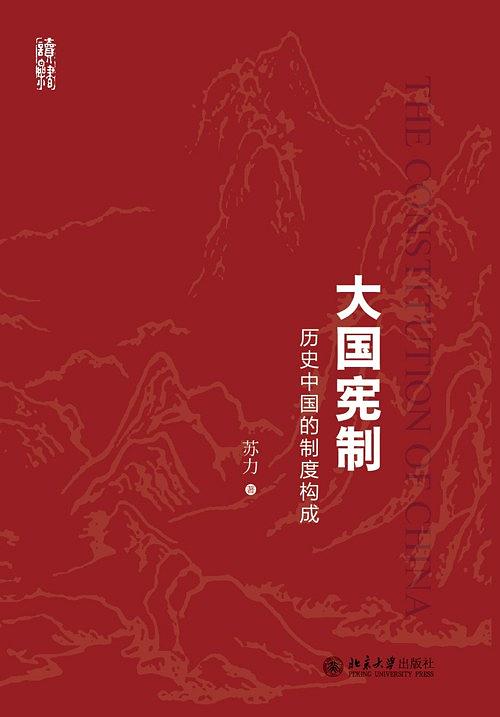
《大国宪制:历史中国的制度构成》
苏力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8-01
相比之下,鉴于女性生理特点以及相应的社会行为格局,从夫居制会全面且大大弱化从妻居制的上述风险,即便不可能消除妯娌间的冲突。这就可以解说为什么世界各地,在传统农耕村落,普遍采纳的是从夫居制。
有从妻居的现象(典型是“入赘”),却不构成普遍制度。也有摩梭人的走婚制:即让外来男性参加农耕村落的家庭关系再生产过程,却不让他们加入村落现有的政治、社会和家庭组织。走婚令男子一直游离于母系农村的组织构成之外;结果是研究者概括的“有父的生育”和“无父的家庭”。
统一的从夫居制度还有其他重要功能。一是可以减少甚至避免某些家庭内财产分配和继承的纷争。绝大多数家庭的土地资源通常不可能在短期内急剧快速增加。在这一约束条件下,若女性婚后继续生活在其出生的村落,她本人或是她的小家庭就必须拥有土地、房屋,她势必要求参与家庭财产(特别是不动产,土地和房屋)的分配和继承;这客观上会大大减少其兄弟可继承的土地等财产,很容易引发她家庭内的利益纷争。从夫居制则大大减少、全面弱化了这类纷争。
二是会减少传统农耕社会不同村庄之间的矛盾。如果女性因本村富裕不愿从夫居,又允许她招婿入赘,另一直接后果会是她出生村庄的人口会快速增长,穷村的人口则会净流失。这种现象最后会拉平富村穷村的人均富裕程度,但各村人口数量的相对增减会改变各村在当地的竞争力和影响力。人口减少力量弱化的村落会强烈不信任,甚至敌视,那些人口净增的村落。为保证力量的自然平衡,各村都趋于坚持外村女性同本村男性婚后一定要定居本村这一统一的原则。从长时段和更大的地域空间上看,这也有利于农耕文明的扩散,会激励村民向周边扩展,开拓适合农耕殖民的新区域。
三是从同姓村落的构成和秩序层面来看,从夫居制加随父姓可以有效保持和延续单姓村落。若不要求本村女儿外嫁并从夫居,只要随父姓,任何单姓村落都会很快变成多姓村落。这就没法用血缘家庭的模板和规范来组织和治理该村落了,村落的组织协调集体行动的成本会迅速增加。多姓村落会出现其他类型的男女关系风险需要甄别和防范。如,在单姓村落中,任何人都可以禁止任何少男少女的交往,就因“同姓不婚”的规则,相关信息费用几乎为零。在多姓村落中,若要坚持“同姓不婚”原则,信息和监督费用会激增,干预者首先必须甄别,交往的少男少女是同姓还是异姓。
即便多姓村落也趋于采取彻底的从夫居外婚制,即无论有无亲缘关系,是否同宗同族,一律禁止本村少男少女的交往和婚姻。这一规则从生物学上看没道理,有点暴虐,但从社会学角度看仍有不少的道理。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或许是,同村异姓男女婚后,夫妻之间难免有冲突,也难免将纠葛诉诸甚至仅仅是告诉自家亲人,但这就会把两家人卷进来。
另一方面,两家在同一村,两家其他成员之间也难免有是非冲突,这也很容易影响小夫妻的关系。因此,农耕村落至今普遍流行“嫁出去的姑娘泼出去的水”的说法,深层次的道理之一就在此。虽然算不上一则社会规范,却俨然是;至少也是一条告诫。这是有社会学道理的,并不是,至少不只因为父母偏心和歧视女孩。
上面的分析都表明从夫居制、外婚制甚或同姓村落本身其实都是制度,都承载了有效和便利构成、组织和维系农耕村落社区的功能。即便在有些村落,这些制度当初发生是无意的,但在社会和历史语境中,就因其实际功用,这些制度才被筛选并坚持下来了,有些则显然是有意创建的。
三、入赘及其背后的社会意义
当家庭没有儿子时,让女儿招女婿上门,即“入赘”就体现了这类追求和努力。入赘与农耕社会的婚姻常态有两点显著区别。第一从妻居;但重要且令人难以理解的是第二点,生育的后代会随母亲姓,不随父姓。
入赘从妻居自然便于赡养无子的老人,对于传统农耕社会的养老很是重要;这容易理解。但入赘者的后代一定要改随母姓,这又为什么?民间的说法是,为了继续这一家庭的“香火”,即这一家将来能有个后人来祭祀或扫墓。这个道理似是而非,缺乏说服力。祭祀或扫墓与姓什么无关。“不改姓就不能进祠堂,只有本族的人才能参加祭祖。”但这只是个证成(justification),不是解释。相反,应当看到,祭祖之所以有如此规定,就为了逼迫入赘者后裔改随母姓。
这就要求我们细细琢磨这一规定的意义或功能,而不是简单接受民间的说法。毕竟,在普遍随父姓的社会中,改随母姓,对这个家族来说,改姓的人也是个“赝品”,特别是考虑到在农耕中国,姓的核心社会功能是“别婚姻”。“香火说”,因此,也就是一说。
迫使入赘者的后裔改随母姓的重大功能,在我看来,最可能是要努力保持单姓村落。这样一来,入赘者的后裔就可以,也必须,继续按同姓不婚的老规矩或娶妻或外嫁,这就无需为“入赘”这一次例外而对村落原有基本制度作较大调整,也不会影响农耕村落的既有组织架构和秩序。事实上,如果只关心入赘者后裔作为生物个体的基因组合,入赘者的后裔与该村其他同辈家庭的孩子也没啥差别,都只有50%源自该村这一辈的某人。
农耕村落对姓的这种“将就”表明,这个共同体关心的并非某人的姓是真是假,是来自父系还是母系,它真正关心的,一是该村落共同体成员的实在福利,即无子成员家庭中有无男性劳动力来确保给老人养老和送终,还不增加家族中其他人的负担;二是要确保现有制度的长期稳定和有效,宁可接受以假乱真,由此来务实应对一个偶发的例外。
四、今天如何看待这一历史制度?
男女关系威胁农耕村落的方方面面,同姓不婚、外婚、从夫居/早婚等制度解决了农耕村落中男女关系的一些麻烦。
对于历史中国,苏力教授致力于用一种有关制度的理论话语来解说,为什么中国是这样的?这片土地上人们的努力,因哪些重要和基本的制度构成了这个中国?
那么今天,随着历史条件的变迁,城市生活大不同以往,如何看待从夫居从夫姓这一历史制度?如何看待Papi酱因孩子从父姓遭非议?
 简体中文
简体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