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看到著名指挥阿巴多(Claudio Abbado,1933-2014)逝世六周年的相关报道,想起一年前,我住在德国南部的大学城市图宾根,坐了十多个钟头夜行巴士到北面的柏林,为的是到柏林爱乐音乐厅,听马雷克·亚诺夫斯基(Marek Janowski)指挥柏林爱乐乐团演奏布鲁克纳的《第六交响曲》。波兰裔的德国指挥亚诺夫斯基是布鲁克纳音乐的专家,对布氏作品的演绎很精彩。
不熟古典音乐的读者,对于“哪个指挥是哪个作曲家的专家”这种说法,可能感到一头雾水,甚至对“指挥”这个角色有什么实际作用也存疑问。我在网上见过有人说,找个拍子节奏准确的人做指挥就已经胜任有余,管他高矮胖瘦。但一个人拍子再准确,也不可能比节拍器可靠。那么,怎样才算好的指挥?或许从已故意大利指挥阿巴多的故事中可以找到一点端倪。
每次去柏林爱乐音乐厅,我总会早一点到场,先吃一个夹了牛油的扭结面包(brezel),然后去商店走走逛逛。去年到柏林爱乐音乐厅的时候,大堂中间做了一个阿巴多的相片展览,因为去年是他逝世五周年。阿巴多在一九八九年接替卡拉扬成为柏林爱乐乐团的首席指挥,直至二〇〇二年卸任。每一幅展板前都有一堆乐迷驻足停留,老的乐迷缅怀过去,年轻的乐迷追忆从前。只要你是古典乐迷,你很难不喜欢阿巴多,就算没有现场看过(这是我的一大遗憾),在网上也不难找到他的指挥片段,并且为他所折服。或许阿巴多是史上最多人欣赏,同时争议最少的指挥。
李欧梵教授写过,在卡拉扬、阿巴多等指挥去世之后,世间再无指挥大师。所谓大师,都是有独特的“灵晕”(aura),像卡拉扬是充满霸气,而阿巴多则以优雅见称。当你以为指挥最重要的作用是打拍子的时候,阿巴多指挥却从来都没有一板一眼地打拍子,而是用他那只被誉为“最优雅的手”(the most elegant hand)的左手,塑造音乐的线条轮廓。如果阿巴多是最优雅的代表,那么惯常不用指挥棒(或间中以牙签作为指挥棒)的俄罗斯指挥葛济夫(Valery Gergiev),就是最不优雅的头号人物了,他在指挥的时候总是面目狰狞。
阿巴多在彩排的时候以“寡言”见称,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叫乐手聆听(listen),聆听其他声部、其他乐器的演奏,希望乐手可以自己找到平衡,做出配合。“聆听”是阿巴多最重视的事,他曾经解释为什么自己一直都留在欧洲,担任欧洲乐团的总指挥,而没有到美国出任乐团的首席指挥,是因为欧洲的乐手有更多室内乐团(chamber music)的训练,而室内乐要求乐手不断聆听乐器之间的平衡。
乐手说,阿巴多很少把指示说得很清楚,但从他的眼神中就可以知道他想怎样。这在卡拉扬身上就永远都不可能看到,因为卡拉扬除了从后台步行上指挥台的那一段路会睁开眼之外,在音乐会的其余时间,都是紧闭双眼投入音乐之中,难有“眼神”可言。
阿巴多接替卡拉扬成为柏林爱乐乐团首席指挥的时候,除了柏林围墙刚刚倒下,柏林爱乐乐团本身也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卡拉扬在晚年的时候,跟乐团的关系破裂,他曾经在彩排时跟乐团说,恨不得用一条大麻绳将所有乐手都绑起来,然后淋上火水(学名“煤油”),一把火将所有乐手烧死。乐手再也忍受不了卡拉扬的霸道横行,联手否决了卡拉扬聘请单簧管女乐手萨宾娜·迈耶(Sabine Meyer)的决定,而卡拉扬在去世之前三个月也辞任了柏林爱乐乐团的首席指挥之位。
阿巴多的徒弟之一是英国指挥夏丁(Daniel Harding)。夏丁说,阿巴多上任柏林爱乐乐团,与以往的独裁指挥(authoritarian figure)完全相反,而且将乐团拯救过来(bring the orchestra out of the dead man)。阿巴多曾经看过另一位意大利传奇指挥托斯卡尼尼(Toscanini)的彩排,后者指挥虽然厉害,但对乐手常常呼来喝去(he was horrible to his orchestra),阿巴多说这样一点也不好。
每次见到阿巴多的照片或影片,都总觉得他很温柔,难怪有团员说他“strong and gentle”。“strong”是指他对音乐的执着,“gentle”是指他的为人。柏林爱乐音乐厅的展览刊出了两封信,这两封信都是小朋友写给阿巴多的,其中一封是一九九六年一位美国初中学生寄来的,信的内容大意是:学校音乐科最近有作业谈及音乐工业,所以有一些问题想请阿巴多解答,例如他做指挥之前有没有做过其他工作?工作以外会做什么事情?还有最重要的一项:可否送我们一支旧的指挥棒去装饰墙报板。我们不知道阿巴多最后如何回复,但把这封信留到今天展出,大概可以知道阿巴多没有因为自己是名人,就对一般人认为无关痛痒的事情看轻看贱。
指挥这一行,重视师徒关系,你跟随过什么前辈、担任过谁的副手,对日后发展至关重要。夏丁除了跟随过阿巴多之外,亦曾担任拉陶爵士(Sir Simmon Rattle)的助理指挥。在这次的展览中,有一幅照片是阿巴多跟美国指挥伯恩斯坦的合照,还有一封他在一九九○年写给生病了的伯恩斯坦的问候信。一九六三年,阿巴多曾经在纽约担任过伯恩斯坦的副手。伯恩斯坦桃李满门,除阿巴多之外,艾度·迪华特(Edo de Waart)、小泽征尔等都系出伯氏(在村上春树的《和小泽征尔先生谈音乐》一书中,就谈到不少小泽先生先后跟随伯氏和卡拉扬的故事)。
回到阿巴多,他从来不会呼喝乐手,但却有点另走极端,说话太少。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阿巴多担任伦敦交响乐团总指挥的时候,有乐手说,阿巴多曾经在一次意大利的巡回演出后请乐手吃饭,在晚饭中发表了最长的一次讲话:“Thank you all very much!”在伦敦的时候,有乐手以为他寡言是因为英语不好(但他在意大利的时候也一样),也有乐手抱怨他说话太细声,常常只说单字,听起来像讲日文单字(always sounded like broken Japanese)。

卡拉扬(Herbert von Karajan,1908-1989)
托斯卡尼尼和卡拉扬等是“暴君型”指挥的代表人物,不要以为这类指挥已经消失,阿巴多在意大利锡耶纳学习音乐时的同学巴伦邦(Daniel Barenboim)就是这类指挥。巴伦邦是柏林国立歌剧院和国立管弦乐团的音乐总监,最近有乐手公开控诉,说巴伦邦一直都躁狂地对待乐团,甚至有前团员站出来说,因为巴伦邦的威吓,令他患上了高血压和抑郁症,需要接受治疗。巴伦邦是政治强人,以化解巴以冲突为己任,其实阿巴多也曾在政治上出力,他在二〇〇九年,事隔二十多年后回归米兰斯卡拉大剧院担任指挥,其中一个条件就是要米兰市政府承诺植树九万棵,改善米兰的环境。
在锡耶纳的时候,跟阿巴多和巴伦邦一起的,还有另一位同学——印度指挥祖宾·梅塔(Zubin Mehta)。在柏林爱乐音乐厅的展览中,同样展出了阿巴多和梅塔的合照(照片中还有小提琴家曼纽轩和钢琴家波里尼),以及一封阿巴多写给梅塔的信,谈到两人的友谊。两人除了是在锡耶纳的同学,还一起在维也纳学音乐。两人最初想观看一些当时著名指挥的乐团彩排,但彩排不是常常都公开,两人想尽办法,最后决定加入合唱团,从而“正面”跟指挥学习。他们当时在卡拉扬、华尔特(Bruno Walter,马勒的大弟子)等名指挥之下唱过合唱团。
阿巴多在二〇〇二年离开柏林爱乐乐团,卸任之前被确诊了癌症,经治疗之后康复。虽然大病初愈,但在二〇〇三年的暑假,阿巴多创立了琉森音乐节管弦乐团(Lucerne Festival Orchestra),乐手成员由来自不同顶级管弦乐团的乐手和独奏乐手组成,可以说是全明星阵容。英国《卫报》乐评人汤姆·瑟维斯(Tom Service)在二〇〇八年的时候就说过,琉森音乐节乐团内有八位不同乐团的首席(concertmaster),非常惊人。而这些人放弃暑假继续演出,为的就是追随阿巴多。而琉森音乐节乐团在阿巴多的指挥下也留下了很多经典的演出。
一场大病,对阿巴多有很大的影响,有人说他的优雅得到了更多的升华(这也意味着他给乐团的指令更不直接、不清晰)。但具体来看,他在很多乐曲的处理手法上有所改变,这也解答了很多想听古典音乐的人的疑问:同一乐曲,不同版本有何分别?
就算是同一指挥,处理手法也可有不同。阿巴多在柏林爱乐乐团上任的第一场音乐会是演奏马勒《第一交响曲》,在最后一个乐章的结尾马勒要求法国号的乐手都一起从座位上站起来,突出音效。彩排的时候乐手全部站了起来,而阿巴多就不停地笑,跟乐手说这个做法已经过时,把乐器提高一点就可以了,不必站起来(我后来还找到一个珍贵片段,1983年阿巴多在东京指挥伦敦交响乐团的演出,法国号乐手一样没有站起来)。到二〇〇九年琉森音乐节的时候,阿巴多同样指挥马勒《第一交响曲》,到最后的部分,法国号乐手全部都站了起来。
在展览中,有一幅照片是阿巴多的一本马勒《第一交响曲》指挥总谱的封面,在封面上,写了他每一次指挥这首交响曲时的乐团、地点和时间,刚刚提到的三场演出都有在总谱上标示出来(例如LSO,83,Tokyo)。
说了这么久,最经典的阿巴多演出是哪一场呢?我想二〇一〇年琉森音乐节乐团的马勒《第九交响曲》是无出其右之选。马勒《第九交响曲》的最后部分写着德语“ersterbend”,即“dying away”的意思,声音不断减弱,直至最后回归宁静。在二〇一〇年的这次演出中,当奏出最后一个音符之后,阿巴多仍然没有放下指挥棒,而全场观众、乐手等所有人也保持静默近三分钟,这时候你就会明白没有声音也是一种声音,音符奏完不等于乐曲奏完。即使是通过影片重看这场演出,也能感受到其中的巨大张力。
阿巴多曾经说,他最喜欢的观众是懂得静默的观众,因为观众能够保持安静的话,也是乐曲力量的一部分,像马勒《第九交响曲》、威尔第《安魂曲》等,都需要观众的合作。
古典音乐有独特的力量,而阿巴多的风格是独一无二的。今年是他逝世六周年,就算不能到柏林爱乐音乐厅看他的展览,也无论有没有在现场看过阿巴多的指挥,甚至就算你对古典音乐不太熟悉,这个时候看看他的马勒《第九交响曲》演出,你就会明白我为什么要这么写阿巴多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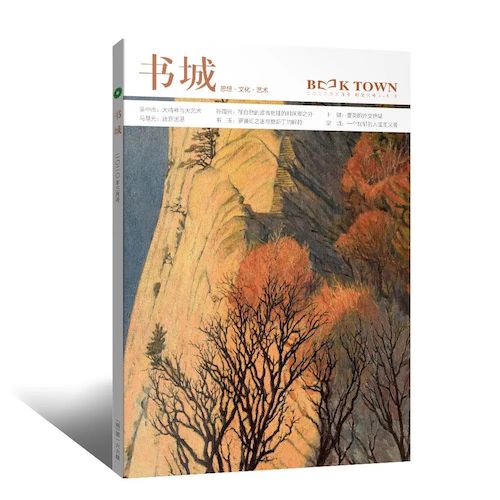
原刊于《书城》2020年3月号
 简体中文
简体中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