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在早逝之前两年反思自己的事业时,将自己描述为一个“为他人指明道路的路标,而自己却被迫在泥泞和尘埃中站立不动”的人。事实上她很少站在原地不动,但现在看来,这句自我描述显得尤其贴切——在伦敦北部纽灵顿绿地,一尊纪念她的裸体女性雕像日前揭幕,却被抹上了许多批评的泥巴。在去世几个世纪后,沃斯通克拉夫特仍然在引发争议。
沃斯通克拉夫特是一位勤奋的文学专业人士,1780年代末被卷入历史的浪潮之中,此后与历史共浮沉,这既为她赢得了名声,也引来了恶名。她是一个来自不健全家庭的不幸女孩,成长为了一个充满怨气、情感需要和知识欲望的女人。她是一个严厉的批评者,尤其是对自己。随着法国大革命的爆发,她把批判的火力转向了政治和文化上的保守主义者,从对1790年埃德蒙·伯克攻击法国大革命的激烈反驳,到对各派”专制“思想家尤其是男性特权的维护者进行大刀阔斧的攻击。她是一个酗酒家暴者的女儿,揭露男性对女性的“专横野蛮”统治,是沃斯通克拉夫特最著名作品《女权辩护》的目标。她在之后的著作中一再回到这个主题,直到1797年38岁的她在分娩时去世。
她短暂的一生以大胆和不循规蹈矩为特点。她曾告诉一位童年好友,自己宁愿“与任何障碍做斗争,而不是进入一种依赖状态”。成年后,她在资源极少的情况下,决心在英国这个阶级森严的父权社会中尽可能自由地生活。她孜孜不倦地努力自我教育,只在学校接受了最基本的阅读和写作教育,却精通四种语言,熟知启蒙思想的所有主要内容。
从19岁起,她就自食其力,生活常常陷入拮据。但当她第一个女儿的花心父亲为了一位演员抛弃她,并提出向她提供经济资助时,她拒绝了。“我不想要这种庸俗的安慰,也不会接受,”她告诉吉尔伯特・伊姆莱。她的下一个情人,激进哲学家威廉·戈德温,同样被告知她决心用笔“赚取我想要的钱”,否则就“永远睡去”。她怀着在未来写出《弗兰肯斯坦》的女儿玛丽·雪莱嫁给了戈德温,却坚持分居,并深情写道:“我从灵魂上希望你驻扎在我心中,但我不希望你总是在我的肘旁。”
然而,这种骄傲的独立,被情感上深深的不安全感,以及沃斯通克拉夫特所描述的由她年轻时的“艰苦奋斗”所诱发的“忧郁的人生观”所抵消。她很少了解或期望简单的感情,她告诉了伊姆莱,因为他也表现出自己没有这样的能力。对爱情的渴望是激烈的,而失去爱情又是无法忍受的。伊姆莱的抛弃让她两次试图自杀,哪怕她的生活和思想都以宗教信仰为基础。沃斯通克拉夫特去世后不久,戈德温出版了一本关于妻子的回忆录,对她的名声造成了长达几十年的诋毁。直到20世纪,特别是随着女性解放运动的兴起,她才有了今天的英雄地位。
“当我们被迫去感受时,我们才会深刻地辨析。”1795年,沃斯通克拉夫特这样评价自己。西尔瓦娜·托马塞利(Sylvana Tomaselli)的新作《沃斯通克拉夫特:哲学、激情和政治》( Wollstonecraft: Philosophy, Passion and Politics )在她的感情和思辨之间游走,绘制出了一幅新鲜而引人注目的肖像。从“她喜欢和热爱的东西”开始(所有章节的标题都让人联想到那个时期的小说),这本书以独辟蹊径的方式分析了她的作品 。我们了解到她对戏剧和音乐的热爱,她的阅读品味,尤其是她对诗歌的热爱,以及她对自然之美的热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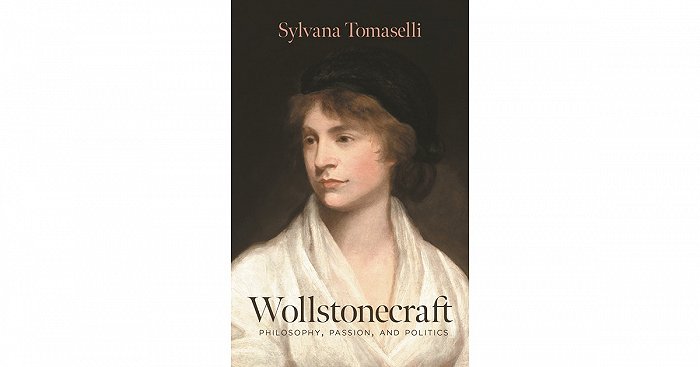
《沃斯通克拉夫特》
沃斯通克拉夫特总是被描绘成一个扫兴的人(女权主义者经常被如此形容),但在这本书里,我们可以看到她拥抱生活的乐趣。她是一个有着无拘无束的生命力的女人,我最喜欢的一个画面——虽然没有出现在这本书中——是她独自在瑞典一个山坡上,她攀爬在高高的岩石上,享受着每一分钟。我们还能看到她作为朋友和情人的样子,见证她浓烈的感情,只不过她的快乐往往被痛苦所取代。但是,如果说沃斯通克拉夫特是一个有着强烈的爱的女人,那么她也如戈德温所说,是一个“非常好的憎恶者”——西尔瓦娜·托马塞利这本书的大部分内容,都在讲述她对社会的憎恶,以及她如何旨在改变这个社会。
《女权辩护》让沃斯通克拉夫特成为名人,她是“女性权利的维护者”,是将女权主义推上政治舞台的“亚马逊女哲学家”,但这不是她在本书中的形象。托马塞利一方面承认沃斯通克拉夫特愤怒于社会对待自己性别的方式,另一方面又想用她的启蒙知识分子形象来取代她女权主义先驱的形象,因为她对女性的看法只是广泛的“人性哲学”的一部分。《女权辩护》作为沃斯通克拉夫特决定性作品的地位应该被“取消”,代之以《人权辩护》( 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Men ),这是她早先对伯克的回信,展现了某种在托马塞利看来她思想的基本特征:她对现代“文明”(civilisation,18世纪的一种说法)的严厉批判,以及她对建立在人类道德改革基础上的自由、平等和社会正义的“真正文明”的革命方案。
这种对沃斯通克拉夫特思想的宽泛视角,并不是托马塞利所暗示的与现有学术的彻底决裂。最近大多数研究也是如此,尽管许多人将她的政治思想与某种“主义”接轨:自由主义、公民人文主义、共和主义。托马塞利拒绝了这类标签,认为它们具有误导性和/或不合时宜。相反,她巧妙地将沃斯通克拉夫特不出名的作品(如她的书评)中的材料与她主要的非虚构文本交织在一起,以捕捉其哲学的“基调和精神”,同时突出其强烈的历史不可知论倾向,这一点从《人权辩护》开始就很明显。当“一种新的精神出现,来组织身体-政治”时,文明世界是如何走到当前的关键时刻的?这一变革时刻又会带来什么?正如托马塞利所言,沃斯通克拉夫特的所有思想都被这些问题,以及对人类潜能和神圣意图的综合信仰所框定——即使是在法国恐怖事件之后,她仍然坚信一个“更平等的自由、人类普遍幸福”的时代最终会到来。
一个勇敢的女人抱有勇敢的希望。我们更应该纪念这位勇敢的启蒙哲学家沃斯通克拉夫特,而不是作为女权主义者开路先锋的沃斯通克拉夫特吗?不,“女权主义者”固然不合时宜(这个词直到19世纪末才开始使用),但从1792年开始,“对我的性别的压迫”是沃斯通克拉夫特最关心的问题,她不断地书写这个主题,并对其进行深刻的辨析。她关于这个主题的著作会让人感到惊愕,尤其是《女权辩护》。这部作品对女性的缺点进行了激烈的谴责:她们的非理性、娇气、轻浮,以及——也许最让现代读者不齿的——女性的感性,她们心甘情愿地被“随意的情欲”所奴役。这种审查性是她那个时代前女权主义写作的典型特点,并且处于变化之中。但托马塞利没有注意到这些变化:她着手颂扬沃斯通克拉夫特的哲学家的面向,却没有追踪她的思想成长,从而削弱了她作为思想家的身份。
沃斯通克拉夫特的文章中充满了不一致和悖论。托马塞利承认这一点却并不重视,而是尽可能地寻求调和立场的互斥。但人们往往是通过这些张力来理解沃斯通克拉夫特的,这既凸显了她正在与之斗争的问题的新颖性和复杂性,也凸显了她为这些问题注入的创造性,随着了解更多和思考更多,她就会转变策略。她不是一个学者,而是一个革命者:单纯的一致性对她来说有何意义?
沃斯通克拉夫特去世时留下了一部未完成的小说《玛丽亚或,女性的错误》( Maria or, The Wrongs of Woman ),于她去世后的1798年出版。在这本非同寻常的书中,她公开为女性非法的性快感辩护(一个多世纪以来,女权主义内部没有再次提到过这个话题)。也许更重要的是,她还通过探索阶级和性别压迫之间的联系,首次尝试解释交叉性理论。沃斯通克拉夫特思想中的这些重大发展,并没有出现在托马塞利的书中,因为作为一个政治哲学家而非文学学者,作者避开了所有对于小说的讨论。
但是,我们不能把沃斯通克拉夫特的哲学家身份与发挥想象力写作的作家身份分开,正如她在第一部小说《玛丽:一部小说》( Mary, A Fiction )导言中所写的那样,写作带来的是“可能性”——无论是关于她的性别还是关于整个人类。托马塞利给我们描绘了一幅精美的肖像画,其中蕴含着丰富的见解,但要想充分领略这位被广泛(也是有争议的)颂扬勇敢、热爱自由的女性(顺便说一句,她本人并不喜欢勇敢的热爱自由的女性被描绘成一个女英雄),我们需要一幅更完整、更有活力的沃斯通克拉夫特的画像,她对自己性别的平等主义雄心壮志在今天还远未实现。
(来源:界面新闻)
 简体中文
简体中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