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前,我和位于布拉格的卡夫卡博物馆取得联系,询问对方是否开门。第二天,一位名叫芭芭拉·耶巴娃的馆员回复称,该馆将持续关闭直至下一步通知出台。“谢谢你,”她在信末写道,“感谢你的理解。”
耶巴娃女士的这句话有什么不同的深层意味吗?毕竟卡夫卡对门略知一二,换句话说,不管开着还是关着,门都会阻碍“理解”。在他的作品中,那些打开的门不许访客通过,而那些关着的门则滤除掉了另一侧竭力助人理解的言辞或行为。一扇门通向另一扇门,无法引向任何地方,也无法带来任何有效交流。从他的中篇小说《变形记》封面就看得出来,卡夫卡希望展示一扇通往黑暗的门。
然而,没有任何一部卡夫卡的作品像《审判》这样,与门产生如此紧密的联系。仿佛一夜之间,卡夫卡的小说就成了对我们的审判。此时的门,不只是为了文中主人公约瑟夫·K而开合,也为了我们这些正在努力理解变化着的世界的所有人。很大程度上来说,门的这一侧和另一侧的光线一样昏暗。好吧,这非常卡夫卡。
从一月末开始,“卡夫卡式”(Kafkaesque)就在媒体上占据一席之地。很有可能这周你就看到了某份报道,有人讲述或者引用了这个词。通常情况下,它被用于形容描述联邦、州立或当地的官僚政府,展示那些渴求得到检测或治疗的病人和前线医务工作者的困境。据韦氏词典介绍,这个词的近期搜索量迅速上涨,可以说已经像病毒一样快速蔓延。
卡夫卡有多少读者,就有多少种对于“卡夫卡式”的理解。也读者承认,自己无法对“卡夫卡式”给出准确定义,但看到相关场景,一定能立马辨别出来。作为读者之一,我发现其中一位名叫弗雷德里克·R.卡尔的传记作者似乎理解得颇为透彻。我们输入“卡夫卡式”这个词时,便能看到他的解读,“我们感觉被生活压迫或陷入困境,侵蚀着随心所欲生活的意志”的时刻。
把这句话的“生活”换成“门”,我们就成功走进了卡夫卡式的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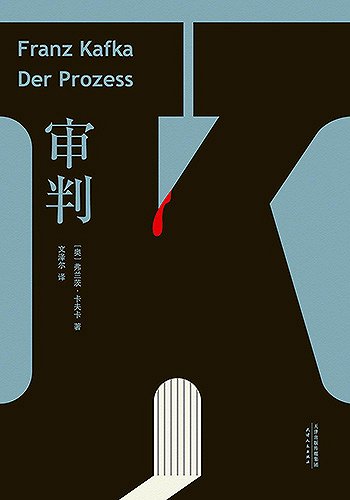
《审判》
[奥地利]弗朗茨·卡夫卡 著文泽尔 译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9-4
卡夫卡带我们匆忙跑向一扇门,小说就此拉开序幕。还在床上的K要求知道自己的早饭在哪里。此时并没有女仆来服务,而是一个奇怪的男人打开了门,身穿一套“看起来很实用,却不知出于何种目的”的制服。从这个开门的时刻起,K的世界变得阴暗晦涩。虽然依旧期盼着生活还能跟前一天一样,他还是不得已地察觉到,人生从此再也不是他自己的了。
当然,“房门被打开,陌生人闯入,人生自此发生天翻地覆变化”的经历,绝非只存在于《审判》里不知名的小城。城市名字的隐匿正像是一只闪烁着霓虹灯光的箭,指明这种经历所具有的普遍性。对当下的我们而言,出乎意料打开门的并不是陌生人,而是陌生的病毒。《变形记》中,高尔·萨姆沙变成昆虫后个人经历随之改变,但这种经历的卡夫卡式本质却并不会有丝毫变化。
如果《审判》的封面色彩绚丽,而不是暗黑色调,我们面对K的窘境会做出不同反应吗?在和米兰·昆德拉的一次谈话中,菲利普·罗斯试想了让马克思兄弟来演《审判》的电影,格劳乔演K,哈波和奇科饰演两个警卫。从猝不及防闯入格劳乔生活,到不知羞耻地偷窃他的食物,哈波和奇科的滑稽言行俨然就是那一群警卫的真实写照,他们似乎都受雇于Keystone Kop学院。当警卫向迷惑却顺从的K解释他为何不能在检察院面前穿睡衣时,人们又怎会听不见在电影《鸭羹》里格劳乔饰演的鲁弗斯·费尔弗莱询问奇科饰演的奇科里尼,“是什么有四条裤子,住在费城,从不下雨却倾泻如注呢?”“这是个好问题,”奇科里尼回复道,“我给你三个答案。”
马克思兄弟
和费尔弗莱一样,K发现尽管自己竭尽全力,却还是没能答上刚刚走进门的男人提出的问题:“你是谁?”问题似乎变成了一个谜语,警卫弗兰兹以提问作为答复:“你按铃了吗?”他当然按了,但这是个正确却毫不相关的答案。弗兰兹还不如直接对K说“我给你三个答案”。最终结果表明,不管对K还是对读者,三种猜测都不适用。我们没有人能找到答案。
这句短到可以在墓碑上刻下的话,不仅描绘了K的状态,同时对多数时间、多数地方的绝大多数人也适用。就在我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刻,我们的时代也不例外。我所住的城市休斯顿正迎来最糟糕的一切,这里刚刚宣布了封城。
虽然我的妻子已经为家庭的未来做打算,囤了不少必需品,但今早在本地超市的景象,联邦快递、UPS和亚马逊送货卡车在街道来回穿梭的情形,在让我恐慌的同时,也提醒了我,像我们这样严肃对待疫情的人只是少数。这并不奇怪。除非你住在希腊古城邦斯巴达或是新加坡,否则这就是你所在国家会做出的选择:一笑而过,掉以轻心。也正因为此,各国纷纷起草各种合约,确保政府当局的公开透明与稳定。
至少在K看来,这是政府应该要做的,所以他才试图请求法庭听听自己的申诉。最后他在一条离家很远的阴暗街道上找到了那栋破旧建筑。在楼梯迷宫中爬上爬下,K在这栋大楼里敲了无数次门也没能成功。就在快要放弃的时候,他故意问了个错误的问题:“请问有位叫兰兹的木匠住在这里吗?”然后在别人的指引下,他穿过右边的门,进入到一间狭长的房间。里面的法官正在读着色情文学,而非法典,这些人相较于教化启蒙,显然更偏爱娱乐。K和踏进房门时一样一无所知地离开了法庭,房间里污秽的气味还缠绕在身边。
他根本无暇在意这些味道,并被告知:“最后大家都会习惯的。”这的确是真理,任何时间、任何地方都是如此。
《审判》剧照
如果需要拆卸一个复杂的东西,能让行外生手做的话,为什么还要问专家呢?举个例子,如果需要解读那些像滕蔓一样缠绕脖颈的法律条文,为什么不问问艺术家呢?
在一位律师的建议下,K艰苦跋涉到更远、更衰败的城市远郊去寻找宫廷画家蒂托雷利。这位艺术家的工作室在一栋公寓顶层摇摇欲坠,阴暗得简直能被埋起来。在一群脸庞上混合着稚气与邪恶的年轻女孩的护送下,K走到蒂托雷利的门口——与其说这是门,不如说是块由不知何物拼接而成的物件:几块木板凌乱地钉在一起,留下了不平坦的宽缝。门缝宽到足够让K从这一侧看到那一侧的蒂托雷利,又能从那一侧听到女孩们还在走廊里窃窃私语。
我们又将视线重新转向了马克思兄弟,格劳乔和奇科正在做合约谈判。对于K而言,根本就没有什么明智条款。取而代之的是他有三个选择——事实无罪,证据无罪,延期。这两个男人首先就撕除了第一选项,为接下来的两个选项争论起来。两者都能让K免除有罪认定,但却无法证明他事实无罪。K因此重获自由状态,却可能在任何时候被取消。最后的结果是没有结果:一场审判结束了,另一场新的审判随时可能到来。
慌忙穿上在这间闷热肮脏的房间里脱下的外套,K蹒跚着朝门口走去,但却没法打开,因为那些女孩在门外紧拉着把手。在蒂托雷利建议下,K尝试打开第二扇门。但这扇门也被锁着,被床堵住了。直到K同意买下他几幅画后,蒂托雷利才弯腰开了门。K下楼梯之后飞速逃离了这栋公寓。
后来K发现这些画竟然一模一样:“暗淡的草地上,两棵虚弱的树彼此间隔很远的距离。” 原来,社会距离主宰着包括树木在内的一切宇宙关系。

《审判》剧照
小说里最令人困惑的门出现在一座教堂,这座教堂就像今天的欧洲教堂一样混黑孤寂。这里是K和一位想要观赏城市风光的外国商业客户约好的集合点。但这名客户并未如约现身,取而代之的是是一位神父,他从栏杆处盯着K,吼叫道:“你能看见两步之外的前方吗?”
神父为K提供了一张地图,然后给他讲起了寓言故事。这个故事多少跟卡夫卡1915年——《审判》出版前不久——出版的《法的门前》有些类似。故事里一个乡下人想要观瞻法,在四射的光辉指引中走向敞开的大门。他请求守门人让自己进去,却被拒绝了,“至少现在不能进,”守门人补充说,“后面的门更多,看门的人更凶。”这个人默默应允,在板凳上坐了下来。他就这样日日夜夜在敞开的门边坐了好多年,等待着从未到来的入门许可。直到将死之时,形容枯槁的他问守门人,为何从未见过其他想要进门的人?毕竟谁不想目睹一番这样的风光呢?“因为这扇门只留给你,”守门人回复道,“而现在,我要关上它了。”
这个寓言也令我们深受震动。过去的一个世纪,关于这个故事的解读实在是五花八门。它是否指向卡夫卡曾生活的哈布斯堡王朝里的拜占庭式人物?还是他与未婚妻菲利斯·鲍尔的关系?或是他对形而上学派意义的极力渴求?
如今四处房屋大门也一一紧闭,拥有物质和财富资源的我们会发现自己也要在很多天,甚至好几个月里坐在板凳上,思索着卡夫卡式的审判与我们现在经历的审判有何相像之处。K试图参考的错误消息,就像是我们社交平台和电视台上虚假情报的彩排。卡夫卡现代主义杰作里的地方法官和警卫,在我们这个后现代主义世界里已经颇为熟悉。最后,K的问题——“究竟哪个机构负责我的审判?”——也是如今正在经历审判的我们的问题。政府和卫生部门一直在互相批判,虽然我们都希望是后者掌握控制权,但也清楚是前者才有最终话语权。
这吸引着人们,或者说是我被引诱着作出这样的结论,虽然K最终在黑暗的采石场结束了自己生命,却不一定意味着这也是我们的命运。我冒险写下这些文字,而不是坐在政府大门前沉默等待,我们当中的很多人都渴望自己的呼声被听到。我想写的还有,有些人在藐视或指责守门人。K的审判结局是被孤立、被偏远,而我们的审判虽然也使自己被隔离,却正在变得越发团结。
与此同时,我也在尽力抵制诱惑。我们在这部“病毒小说”里的经历,就像卡夫卡的小说一样,尚未完结。
本文作者Robert Zaretsky是《洛杉矶书评》历史编辑,在休斯顿大学荣誉学院任教。
(翻译:刘欣)
 简体中文
简体中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