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饮酒就是文人名士用以消遣和激发创造力的方式之一。从魏晋时期的竹林七贤到“醉者神全”的庄子,无一不在酣饮和酒醉中抒发诗性。唐代之后,饮酒作诗几乎成了每个诗人的课题。在这方面,“诗仙”李白最有发言权——“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而与之齐名的杜甫同样是爱酒之人——“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直到晚年病痛缠身才终于“潦倒新停浊酒杯”。另一位诗人白居易不仅爱饮酒,还懂得如何饮得惬意——“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
事实上,除了爱好饮酒作诗之外,古代的诗人们也善于“以茶入诗”。相比酒文化的繁荣,茶叶在唐代之前还只是中国南方不太起眼的地方特产。8世纪中叶后,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茶园、茶商不断增多,茶叶开始在各地推广,并被文人墨客奉为会客的佳品。他们发现,茶不仅令人冷静、清醒,而且有助于长时间地坐禅冥思。茗饮的意趣也为许多诗人带来了灵感,创作了一系列以茶为主题和反映茶之美学的“茶诗”。
加拿大学者贝剑铭(James A.Benn)在《茶在中国》一书中指出,中国古代茶文化的形成很大程度上源于佛教僧侣们对茗饮的传播。在寺院中,僧人出于戒律不可饮酒,只可饮茶,原本不足为奇,但值得一提的是,寺院也是精英们交流思想与文化的重要场所。“以茶代酒”的风俗使僧侣和文人得以聚集在同一方天地,分享相同的审美观念,而不必担心醉酒的危险。
在这样的情形下,中国的茶文化、佛教的禅宗与唐代的茶诗一同兴起,相辅相成。在流传至今的茶诗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现代人赋予茶的价值,诸如天然、健康、解毒、提神醒脑等,并不是新观点,而是唐代诗人早已提出的。除了关注茶的特性和饮茶的感受外,茶诗中也常常蕴含着诗人们对充满禅意的隐居生活的向往。经出版社授权,界面文化(ID: BooksAndFun)从《茶在中国》一书中选取相关内容,以飨读者。
《唐代茶诗》
茶诗中的宗教及美学意义
据时人所言,茗饮之风始于开元间(713—742)泰山的75降魔藏禅师,然后传遍整个大唐帝国。我们不必对大约与此同时诗歌中突然出现茶而感到惊奇,因为这无非证实了8世纪中叶饮茶大为流行的其他证据,我们也不必讶异于唐诗中茶与寺院、僧人紧密关联。活跃于开元初的诗人蔡希寂提供了一个比较特别的例子,反映了此种关联,他在《登福先寺上方然公禅寺》的最后一句说到“茶果”是典型的僧人晚餐。这是现存最早言及茶的唐诗,而且很明显作者并不想强调“茶果”是很独特的物品。有趣的是,正如降魔禅师,蔡诗中的湛然也属于北宗禅一派。不管有意无意,禅宗的兴起与茗饮的发展在唐代文献资料中常常连在一起。不过,一位唐代小诗人对寺院用茶的随便一提决不能代表茶与佛教之间全面的相互影响,这一点我们能从更著名更多产的诗人之诗作中窥知。
8世纪一位声名尤著、崇信佛教的诗人王维(701—761)留下了几首咏茶诗。此外,与王维同时代的几位著名的盛唐诗人如岑参(737—792)、李嘉祐(活跃于8世纪)、韦应物(737—792)也写过一些与茶有关的诗歌。从18世纪重要的诗歌选集《全唐诗》中流传下来的茶诗来看,提及茶次数最多的唐代诗人为白居易(772—846)。但是我们要正确看待这一事实,因为白居易的茶诗不超过30首,与其诗歌总数(2800多首)相比是一个很小的数目。这一统计数据表明,虽然茶诗的内容与影响或许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但它从盛唐时期诗歌总量的角度看依然是一个微不足道的类别。

崇信佛教的诗人王维(701—761)
众所周知王维与佛教关系深厚,但其茶诗不见有明显的佛教内涵。王维传世的诗歌中有三首谈及茶。《赠吴官》中有“长安客舍热如煮,无个荼糜难御暑”。《酬严少尹徐舍人见过不遇》曰“君但倾茶碗,无妨骑马归”,从整首诗的上下文判断,这句诗说到了茶令人不眠的作用:喝茶后会恢复精神,一扫前一晚过度劳累造成的疲乏。在另一首诗《河南严尹弟见宿弊庐访别人赋十韵》中,王维描画了“花醥和松屑,茶香透竹丛”的情景,从中我们可以推断诗人家中同时用浸泡过花朵的酒和茶待客。从这三个对茶顺便一提的诗句显然可见在王维所处的时期,茶已因为能解渴、御暑和提神而为人喜爱,被广泛用作普通的饮品。王维的诗歌也表明一般人们并不觉得茶应该承载深刻的宗教或美学意义,这样做是诗人们自己的选择。
如果说王维的诗歌只是把茶放在某个背景之下或当作陪衬来描述,那么与其相反,一些同时代的诗人则把茶作为诗歌的核心。韦应物就是这样一位愿意以茶为主角的诗人,其《喜园中茶生》云:
这是一首短诗,但它包含了有趣而新鲜的观念,值得分析。首先,茶树被赋予了超凡脱俗的特点:它性洁,不能被玷污。这一观念很有可能受中古中国佛教认为万物皆有佛性的思想影响。我们知道,这一思想本来仅适用于有感情的生命,但是到了唐代甚至延伸至草木。下一句诗进一步强化了韦应物对茶的理解:茶能“涤尘烦”。在佛教文本中,“尘”通常代表蒙蔽我们本性的妄念与污垢。“烦”字意为“担忧”或“焦虑”,但也是“烦恼”之烦,它在佛教中指“烦恼障”(梵文:klesa)。因此,这些诗句既使茶具有强烈的佛教色彩,同时也呼应了《茶经》中茶能涤烦一说。而且,在诗人笔下茶树和其他植物生长在一起,正如圣人或菩萨虽意识清明,心性澄净,却混迹于凡夫俗子当中。似乎是为了强化这一宗教意味的解读,诗人又告诉我们茶有“灵”味。因此,我们可以从这寥寥数行看出唐代诗人如何有意识地把佛教教义与他们对茶这一新饮品的赞美相连,精妙的诗句由此构建了围绕茶深有影响的非世俗性审美。
新的文化空间:寺院饮茶
有时诗人把名刹的某种茶当作写作题材,有时他描述和某位高僧一起喝茶,但也有些唐诗将目光投注于在寺院饮茶的经历,这种经历及其在文学艺术作品中的表现对于贯穿后世的对茶的审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盛唐诗人岑参描写了夜宿寺院见一茶园的情形。在作于763年秋的《暮秋会严京兆后厅竹斋》中,诗人形容了茶的色与香,令人如临其境:“瓯香茶色嫩,窗冷竹声干。”对该诗而言,寺院是一个适合静思的地方——而茶最适合静思默想之时。不过,用茶待客的高官通常以人为主题而不是茶自身。例如,李嘉祐的诗歌提到了五种不同情境下的茶:春天的阳羡茶园;与荐福寺老僧“啜茗翻真偈”;送别之茶;独自饮茶;宴席上饮茶。从环境的多样化可知到李嘉祐的时代,茶已进入官僚生活的各个方面。下面我们来读其中一首以寺院为背景的诗歌:
除了茶,李诗还提及绳床。诚如柯嘉豪(John Kieschnick)所言,和佛教徒紧密相关的绳床是中国家具史(以及身体姿态史)上的重要创新。文人墨客构建了真正享受茗茶的理想化或审美化场景,文人像僧人那样坐在绳床上边啜茗边看佛偈的形象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元素。我们会看到,优雅、有意义的理想化品茗场景是始终会在明清文人的心中引起共鸣。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唐代诗人经常称赞茶激发了他们的诗兴。在唐代知识分子刘禹锡(772—835)写给白居易的诗歌之一《酬乐天闲卧见寄》中,诗人说“诗情茶助爽,药力酒能宣”,指出了茶的功能之一——正如酒能增强药效,茶能激发诗情。刘禹锡还进一步抒写了与同伴品茶的经历,即《西山兰若试茶歌》:
刘诗的独特在于他一直关注茶的物质性——其采制、煎煮与分布。它也提供了宝贵的证据,证明顾渚山上一个寺庙的僧房周围生长着茶树。在后面的几章中我们还会遇到顾渚茶,而且我们从其他资料知道,珍稀的茶叶往往长在山寺中或近旁的小块土地上。刘禹锡还述及如何为贵客煮茶——主人亲自采来最嫩的新芽炒制,然后用当地新鲜的泉水煮成一盏香茗。诗人注意到了茶叶的外形与香气,还说这种茶叶好就好在生长在竹子下面长满苔藓的地方,无意中显示了自己的鉴赏能力。有趣的是,他步陆羽后尘,也称神农(诗中呼之为“炎帝”)为茶叶的发现者,不过他把品饮这一堪称“翘英”的春茶的乐趣明确地放在现在而不是远古时期。在诗人笔下,这位僧人是具有“清泠味”之美妙“花乳”的高雅守护者和鉴赏家。他还说,寄递此茶若用“白泥赤印”缄封会有损茶味,唯有山中隐士知其真味。这里又是诗人把涉及茶之美学的许多元素集中在一起,聚焦于远离宦海沉浮的理想化寺院生活。
刘禹锡的另一首诗《秋日过鸿举法师寺院,便送归江陵》,更间接地用茶再现偶遇高僧的经历:
在这首诗中,言及茶的仅为茶烟、茶杯之句,但茶的出现显然是为了让读者把茶与僧人静思默观的生活相联结。刘禹锡的这几首诗反映了诗人们如何书写茶——是作为诗歌的主题,抑或是人际交往中用以表情达意的语言宝库中的一个元素。除了上述几例,许多中唐诗人也写诗歌咏茶、寺院、隐士,如孟郊(751—814)经常在诗中提及在寺院饮茶。张籍(767—830)的许多诗涉及隐逸、清寂的概念,并以茶入诗。客观地说,与高僧共饮茗茶的文人形象成为唐诗的惯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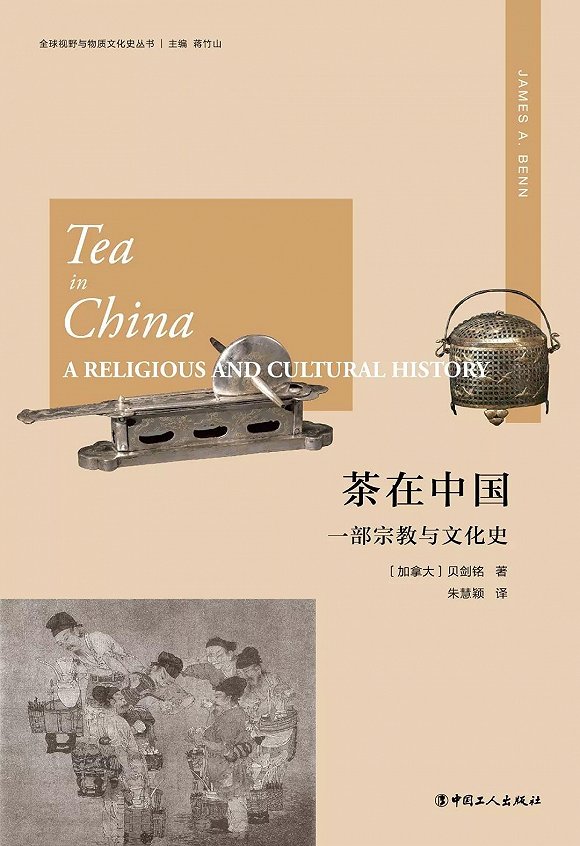
《茶在中国:一部宗教与文化史》
[加] 贝剑铭 (James A.Benn) 著朱慧颖 译
中国工人出版社 2019-12
本文书摘部分节选自《茶在中国:一部宗教与文化史》一书第四章,较原文有删改,经出版社授权发布。
 简体中文
简体中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