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顾一个人意味着什么?
当越来越多的人试图照顾被隔离的父母,得知有人在医院里没有亲人的情况下死去而心疼不已时,这个问题就在无数人的脑海中浮现。
“照顾一个人”有一个公认的含义。但在一些奇特的情况之下,它通常的意思会被颠覆。比如,从暴徒的口中说出同样的短语——“我想让你照顾某人”,可能意味着谋杀。即使是在不那么险恶的情况下,简简单单一句话的含义也可能被深深颠覆。
在我们度过当前危机的过程中,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特别是在重读了两部小说——J.M.库切的《耻》和阿尔伯特·加缪的《鼠疫》——之后。
人们在想到1999年获得布克奖的《耻》时,往往会想起一位南非的大学教授在与他的学生发生短暂而令人作呕的风流韵事后被曝光的故事。当我在一月份决定重读这部小说时,我想知道,根据最近的“取关文化”( 一些明星或名人往往因一句话或一个行为而遭遇网友的“取关”甚至抵制——译注 )和反性骚扰运动的发展,《耻》读起来是否会有所不同。
在库切的小说中,主人公大卫·鲁里是一位英语教授,当他的不良行为公之于众,他事实上在社会和职业上都遭到了驱逐。因为觉得自己与众不同,他没有按照预期的方式赎罪,但他丢掉了工作,离开了小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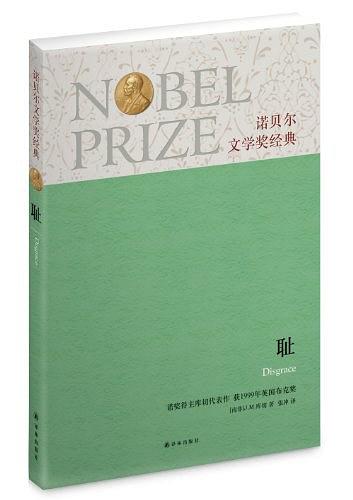
《耻》 [南非]J·M·库切 著张冲 译 译林出版社 2013-2
但所有这些只是一个序曲。鲁里去农场和他成年的女儿住在一起。在那里,他在一次入室行窃中被袭击,并被锁在一个房间里,而他的女儿在房子的另一个房间被强奸。在此之后,全书的情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如果《耻》一开始是关于当男人滥用权力时每个人都要付出代价的故事,那么它逐渐变成了另一种“耻”——在极端情况下,我们无法相互照顾的“耻辱”。
读完《耻》后,我像过去一两个月里的许多人一样,把目光转向了《鼠疫》,并惊讶地意识到这两本书在许多方面存在相似性。
加缪这部伟大的小说主要讲述了在阿尔及利亚城市奥兰爆发瘟疫期间医生里厄的故事。这本书经常被认为是一部法西斯主义的延伸寓言。但在全球流行病大爆发期间,它却被更多人当成了直接的报告文学来解读。
医生应该照顾他们的病人,拯救生命。但在瘟疫期间,里厄难以拯救任何人——在被隔离的小镇上,医生的家庭访问“变得难以忍受”。“诊断出感染意味着需要迅速移走病人。这时开始出现困难、变得抽象,因为家人知道,除非病人被治愈或死亡,否则他们再也无见到他。”
就像如今的医务工作者一样,里厄必须服从抽象的要求:将伤害降至最低。让伤害最小化优先于更多其他的人类冲动:触摸、情感、怜悯和同情。伤害最小化不仅优先于对“照顾”意义的一般理解,也优先于人类的“权利”观念。
事实证明,我们没有权利。这只不过是一种光荣的虚构。更为迫切的抽象概念,例如打败瘟疫,或者用今天的说法,“拉平曲线”,充其量让人们拥有了临时性的权利。
里厄当然会感到怜悯。他当然认为人们死时要有亲人的陪伴,应该有尊严地安葬。但在瘟疫的紧急时刻,怜悯又有什么用呢?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现在全世界的医务工作者发现自己正陷入类似的境地。在《华盛顿邮报》日前的一则视频报道中,布鲁克林麦蒙尼德医疗中心的传染病医生莫妮卡·盖坦说,她专门研究传染病,“是为了让人们变得更好”时,听起来几乎有些羞愧,她只能承认“我们能提供的东西很少很少”。

《鼠疫》 [法]阿尔贝·加缪 著李玉民 译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8-3
在《鼠疫》一书中,里厄就像奥马尔·塔哈一样,后者是迈蒙尼德医院的肺病和重症监护专家,曾将自己的角色比作军人。他明白,唯一的确定性就是工作。“其余之事都悬在线上,在不知不觉中移动着,人们不能在此纠缠不休。最重要的是要做好本职工作。”
读完《耻》之后再读《鼠疫》,令人唏嘘不已。我被加缪笔下令人钦佩的主人公、库切笔下不那么令人同情的主人公和今天在前线的医务工作者的经历之间惊人重合所吸引。
《耻》中鲁里教授的丑闻发生后,他在女儿的介绍下认识了朋友贝芙。贝芙经营着一家动物收容所,由于没有更好的事情可做,鲁里只好在那里帮忙。不久,他发现自己完成了一项任务,这实际是小说的道德中心:通过注射一只接一只地杀死被遗弃的狗。
这些狗是人类冷漠之瘟疫的受害者,甚至反映了人类更无人格的一面。“(它们)被犬瘟热、断肢、感染的咬伤、疥疮、良性或恶性的忽视、年老、营养不良、肠道寄生虫咬伤所困扰,但最重要的是被它们自己的生育能力所困扰。实在是有太多狗了。”
把这些狗带到诊所的人,希望贝芙“处理掉(狗),让它消失,让它被遗忘”。库切写道,人们要求的是一种“升华”,“就像酒精从水中升华一样,没有残留,没有回味。”
但是还有残留的尸体,这才是真正的耻辱。鲁里的工作就是处理这件事。他把尸体装在袋子里,送到医院后面的炉子里焚烧。换句话说,他“照顾”它们。
人类不是狗。但我们每个人在死后都会留下这样的残留物,一具必须处理掉的尸体,还有很多其他的东西。这一事实的耻辱可能要到死亡来临时才会打击到我们。但它会影响我们所爱的人和那些没能拯救我们的人。鲁里认为,当他按住它们不动时,这些注定要死的狗可以闻到他的耻辱和羞耻,“针找到了静脉,药物击中了心脏,腿扣住了,眼睛模糊了。”他无法习惯自己的工作。开车回家时,这个精神萎靡、道德败坏的男人不得不停车来恢复元气。“泪水止不住地从他脸上流下来,他的手在颤抖。”
但工作还在继续。鲁里因为他不太明白的原因继续做着他的工作。他只知道,“一旦它们完完全全不能照顾自己的时候,他准备好照顾它们了。”
这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所以让我澄清一下:我不是把死于Covid-19的人类比作狗,也不是把竭尽全力挽救生命的医院工作人员比作给动物注射致命药物的人。我想说的是更深层次的东西——我们人类共同的无助——《鼠疫》和《耻》都是关于人类的无助。
在库切冷酷的笔法下,《耻》实际是一本极富同情心的书。它讲述的是我们如何努力去照顾彼此,虽然有时暂时可以成功,但最终总会失败。我们可能会努力避免伤害到我们所爱的人,甚至是那些被忽视、被遗弃或不被爱的陌生人。但我们无能为力,即使是在普通的情况下,我们也无力阻止最终会发生在他们、你和我身上的一件事:经历从生到死的屈辱。
每一次死亡都会让我们明白这一点。但是,我们现在所经历的情况却让这一点变得相当残酷。病人们正在死亡,恐惧和孤独地死去,人数众多。像麦蒙尼德医疗中心贾内特·佩雷斯这样的护士们,他们在检查监护仪和重新插管的间隙,给垂死的病人唱歌,陪他们聊天。佩雷斯告诉《华盛顿邮报》,“我跟他们聊天,就像在跟我的家人和朋友聊天一样。”
在《耻》的动物诊所中,贝芙尽她最大的努力帮助动物们度过难关:“我不认为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在没有陪伴的情况下,准备好了去死。”当他们进行这项严峻的工作时,鲁里和贝芙不会说话。“(鲁里)现在已经从她那里学会了把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他们要杀的动物身上,他给这种行为起一个他不再难以启齿的名字:爱。”
本文作者Sebastian Smee是一位艺术评论家。
(来源:界面新闻)
 简体中文
简体中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