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哈通社报道,4月14日,哈萨克斯坦外交部就中国互联网上流传的一篇题为《哈萨克斯坦为何渴望回归中国》的文章向中国驻哈萨克斯坦大使表达不满,并指出文章内容与哈中两国的多边战略伙伴关系精神不符。
这篇引发外交风波的文章先是回顾了哈萨克斯坦的历史,称哈萨克斯坦与中国“自古以来渊源就非常深”,尽管中国曾多次侵略哈国,当地人却“好像并无太多怨言”,在文章末尾,作者又写道,哈萨克斯坦的一个小镇居民“坚持说自己是李白的后裔,还有一部分人说自己是汉族后裔……他们一心想回到中国”。
哈萨克斯坦不是疫情期间唯一一个“被渴望回归中国”的国家和地区。据澎湃新闻报道,截至4月15日,公众号“最新汽车的资讯”发布了近30篇名为“XX为何渴望回归中国”“XX为何从中国独立出去”的文章,吉尔吉斯斯坦、越南、缅甸果敢、印度曼尼普尔等地均被点名。这些文章结构高度雷同,大致讲述双方渊源既深,又同风同俗云云,进而可知“XX自称中国人也是有道理的”,最后抛出“该地越来越多的人因中国近年发展迅速而渴望回归”的结论。
此前,一组题为“疫情之下的XX,华商很难”的文章也在微信上获得大量关注。这些文章同“渴望回归中国”系列一样,套用同一个叙事模板进行批量生产和发布,只简单地修改其中的地名、人名等信息。尽管微信方面表示,过去的三个月里,公众号平台已着手清理了上万篇编造假消息并借疫情进行营销的文章,但此类以标题攫人眼球的假新闻却层出不穷,像是高速自我复制的塑料垃圾,不断涌入信息海洋。
假新闻的出现当然与一些人借疫情牟利有关,但屡禁难断的困局恐怕不能简单地用“人心不古”来轻轻带过:这些虚假、简陋而富有煽动性的信息像皮癣一样顽固,它们完美地迎合了后真相时代“情绪先行,事实第二”的法则,而当后现代理论、“平衡报道”、“平等主义”沦为狡辩的工具时,事实甚至连第二位也排不上。新冠疫情笼罩之下,情绪的浪潮总是比理性更先靠岸,民族主义伺机回魂,将自己掺杂在恐惧、忧虑等情绪中,借助各个渠道、各个层面的各类表述不断壮大声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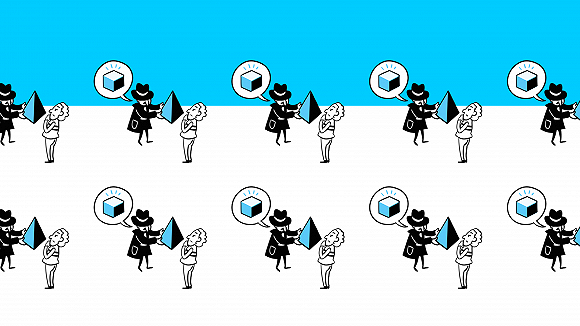
虚假、简陋而富有煽动性的信息像皮癣一样顽固,完美地迎合了后真相时代“情绪先行,事实第二”的法则。
值得警惕的是,民族主义的话语总是黏靠于历史书写。19世纪法国思想家厄内斯特·勒南(Ernest Renan)在其著名演讲《民族是什么》中指出,遗忘,甚至历史的刻意误记,是型塑“民族”的关键因素。后真相时代“大到不可知”的事实、观点与事实的混淆以及沸腾的情绪无疑加速了这种“遗忘”,更为出于种种原因的“刻意误记”批上新知的外衣。从事实到观点,没有什么在后真相时代是安全的。
后真相时代的情绪何以胜过事实?
2016年,牛津词典将“后真相”(post-truth)评选为年度词汇,用来描绘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事件中“客观事实在形成舆论方面影响较小,而诉诸情感和个人信仰会产生更大影响”的情形。
事实让位于情绪,这个描述放在今天也显得十分恰当。无论是“华商很难”的故事编造,还是“渴望回归中国”的闹剧,都产生在国内疫情趋向稳定、国外疫情日渐严峻的时间点上,利用人们的紧张和焦虑博得关注。然而,恐惧与忧虑不是后真相时代所独有的,人类历史上的战乱与危局不断激起类似的情绪,滋生谣言,但为什么是在今天这个辟谣愈发频繁和便捷的时刻,我们感受到了一种全新的不确定性?
与其说这种不确定性是因为今天的谣言和假新闻更能契合我们的偏见,不如说事实的节节败退才是引发动荡的源头。
哈佛大学伯克曼互联网与社会中心的资深研究员戴维·温伯格(David Weinberger)在《知识的边界》中区分了17世纪以来“事实”经历的三个阶段,并指出随着社交媒体的普及,当代人正处于“网络化事实”(networked facts)的阶段。他认为,“大到不可知”是网络化事实的一大特点。仅以新闻领域为例:从前,新闻的生产由专业的大众媒体完成;今天,借助智能手机和网络平台,人人都可以发布“第一现场”的相关资讯,互联网的连通使得世界上发生的所有事在理论上变得可知,事实呈井喷式增长。
事实看似空前繁盛,人类却失去了掌握事实的能力,并为此愤懑不安。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胡泳在《后真相与政治的未来》中提出,“大到不可知”的事实催生了人们对真相“愤世嫉俗的态度”,因为过于广博的事实宣告了人类总结能力的失效。在我们依据已知的大量事实作出结论时,“网络化事实”中总是可能潜藏着未知事实,我们不知道其数量多少,甚至不知这种未被挖掘的事实是否存在,于是一切变得摇摇晃晃。就像“华商真难”案例,如果不是高度雷同的格式与内容暴露其虚假性,读者很难直接断言,埃塞俄比亚没有一位从事物流业工作的徐先生因为疫情而焦虑,匈牙利没有一位开餐馆的刘小姐生意受到影响。尽管我们的理智尽可怀疑信息的真实性,但“大到不可知”的事实与“一切皆有可能”已使人在鄙弃假消息前放弃了对自己的辨别能力的信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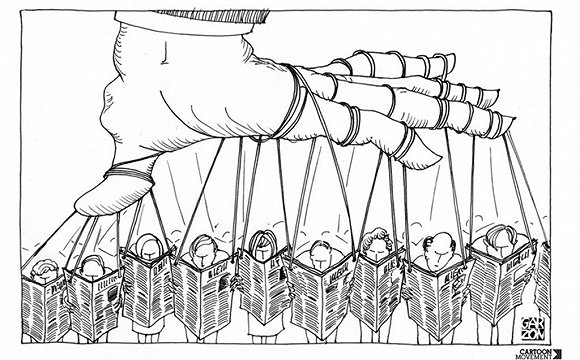
“大到不可知”的事实与“一切皆有可能”已使人在鄙弃假消息前放弃了对自己的辨别能力的信任。
更为致命的是,数量庞大且随手可得的事实便利了各种观点对它的挪用,在辩论中,举证不再是一件困难的事,每一个观点都拥有自己的“事实”。相反,查证倒成了一桩不讨喜的苦差事。既然事实来得轻而易举,那么在辩论时,大量堆叠有利于己方观点的事实就比去核查对方的事实、反思其观点更轻松、更容易实现。对现实事实的共同认知不再是讨论的前提,事实大可以与观点一起“自说自话”。
事实的井喷式增长削弱了人认识现实的信心,观点对事实的随意援引进一步消解了事实作为知识基础的价值。在后真相时代,事实的作用不过是为观点站队,两者之间不再有泾渭分明的界限。因而,说出“事实”可以和信口胡诌一样容易。事实的生产不需要经过收集、核验、整理等一系列复杂过程,它只需要被“感受”,尤其是当后现代主义告诉人们“现实是知识的建构,而知识由权力建构”后,用来认知事实的理性和事实一起遭到贬黜,“感受”成为挑战权威的先锋和认知世界的唯一手段,“情绪高于事实”也由此获得正当性。
假新闻中民族主义的后真相气质
当世界公民的理想在疫情中加速衰退时,“归国”话题逐渐成为舆论主流,“华商很难”系列文章基本都为主人公设置了“要不要回国”的烦恼。然而,在4月涌现的“XX为何渴望回归中国”系列文章中,“归国”情绪大踏步迈进,异乡孤旅的愁绪被高昂的民族主义取代,海外华人个体的选择被替代为其他国家或地区的集体表态,思来想去的犹豫也成了斩钉截铁的“渴望回归”。
这类假新闻虽然可笑,但值得注意的是,它们无一例外地寻求一种历史式的书写方式,以期增加自己的可信度。以《印度“曼尼普尔”为何渴望回归中国》为例,文章试图论证曼尼普尔是“身在‘曹营’,渴望回归”的遗落之地,却找不到什么有力证据,只好用虚假的“渊源感”来自证:首先,对“渊源”的追溯应当是推得越早越好,选用的例子应当尽可能的耳熟能详,诸如张骞出使西域、玄奘西行取经一类;其次,尽管没什么严谨性可言,但文章在用词上还是有些讲究,专门使用“自古以来”“素有”“后裔”等能够营造时空纵深感的词;最后再毫无逻辑地将这种空疏的“渊源感”嫁接到自己的观点上,造成一种“确实如此”“有几分道理”的幻觉。
历史学家罗新在《走出民族主义史学》一文中梳理了民族主义与历史书写的关系。他指出,民族的形成总是依赖于对过去的讲述,而历史是有关过去的丰饶之海。《印度“曼尼普尔”为何渴望回归中国》对曼尼普尔和中国古代王朝的稀松关系语焉不详,又对当地的王国历史、英国殖民统治只字不提,刻意遗漏其他“历史渊源”。勒南所说的“遗忘”和“刻意误记”民族型塑手段均可以在“XX为何渴望回归中国”的民族主义话语中找到例证。

“民族的形成总是依赖于对过去的讲述,而历史是有关过去的丰饶之海。”
与叙述更为严谨的民族主义史学论著相比,批量假新闻处处显示出业余的拙劣,然而,两者的思路却是一致的,也正是这种泛滥的拙劣彰显了民族主义的某种后真相气质——在网络上,人人都可以依据自己的观点和利益对作为事实的史料涂涂改改,以致于越南误把“六星旗”当作中国国旗使用的照片都能讹变成曼尼普尔“渴望回归中国”的铁证。
此外,民族主义的历史书写还呈现了后真相时代“观点事实化”的动向。除去利用后现代主义将现实解构为观点,后真相干扰认知的另一个重要方式即是把观点当作事实。民族主义时常展现出一种不容抗拒的亲昵,又用同样武断的方式排除异己,有时,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针对的乃是同一群体,可见民族主义按需变化的随意性。
勒南在他的演讲中还提出,种族、语言、宗教与地理都不是划定民族的标准,也并非民族的内容。他强调,“‘民族’是一种精神原则……‘民族’的意愿就是它唯一的合法性标准,各种标准终将汇融为这种意愿。”尽管民族主义乐于从风俗、语言、历史以及地域中挖掘自身的合理性,但民族首先是一种人类的精神意愿,是历史复杂状况的表现,不由动物起源所决定,语言、文化以及山川河流也只是这种意愿显形时的依凭,而非其实质。
利用新闻专业主义:“故事有两面”的虚假平衡
“华商真难”与“XX渴望回归中国”的制作流程一经曝光,批评自媒体消息质量低劣的声音再次出现,然批评之余,人群中并没有出现转向传统媒体寻求事实的趋向。社交媒体崛起后,传统大众媒体在新闻报道速度上一直处于劣势,社交媒体上流传的最新消息不断挑战着新闻报道的确实性,而社交媒体文本的不完整、不全面与失实也无法令公众满意。
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胡翼青在《再论后真相:基于时间和速度的视角》一文中指出,诚如社交媒体所揭示的,大众传媒的确在有组织有谋划地制造“真相”,但社交媒体在摧毁了“大众传媒客观立场”的神话后无法提供有关真相的新秩序与机制,这才是后真相的症候所在。大众传媒讲述的“真相”(truth)随着其功能和意义的解构走下神坛,然而,产生混乱的根源在于“事实”(facts)也被一同摒弃。事实不再是观点产生的基础,相反,它接受观点的选择和改造:民族主义者可以选择性地讲述那些温和无害的“历史渊源”,对一些“多余”和“有害”的记忆进行裁剪,如果实在找不到或者懒于寻找合用的材料,那么在“大到不可知”和“一切皆有可能”的荫蔽下捏造几个生活艰难的人物也不是什么难事。
大众传媒“挑战科学”的遭遇表明,事实次要化并不意味着观点是安全的,后真相的另一个特征是对观念理论毫无节制的滥用。上世纪50年代,科学家发现罹患癌症与烟草中的焦油有一定关系。此消息一出,美国各大烟草公司的负责人便聚集到纽约广场饭店,商讨对策,以保障自己的香烟销量。领导人物约翰·希尔(John Hill)提出,与其在业内相互竞争,搞“健康香烟”竞赛,不如团结在一起,赞助更多的“研究计划”来“打击科学”,让公众对学界已达成共识的研究结果产生怀疑。
此后的四十年里,烟草工业不断透过媒体向公众传递“吸烟不会致癌”“香烟与癌症之间的关系尚需更多研究”等消息,它们让媒体和其读者相信,烟草风险是一个有争议性的话题,“故事”存在两面,而每个面向都应受到同等重视。
美国历史学者Naomi Oreskes与Erik M Conway在《贩卖怀疑的商人》一书中指出,借用“科学研究”打压科学的“烟草策略”得以成功,离不开烟草工业对新闻专业主义的利用。Mclntyre认为,媒体对客观性的追求反而在某种程度上损害了新闻报道的确实性,主动用同等篇幅和时间报道“故事两面”的做法为后真相的“怀疑贩售”提供了可趁之机,在报道中制造了一种以虚假对抗真相的“假平衡”。一位烟草业高层人士就曾在备忘录中坦明“烟草策略”的阴谋:“怀疑是我们的产品,这是与公众心中的‘事实’相互竞争的最佳手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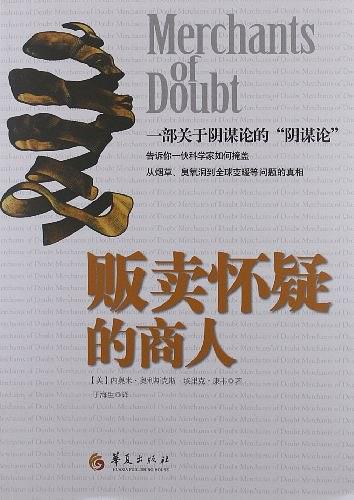
《贩卖怀疑的商人》华夏出版社2013年版
于是我们看到,科学界已有明确定论的研究结果在公众舆论中呈现出“争议性”面貌,等到公众心中的“事实”终于克服怀疑的时候,资本巨头早将巨额利润揣入囊中,留下媒体来承担恶名和指责。“烟草策略”不仅撼动了科学的权威,还找到了玩弄新闻专业主义的方法。科学的事实在后真相面前低头后,人文的事实显得更加脆弱,对“平衡报道”“两面性”“观点平等”等新闻报道原则的操纵也进一步扩散到其他领域,各种理论、理念与事实一样,尽可脱离原有语境和道德的考量,“为我所用”。说到底,当事实退居其次后,依据事实说话不再是被看重和褒奖的品质,玩弄概念成为掌控话语的捷径,在争吵的聒噪与怀疑的混乱中,谎言找到了最肥沃的土壤。
 简体中文
简体中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