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1月11日是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诞辰200周年,而近日出版的由德国学者安德里亚斯·古斯基撰写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传》或将带给我们一个重新认识陀式及其作品的机会。与市面上已有的众多陀式传记相比,古斯基的版本不仅是新作新译,而且不可避免的借助其德国视角发掘出作家不为大众所知的一面。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那些充满张力的画面以及对人性的不断拷问,也在这部新传中清晰地呈现,揭示了陀氏作为一位“危机”作家的本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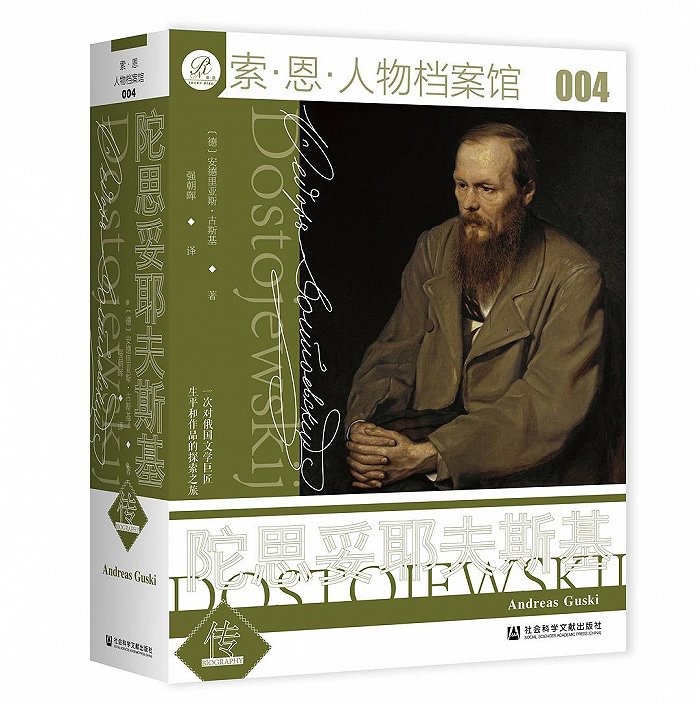
《陀思妥耶夫斯基传》
[德]安德里亚斯·古斯基 著 强朝晖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1-10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传》的新书分享会上,翻译家刘文飞与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俄罗斯文学研究室主任侯玮红共同探讨了这部作品与俄国本土陀氏传记的重要差异,以及我们在今天阅读陀氏传记与作品的意义。正如两位嘉宾指出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身上反映了俄罗斯人的民族性,他的一生都在关心人类善恶的斗争、自由和信仰的关系,以及俄罗斯民族的命运,而他人格上的矛盾、思想上的分裂,都可以在古斯基的这部传记中找到依据。
新作、新译与新的德国视点,是古斯基版陀氏传记的价值
在市面上众多陀氏的传记中,古斯基所写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传》篇幅不算长,大约有20-30万字,但刘文飞表示,他阅读时却花了更长的时间,也收获了不少新鲜感,他将之归纳为三个“新”。第一个“新”是指作者,无论对于刘文飞本人还是俄罗斯本土的俄国文学研究者,古斯基都是一个新鲜的名字。刘文飞还注意到,书中的序言写于2017年11月,也就是说这是一本近年刚刚完成就被译介到中国的作品,对于读者而言,这意味着它涉及到的有关陀氏的信息会比以往的传记更多。

活动现场(出版社供图)
第二个“新”在于这部传记是创作于21世纪的陀氏传记。刘文飞介绍道,与其他俄国作家相比,陀氏的传记在30、40年前并不多见,在俄语传记中明显少于普希金传和托尔斯泰传,这是因为在整个苏联时期,人们对陀氏的评价不是很高,有人说他是一个残酷的天才,也有人说他是反动作家。但另一方面,有关陀氏的研究著作却很多,刘文飞认为,之所以出现“研究多而传记少”的奇怪现象,可能是由于传记作家对如何评价陀氏感到为难。
尽管如此,在上世纪60至70年代,前苏联已经出现了最早的一本陀氏传记,作者是格罗斯曼,这本书在1987年被外国文学出版社译介到中国。后来,人民文学出版社于2011年出版了谢列兹涅夫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传》,是国内学者参考较多的俄罗斯人所写的传记。还有一本比较重要的陀氏传记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约瑟夫·弗兰克的五卷本《陀思妥耶夫斯基》,它创下了陀氏传记最大篇幅的记录。此外,较为人知的陀氏传记还有美国的斯拉夫学者斯洛尼姆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三次爱情》,以及陀氏夫人所写的日记和回忆录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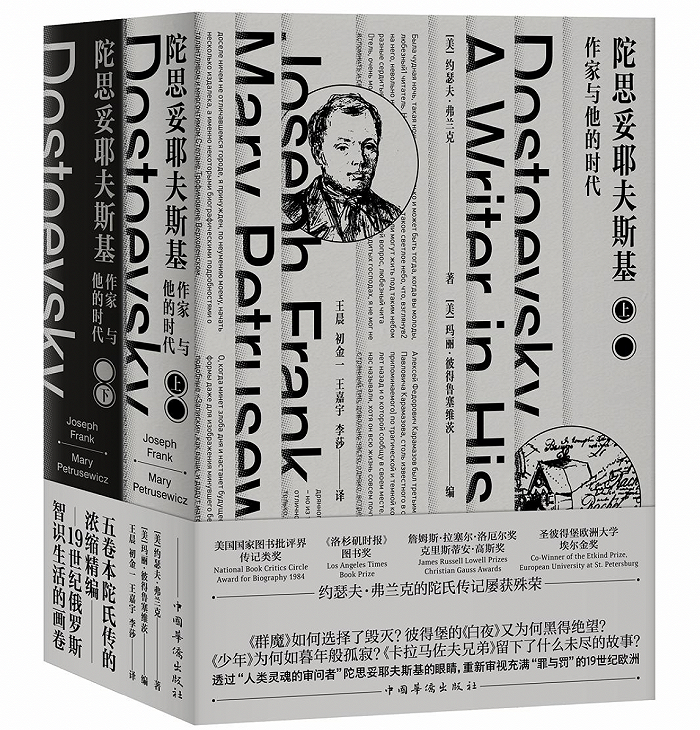
《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家与他的时代》
[美]约瑟夫·弗兰克 著 王晨 等译
三辉·中国华侨出版社 2019年
以上提到的传记大部分都已推出中译本,但刘文飞注意到,它们无一例外都是译自俄语或英语,然而,古斯基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传》却是译自德文,书中呈现出的德国视点也令刘文飞感到格外的“新”。“相对而言,它比较侧重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哲学层面、思想史层面的理解,比如我们在书中可以看到,他(陀氏)受到了很多来自康德、克尔凯郭尔、谢林等哲学家的影响。”换句话说,古斯基作为在德语文化语境中成长起来的作家,对德国哲学历史如数家珍,对德国哲学家们的理解也会远超别国学者,这一点是他写作这本传记的优势。此外,刘文飞发现,古斯基的德国视点还表现在相对浅的生活层面,比如他会格外关注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国外度过的那些岁月,关注他到过德国哪些地方——我们后来才知道,原来陀氏的很多作品是在德累斯顿和巴黎写成的,相当于“侨民文学”。
侯玮红也留意到古斯基这部传记的新意以及当代性,她还对作家叙述的方式印象深刻。“他在叙述的时候很有电影的画面感、时空感,很像拍摄时的摇臂,一会儿摇到陀氏的时代,一会儿摇到当代,让你有种互相映衬的感觉。”侯玮红记得,在写到陀氏去世以前不久,普希金纪念碑落成的时候,古斯基将陀氏和屠格涅夫在落成仪式上的演讲说成是二者之间的决斗。“屠格涅夫是贵族的、高傲的、带着自信和自恋的形象,可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却是一个面带病容的、神经质的、令人心生同情的中世纪僧侣的形象。”她认为这种对细节的生动刻画固然有演绎的部分,但作者能把演绎、想象和史料、作品以及人物等特别自然地融合在一起,的确令人感到惊喜。
想要了解俄国人的民族性,阅读陀思妥耶夫斯基可能是一个捷径
从文学研究的角度看,古斯基的德国视角也与俄国的本土视角形成了有趣的对比。刘文飞提到,俄国人看陀氏的传记会认为他是一个圣人,直到现在,俄国学者包括萨拉斯金娜所写的陀氏传记,基本上态度都是仰视的,很少在叙述时去揣测陀氏的心理或对某些争议性问题的看法,因为他们认为这是对文学圣人的解构。而在古斯基的新传中,恰好有一章的题目叫“封圣”,其中谈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葬礼开创了俄国人民为作家封圣的先例——一个作家去世以后,要抬着他的灵柩在大街上走,让成千上万的人为他送葬。从陀思妥耶夫斯基开始,屠格涅夫、托尔斯泰、马雅可夫斯基、帕斯捷尔纳克都经历了类似的送葬仪式。“作家的封圣在俄国人看来很正常,但是异域的人看,总是有点调侃和解构,何况还是在这么新的一本书里。西方的知识分子本来也有解构的传统和心态,不太想把一个作家写成圣人,”刘文飞说。
俄国内部与外部作家的另一个区别体现在他们对陀氏所代表的民族性的不同解读。刘文飞指出,俄国人更关注陀氏身上体现的俄罗斯民族意识,而俄国境外的人是把他看作最典型的俄国人,比如他的喜怒无常、极端蛮横,还有他的睿智,通过破解他来认识俄罗斯性。尽管都是要了解俄国人,但从这点上看两者恰好是相反的:前者是拥戴的,后者是挑剔的。特别是在前苏联时期,苏联官方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稍有贬低,这时西方会更抬举他的现代意识;当苏联解体以后,苏联官方把他当做意识形态代表的时候,西方反倒对他有所贬低。
在陀氏诞辰200周年之际,两位嘉宾也谈到了今天人们阅读陀氏的著作及其传记的意义。在刘文飞看来,如果想要了解俄国的文化、文学,了解俄国人的思维方式和他们的民族性,阅读陀思妥耶夫斯基可能是一个捷径。另一方面,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同时代的作家中,可能是以文学介入人的内心最深的人,因此阅读他的作品会让人更了解人的复杂性。正如古斯基在传记中分析陀氏的小说《地下室手记》时提到,陀氏将人分成两类,一类是知足常乐的人,也就是普通的人,另一类是“地下室人”,是怀疑一切的人。像“地下室人”面对世界的这种怀疑精神、否定精神,才有可能帮助人在某种意义上更完满地实现自己的个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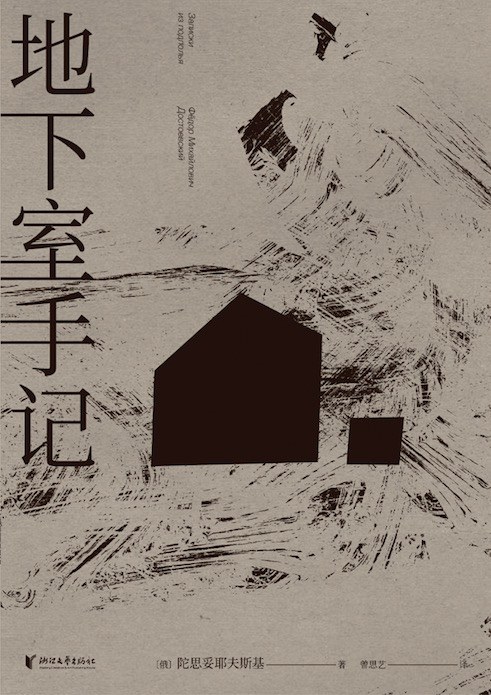
《地下室手记》
[俄]陀思妥耶夫斯基 著 曾思艺 译
果麦文化 |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20-05
古斯基的传记也格外强调陀思妥耶夫斯基身上的分裂性。熟悉陀氏的人都知道,流放西伯利亚的苦难岁月对于他后期的思想形成起到了关键作用,自此之后,对世俗生活的渴望和宗教意义上对新生的渴望这两者的分裂时刻缠绕在他的思维之中。刘文飞认为,陀氏一生都在关心人类善恶的斗争、自由和信仰的关系,以及俄国和欧洲的问题。他在晚年提出“俄罗斯理念”,认为西方因为资本主义的自私性已经失去了信仰的纯洁性,只有坚守东正教传统的俄罗斯人还在肩负一种通过改造信仰拯救世界的使命。“对于个体的人来说,他让我们看到人本身的深刻和复杂,而对于一个国家来说,他让人看到俄罗斯这个民族的发展过程的艰难和慎重。”
侯玮红则将陀思妥耶夫斯基身上的矛盾概括为个人的、民族的/时代的,以及人类的三个方面,这三方面的本质问题是人的归属感,也就是肉身的安顿和心灵的安顿。在肉身上,陀氏一生都在为健康所困扰,古斯基就提到了他所得过的疾病,包括癫痫、呼吸道疾病、头晕、多疑、焦虑等;在心灵上,他不仅对文学事业上的成就有着各种野心和欲望,还一直对信仰持一种又想坚信又不断怀疑的态度。“我觉得他身上反映了作为一个人的所有矛盾的集大成,所有精神上的困顿、矛盾、求索,往大里说,就是国家的前途问题,民族的命运问题,就是人类的问题,有点像我们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刘文飞还提到,文学的写作和阅读从19世纪至今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人们其实更多还是在阅读古典主义的文学大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可能构成我们阅读文学的一个转折和延续,因为小说写作的现代性开端正是在陀氏那里,他让人意识到故事本身不一定重要,写法也很重要,而且可以出现意识流,出现对生活的怀疑。侯玮红也认为,陀氏的影响是渗透在当代作家的血液中的,具体到文学创作,最典型的两个全面继承陀氏的批判现实主义传统的作家是马卡宁和奥列格·帕甫洛夫。因此,无论是阅读现代派文学还是后现代文学,读者都可以从陀氏身上找到源头,这也是我们在当下阅读他的理由。
(来源:界面新闻)
 简体中文
简体中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