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苗不会很快问世。头脑冷静一点的人更是认为,哪怕在最理想的情况下,疫苗也要等到2021年秋季才能上市。疫苗研发是要花时间的。大批量生产及分发的基础设施必须到位。在采购和销售之前,公司还必须走完美国食品与药品监督局(下文一律简称FDA)的审批流程四阶段中的前三个。而要通过审批,公司就需要一种对任何药物或疫苗上市而言都不可或缺的原材料:健康的人体。
首次人体试验研究(First-in-human studies)或曰第一阶段研究(Phase I studies),是临床试验里风险最高的环节。该阶段的研究仅需摸清某种药物对功能健全的人体有何影响(如是否会引起呕吐、头疼或心脏骤停)。健康的人体是一件稳定的器具,透过它科学家可以得知某种药物或疫苗是否对你有害。药物对你有益与否并非主要关注点(留待后面的阶段处理)。5月,某新冠疫苗完成了第一阶段研究。过了几天,其开发者Moderna公司就宣布该疫苗在首次人体试验研究中经受住了最严格的测试,其安全性有保证,FDA已批准其开展下一阶段试验。
在对抗新型病毒的第一针疫苗最具风险的研究环节里,究竟是哪些人在献身?鉴于参与者可以公开谈论此事,记者自然是很客气地强调了人们的责任感和爱国主义精神(它们无疑也是真诚的)。这些人没有要求金钱。FDA从其职责出发,也会按照法律要求对参与试验之人群的种族和性别进行审查。有关部门不会询问这些人参与第一阶段试验的频率高低或新近与否,该阶段试验的风险尽管最高,但参与者得到的报酬也是最丰厚的。
社会学家吉尔·费舍尔(Jill A. Fisher)在新书《不良事件》里对此提出了质疑。她在首次人体试验参与者那里得到的答案表明,美国系统性的反黑人种族主义支撑着临床试验产业,而该产业反过来让有色人种群体不成比例地陷入了经济上的不安定状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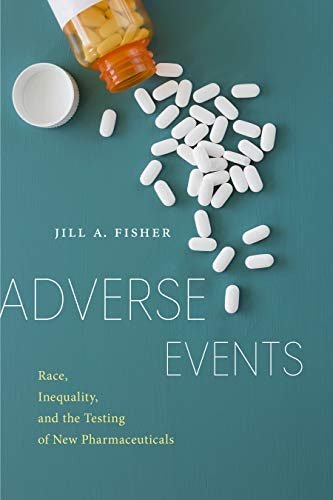
《不良事件:种族、不平等与新药的测试》
传统的看法是,有色人种在临床研究中代表性较低,原因在于其对医药界建制派的不信任。其代表性较低的另一原因,是塔斯基吉梅毒试验( 1932年起,美国公共卫生部以黑人为试验对象,秘密研究梅毒对人体的危害,使当事人及其家庭付出重大代价,此事在1972年曝光,直到1997年政府才正式道歉——译注 )曝光后,联邦法律开始保护弱势群体——尤其是美国黑人——免受医药产业的剥削,降低了该群体的试验参与度。这套说法大体上没有争议。但费舍尔表明,有色人种的参与度尽管总体上不高,但参与最危险阶段研究的黑人却多到过分,而此类研究又不太可能为参与者带来医学上的好处。
在《不良事件》一书里,费舍尔讲述了自己走遍全美,考察诸多第一阶段研究设施这一“地下世界”的故事。费舍尔访问了超过200名身体健康的第一阶段研究被试者及负责管理、训导和照料他们的工作人员,这些人分别来自东中西部的六处研究设施。她会在设施里呆上好些天甚至几周的时间,并且会和各地的受访者给这些设施取一些诸如监狱、欢乐屋或者奇妙游轮之类的诨名,具体叫什么取决于你的口味——某家没有厨房的医院会让IHOP连锁餐厅送餐,电视里播放着蠢蛋搞怪秀。不管怎样,出门都是一件难事。开展第一阶段试验的诊疗场所通常大门紧锁、没有窗户,且需要一直留宿。在安检流程中,工作人员会筛查是否有外带的食物或可疑的洗漱用品,一切带摄像头的装置也会被没收。想一下机场安检吧,它比机场安检还要糟糕一些。
第一阶段试验堪称责任梦魇(liability nightmare)。开发新药和疫苗的公司一般不会自己做试验,这并不出人意料。新冠疫苗也一样,药企通常会把试验外包给其它公司。这些私人承包商是专做临床试验的,其中更有不少只做利润最高的第一阶段试验。当中还有一些学术机构,接受药品开发者的合同是为了维持预算平衡,可见美国的健保及健康教育状况不容乐观。
“第一阶段试验可以被看成是一种对身体健康的志愿者造成伤害的协议,旨在积累试验药的安全性档案,”费舍尔写道。在试验产业里,这些伤害会被委婉地说成是“不良事件”,也就是费舍尔为新书选定的标题,意味颇为深长。她在与人们交谈时发现,白人通常来讲只会参加一次此类试验,几乎没有参与两次或两次以上的。参与过五次以上者一般都是黑人,部分人甚至参与过五十次以上的试验,其中有一名非裔美国人估计自己已经参与过百次以上的试验。

参与过五次第一阶段试验以上者一般都是黑人
偶尔参与此类试验的群体与上述这种常客(serial participants)相比,其生活境况有着重大的差异。不同于只参与过一两次或几次第一阶段试验的人群(主要是白人),常客们面临的生活困难不仅数量繁多,而且有交叉影响。他们可能失业或负有债务,或者有坐牢的记录,也可能学历不高。种族和频繁参与第一阶段试验之间的关系,目前还不够明确。但在如今的美国,鉴于种族主义对教育、就业、健保和刑事司法等领域的影响,黑人面临的不利状况与白人相比要不同寻常且不正义得多,这是不争的事实,眼下如火如荼的Black Lives Matter运动即体现了这一点。如费舍尔所言,不良的生活事件给人们带来了不良的健康事件,且这种影响不成比例。
“常客”处在一个恶性循环当中。他们把行李塞进车里,车子可能比房子还大两倍,带着新签的合同驱车前往试验设施。他们彼此会交换心得,更倾向于前往出价更高的去处。他们学会了在各种研究当中做选择(譬如:腰椎穿刺就不能去),甚至还有人考虑成立一个工会。
但工会只能让这种透过将参与者置于“永久性的经济不安定状况”来维系其劳动力再生产的零工经济更趋强化。在这种不良的经济模式里,罪魁祸首是医药产业,美国政府疲弱的规制则充当了帮凶。在奥巴马执政后期,美国政府接纳了一系列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新规定,以约束各种有人类被试者参与的研究。经过专家、业界和公众为期六年的共同努力,这一领域四十年来首次有规矩可循了。所提出的规定旨在加强对私人资助的临床试验的管制,此类试验由于不拿联邦资助,可以不用遵守某些联邦层面的规定。加强的方面主要包括:私人资助的试验必须有浅显易懂的同意书,承包商必须对参与者负起基本的责任,要接受联邦的听证。然而,由于业界的反扑,联邦政府最终决定不将规制扩展到私人产业,声称“不受规制的临床试验这一问题尚待进一步研讨”。
与新冠疫苗试验不同,费舍尔提到的那些研究里基本没有英雄可言。常客们想方设法阻止亲友团知晓其工作的性质。长期关系本就不易维系,而参与者的保密性更是一种羞耻的标志,卷入程度越深,羞耻感就越强。“如果健康志愿者相信参与第一阶段试验是一种羞耻,那么令他们在其中有坐牢或非人感的不合格设施只会加强这一信念,”费舍尔写道。
此外,还有人认为,自己或别人之所以愿意参加待遇差、工作人员培训不精的临床试验,乃在于财务上的绝望心态;反复去这类地方意味着某个人的确没有更好的选择,这使得参与此类试验的羞耻感变本加厉。
试验场所的情况当然各不相同,但其建筑类型却有雷打不动的规律:“旧仓库、旧厂房、办公园区里的套房。”参与者在研究过程中若有违规行为,工作人员便会课以“罚款”——譬如抽血迟到了几分钟——如此一来实际到手的报酬就会打折扣。这个产业根本不愁找不到愿意参与试验的人,因而也没有什么改良设施或者提高薪水的动机。
“健康志愿者、诊疗场所和医药产业都有动机让试验药物看起来是安全的。”
做全职被试者,一年挣两万美元,这对你而言想必压力极大。每天的平均收入是250美元,要满打满算地拿到这个数并不容易。除非你和工作人员关系好、从不迟到早退、服从管理且给出的数据质量高。和参与者类似,工作人员的待遇也好不到哪里去。护士、厨师和管理人员对待参与者的态度轻蔑而刻薄,但他们自己也要干不少分外的工作,而且日程极为紧张。为了保住工作,他们必须确保雇员时刻在干活。为确保雇主的利润,第一阶段试验的工作人员所提供的数据必须能说服FDA,使其相信最新的研发计划是安全的。
临床试验产业的这一格局不单单违反社会正义,它作为科学而言也是不合格的。直接捏造数据固然不常见,但工作人员会训练及协助参与者调整自己的身心,以操控数据,譬如降低血压来取得资助者所希望的结果。费舍尔解释说,“健康志愿者、诊疗场所和医药产业都有动机让试验药物看起来是安全的。”结论在研究开始之前就已经定好了。
费舍尔对试验设施的调查令人印象深刻,且来之不易。工作人员忌惮她的在场,领导们自然也坐立不安。为了得到这种绝无仅有的准入资格,费舍尔也要向对方保证,自己身为北卡罗莱纳大学的教授,享受国立卫生研究院的充足拨款,所做的只是社会科学家的中立分析,绝无任何新闻曝光成分。“这不是一个大药企如何缺德的故事,”她告诉我们,“尽管话也可以这么讲。”英国的大卫·希利(David Healy)、美国的约瑟夫·杜米特(Joseph Dumit)、印度的考希克·桑德尔·拉詹(Kaushik Sunder Rajan)等作者已经在揭露药企之恶方面做了不少颇具影响力的重要工作,人类学家阿德里亚娜·佩特拉纳(Adriana Petryna)则考察了跨国公司的各种“离岸”场地。
《不良事件》仅凭单纯的描述即足以谴责试验产业,但费舍尔的分析还有一项更大的关切。该产业乃是美国的种族主义资本主义(racist capitalism)带来的病症,费舍尔在书中如实地记录了充满种族歧视且高度不平等的经济体系是如何陷人们于囹圄并迫使其参与首次人体试验的。在十年前开始这项研究之际,她尚未预料到问题的紧迫性。
本文作者Laura Stark系范德比尔特大学医学、健康与社会中心助理教授,《历史与理论》杂志编委,著有《幕后:机构审查委员会与合乎伦理的研究的诞生》一书。
(翻译:林达)
 简体中文
简体中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