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少有女诗人像金.阿多尼兹奥一样,在作品中大胆直接地书写身体与性爱,甚至毫不避讳地将私生活作为写作的素材。这也是为何美国文学界称阿多尼兹奥是一个“丑闻缠身”(scandalous)的诗人,但与此同时,她也常常被评论家们视为“美国最刺激、最尖锐的诗人之一”。
从1994年出版第一本诗集《哲学家夜总会》开始,阿多尼兹奥每过三五年便有新的作品问世。到目前为止,阿多尼兹奥已著有七部诗集,两部长篇小说、两部短篇小说,另撰有回忆录和多部诗论。值得一提的是,她于2000年出版的诗集《告诉我》曾入围“国家图书奖”短名单,这本书同时也进入了“美国国家书评奖”的候选名单。尽管阿多尼兹奥最终与大奖擦身而过,但参与评奖却带给她一个戏谑的绰号:穿太阳裙的布考斯基。
众所周知,诗人查尔斯·布考斯基是个酒鬼,擅长以粗犷不羁的笔触书写底层生活,因此被誉为“贫民窟的桂冠诗人”。而在阿多尼兹奥的诗歌中,酒精也常常作为情感爆发的刺激物出现。对于这样的比较,阿多尼兹奥不以为意,但她回应的方式更为戏谑——2016年,她出版了以绰号为名的回忆录《穿太阳裙的布考斯基》。书籍封面的照片上,年过60岁的阿多尼兹奥身着低胸迷你裙和渔网袜躺在厨房的工作台上,双腿岔开,正大口喝下一杯葡萄酒。
除了性爱与酒精,阿多尼兹奥另一个重要的写作主题是生命的衰变与死亡。诗歌中所描绘的死亡往往带有虚构的色彩,善与恶、光明与黑暗、快乐与痛苦等有关生命的双重本质在这里得到了凸显。透过诗人的比喻、扭曲或夸大,这些作品营造出一种邪恶而恐怖的氛围,也反映出诗人眼中的另一种真实。
近日出版的《爱情之谜》是阿多尼兹奥在中国出版的第一部诗集,收录了她在中年时期的五十多首诗作。总体而言,诗集中的作品多以爱与身体为主题,强调从感官到心灵的释放,充分体现了阿多尼兹奥火辣、细腻又坦率的写作风格。经出版社授权,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从中选取部分诗作,以飨读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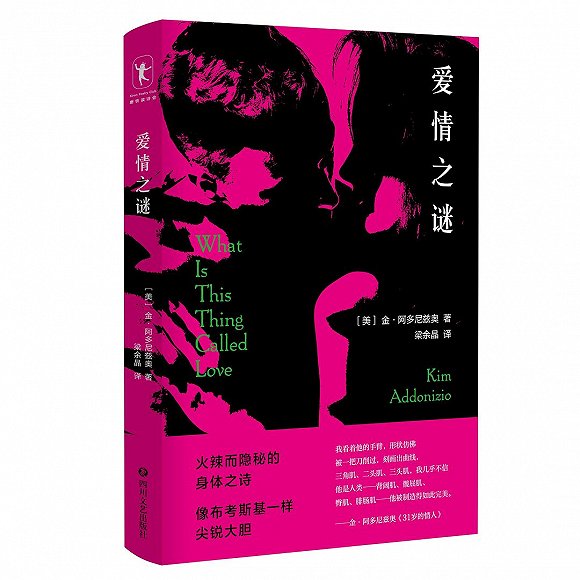
《爱情之谜》
[美]金·阿多尼兹奥 著梁余晶 译
四川文艺出版社 2020-06
31岁的情人
当他脱掉衣服,
我想到一块正打开包装的黄油,
那种牛奶般的光滑质感,
从冰箱拿出来时它还很硬,
就像他的身体很硬一样,结实
高耸的胸肌,乳头像崭新的硬币
压进胸脯,下方腹肌铺展开来。
我看着他的手臂,形状仿佛
被一把刀削过,刻画出曲线,
三角肌、二头肌、三头肌,我几乎不信
他是人类——背阔肌、髋屈肌、
臀肌、腓肠肌——他被制造得如此完美。
他裸体站在我卧室里,还没受到
任何损害,虽然他很快就会
受到损害。有一天他会长出肚子,
铁丝状的白发,流尽柔软的深色
纤维,他皮肤的奶油色也会
松弛,慢慢分离,罩着一团矮小稳定的火焰,
他对此不知道,正如我曾经不知道,
我也永远不会告诉他这点,
我会让他在床上摊开身体,
这样就能一次次吸纳他的
富饶资源,用我唯一能做的方式将其夺回。
死女孩
经常出现在电影里,脸朝下
卧在公路旁的野草中。
孩子们在河边找到她,或树林里,
叶子下,一只涂了粉色指甲的手猛然出现。
侦探在公寓里俯视她们,
或在她们几乎从小长大的房子里
从钢琴上拿起她们的照片。
一个死女孩能让影片顺利发展,
效果好过酒吧斗殴,好过
工厂爆炸,只需
躺在那里。任何人都能演她,
街边的任何孩子
都能绑住四肢,从面包车上搬下,
或勒得发青,在厨房里,浴室里,
小巷中,学校里。这就是
死女孩之美。哪怕长相平平,
自我感觉一无是处
像块泥巴,整天盯着
时尚杂志,因悲伤
而碎裂,
都能重获完整,最终被
她无能为力的一种状态所救赎,
成为关注焦点,那个特别的、
招人爱的、死去的、死女孩。
一起吃
我知道我朋友要走了,
虽然她还坐在
餐厅里,我对面,
身体朝桌上倾着,拿面包
蘸我盘子里的油;我知道
她的头发曾多么浓密,
知道就餐中途,她多努力
才摘去她的男式帽子,
为了直视那位年轻侍者,
当他问我们菜怎么样时,
报以微笑。她吃的样子
仿佛会饿死——鸡肉、葡萄叶包饭、
涂了黄油的细面薄片——
那些折磨她的东西
也在吃。我看着她拿起
一只闪亮的黑色橄榄,
把果肉从核上剥下,看着
她细长的手指,她的脸
因药物而浮肿。她垂下
眼睛,看着食物,假装
不知道我知道什么。她要走了。
我们继续吃。
世界之道
我们知道丑人憎恨美人,
痛苦屌丝都抱着劣质咖啡
生闷气,沐浴在快餐厅
肮脏的荧光里。我们知道
轮椅憎恨鞋子,
药品嫉妒维他命,
这就是为何有时整瓶
安眠药会波浪般聚集,
灌下某人的喉咙,淹死
在胃的酸性海洋里。
我们甚至不用说到穷人,
反正基本没人提起。
这就是世界之道——
悲伤与幸福对立,
傻瓜与所有人为敌,
尤其他们自己。所以别装得
你很高兴,当你的旧友
职场或情场得意,
而你还在人生中漂泊,
像餐厅水缸里的龙虾。算了,
承认吧:你想钳死他们,
如果你能。但你很无助,
徒劳地敲着明亮玻璃,
无法突围。他们在开香槟,
把你忘了,正如你没注意
你爬过多少张背
才走到这里,你的黑眼睛闪光,
你缓慢的腿顽强而稳定地行进。
酒鬼人生
这只瓶里装着灼热的头痛,
那只里有辆车偏离了道路,
撞上邻居院内一棵树,
下一只里,一个男人脱掉
你的衣服,你旋转着
掉进黑色床单的旋涡中。
另一只瓶底:上锁的金属盒,
你撬不开,尽管能听见
有人在里面哭喊抱怨,
诉说她有多难过。
别忘了那条耻辱之虫
有时在你喉咙里舒展身体,
还有那些卫生间,你蹲在
马桶前颤抖,毛发虚弱,
体内升起一个酸痛的夜晚。
那么你在干吗,坐在那儿
端着半空的威士忌酒杯,
听着冰块爵士乐,一支刚点的烟
唱出缓慢的布鲁斯?某个声音
低吟着你的名字,吧台后
正倒着双份酒,酒中
次中音萨克斯开始独奏,
在变调中带你出门,听着
就像爱情,就像它永远不会结束。
这首诗极度想成为一首摇滚歌曲
我和朋友们聚在父母的车库里,
在洗衣机和托罗牌割草机之间
用震耳欲聋的音量练习这首诗,
同时吸着塑胶袋里的帕姆油味。
这首诗抓住了今日年轻人的本质,
一种催情香水,
由麝猫的睾丸分泌而来。
我喜欢这些诗行押韵的方式,就像一首歌。
图派克 沙希德 安妮·塞克斯顿 艾瑞卡·琼。
让我告诉你这首诗实际上想怎样:
它想要你跳起荡舞,挥动拳头,
直到你爬过夜总会黏糊糊的地板,
带着深刻的领悟流下泪水,
最后呕吐在女厕所洗手池里。
它想要你一遍一遍又一遍地听它
因而三十年后
你干过的所有任性的蠢事
都会带着怀旧的光泽回来找你——
哦,记住曾在午夜时分晕晕乎乎
游荡于高尔夫球场,记住
你老爸工作地点的保安发现我们
一丝不挂,还有那个持刀的家伙
确信我们是外太空来的昆虫,
那些就是过去的日子,那首诗
在每个人的汽车广播里,反复循环。
让我们再去找回那本书吧
感觉我们曾经找过。点上几炷香,
加上一捆香草味的小小许愿蜡烛。
到我这里来,让我迷乱,
我正一字一字朗诵这首诗,
包括那些绝妙的吉他曲,
我能演奏它们,用这把漂亮的乐器,
纯粹由空气制成。
本文诗歌部分选自《爱情之谜》一书,经出版社授权发布。
 简体中文
简体中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