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缪的《鼠疫》
伟大的小说多多少少都是危险的,作家会用一些极端的情节,若干特别的人物,来挑战社会的欣赏和容忍度。在阿尔贝·加缪赖以打响个人品牌的《局外人》中,默尔索的“荒诞杀人”就曾令无数世人惊愕。不过,他在1947至1948年间发表的《鼠疫》却相反,这部小说的美学追求和提出的道德判断,两者之间不存在任何冲突。作为一个在书中往往保持沉默的主角,医生里厄从鼠疫的兴起,一直到退潮,他都在场,在看,在思考,在行动,在抵抗,在北非阿尔及利亚加缪故乡奥兰城。
Rieu,“里厄”,这名字听起来像是一怔,把所有话都咽了下去一样。里厄本人就是这个性。当格朗哆嗦着说“这是个疯子”的时候,他期待里厄附和一下,给点安慰:“是的是的,他只是疯,并没得病。”可里厄的回答粉碎了这期待。残酷的事实总要有人讲的,医生当仁不让,我们颤抖地赞为“奉献”“牺牲”等的其他工作,在作为医生的里厄这里仅属于存在意义上的人的必需。
一部小说的伟大,在于时过境迁,还总仿佛在回应当下的事情。过去,一般都认为《鼠疫》虽然背景设在北非,却是比喻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巴黎,其中有奋勇抵抗德国人的,有怯懦偷生的,有犹豫不决的,有许多人牺牲,而更多的人幸存到了解放的欢庆时刻,毕竟小说发表于二战结束后不久,而且加缪本人也是在1940年法国投降之后,亲身参与了地下抵抗运动的。然而,在埃博拉病毒近年肆虐西方的时候,这个故事就已回归到了它的字面意义,而今,一切终于临头,我们也终于能体会到书中人物的痛切挣扎了。

在书的末尾,里厄医生在沉思着鼠疫还会再来,因为人们已经种下了祸根:“鼠疫杆菌永远不死不灭,它能沉睡在家具和衣服中历时几十年,它能在房间、地窖、皮箱、手帕和废纸堆中耐心地潜伏守候。”这些话固然可看作是在警告那些认为战争已经过去而且“NeverAgain”的人,但加缪对奥兰城历史上的那场真实的鼠疫(发生在1849年)也做过详细研究。在他写于1941至1945年的笔记里,我们可以看到,他一直在为日后《鼠疫》中的种种情节做思考和准备。
笛福的《瘟疫年纪事》
生活在17至18世纪的丹尼尔·笛福,以《鲁滨逊漂流记》著称,他写作生涯早年不写小说,倒写了不少政论和宣传册,以及一部纪实文学《瘟疫年纪事》。这个“瘟疫年”指的是伦敦的1665年。那场疫情的起因不明,只有各种传闻,也不知病毒是如何进入伦敦的。它的传播,有人认为是通过呼吸,有人认为是接触了病人的床褥、衣物之类。医生对疫情完全没有办法,更可怕的是患者的无知,他们往往直到死时才明白自己是感染者,因而之前与其来往过的其他人都遭了无妄之灾。
据说,这本书直接启发了加缪写《鼠疫》。
在1665年的伦敦,大多数人即便知道疫病有传播性,也不懂得如何去防止,卫生常识是缺失的,迷信第一时间占领了人心,将疫情归结为上帝的惩罚是时人很自然的思路(加缪对此种心理也很感兴趣,他在1940年代初专门向牧师请教过,《鼠疫》中牧师布道的场景写得格外精彩),因此宿命的悲声大作;与此同时是各种偏方的流行,有人整日口含一颗大蒜,还有人把脑袋浸在醋坛子里。同这些怪异的现象相比,《瘟疫年纪事》中更多篇幅交给了那些让人不忍卒读的场景:妈妈已经没了呼吸,婴儿仍在她的怀里嘬奶;父母守着幼子死去却毫无办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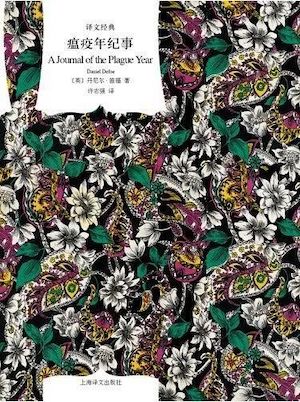
《瘟疫年纪事》是一份真正意义上的报告文学,在高度写实的同时,笛福还发挥了他在政论上的特长,对政府、医生、神职人员等等的作为做了一番分析。他揭露了神职人员的伪善,说他们自称了解疫病的真相,却是十足的骗子和丑角。在对政府和公务员的评价上,他的立论相对持平,例如他说,死亡人数绝对是被政府瞒报的了,但政府在及时处理尸体、防止病毒扩散上面是有功的。他还说道,封城、封楼这些命令在实践中是大打了折扣的,因为一些大楼看门人在贿赂或死亡威胁的面前放了居民出门,而居民若是对民政官员隐瞒了一些危险的实情,官员也无法察觉。
小说《鼠疫》比起《瘟疫年纪事》的最大优点,就是有人物,比如里厄和他的至交塔鲁,他们两个人都在记录。里厄愿做见证者,只是记录;塔鲁却愤世嫉俗,他用讽刺的眼光来观察人们的举动,同时思考鼠疫之下的生活的意义。
《瘟疫年纪事》中的揪心情节,如今读来更加揪心:公共场所发现了越来越多的死老鼠,旅馆里、餐馆里、公交车上、民宅中,起初人们不以为意,即使耳闻了病例也强行认定是偶然事件;后来病例渐多,各方人士又散布消息说不会传染,要员们总是在安抚,把有利的消息都散布出去。再后来,人们自欺的防线塌了,封城了。人们接受了现实,一番怨念之后,坐等官方消息……鼠疫过去的时候,没人敢轻举妄动,就如同当舞台黑下来,每个人都在屏息等待第一声鼓掌,以便确认戏真的已经结束了。
黑塞的《纳尔齐斯与歌尔蒙德》
作为同样经历过战争的作家,赫尔曼·黑塞也时时思考疫病的隐喻。但在他这里,疫病作为一种极端的处境,主要是为了让主人公领悟到某些超乎自身的东西而存在的。黑塞不像加缪那么注意社会,他醉心于对个人的探索,他典型的主人公都是漫游式的青年,在1930年后发表的《纳尔齐斯与歌尔蒙德》这部长篇中,这个青年是感官主义者歌尔蒙德。他在中世纪的欧洲大地上四处流浪,追寻自由而有意义的人生,却与当时正肆虐的黑死病频繁相遇。他看到村里堆积的尸体;他的一个女友埃莱娜,被黑死病人强奸并咬伤后死去了;他的另一个女人,犹太女人蕾贝卡,由于欧洲人把黑死病归因为犹太人而受到迫害。
纳尔齐斯曾是歌尔蒙德在修道院的老相识,两人亦师亦友,他安于寺院里恬静的学术生活。在故事的后半段,两个人再度相遇,歌尔蒙德得知修道院里也闹过疫病、死过人的时候,他便追问道:在你们这里,有没有发生过烧死犹太人的事情?

歌尔蒙德是那种因为所爱的人受害,才注意到疫病的人。黑塞始终在思考的是个人,因而会赋予他的主人公以某种“天选”的光环,能够体验一切并发出追问,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免疫”于凡人的痛苦。
马尔克斯的《霍乱时期的爱情》
在加西亚·马尔克斯的《霍乱时期的爱情》里,主角的“天选”光环甚至有些无耻。三位主角都生活在霍乱肆虐的城里,但终生不受病毒侵害。女主费尔米纳和她的丈夫乌尔比诺都是上流社会的人,但和费尔米纳早有书信传情的阿里萨则是个穷小子。阿里萨一心盼着乌尔比诺让位,然而,进入婚姻后的费尔米纳一直稳稳地镶嵌在她的身份里,虽然感情上时有波澜,却也不是能乘虚而入的;而乌尔比诺,从法国学医回来的他一直是政府要员,是全城公共医疗事务方面的一把手,负责平息霍乱。
阿里萨号称情种,在被费尔米纳拒绝后移情于各种社会女子,他有过无数情人,却从未染上过霍乱,在马尔克斯的暗示中,阿里萨的青春活力正是靠不知疲倦的涉猎情场来保持的。“爱情如一场霍乱”,小说上来就放出了基调,它是病,却是万千疾患中最为可取的那种,甚至还能提升对真实霍乱的免疫力。阿里萨的母亲发现儿子腹泻,吐绿水,辨不清方向,还经常突然昏厥,脸色苍白,脉搏微弱,呼吸时发出沙哑的声音……她十分惊慌,但事实证明阿里萨害的是相思病,只是严重到“和霍乱病的症状完全一样”。

霍乱隐藏在三个主角的背后,经常露一小脸,却从不打扰到他们。但是,乌尔比诺虽然一上任就控制住了霍乱,从而奠定了一生的荣光地位,可是到他以81岁去世的时候,书中却明明写道,霍乱仍然存在,当久居城里的费尔米纳难得回一趟乡下老家,就看到满街的霍乱病患者,“尸体在阳光的暴晒下肿胀起来,嘴里流出白沫。”霍乱并没有被斩草除根,只是受害者的范围被限制在了主流社会视野之外,都是“丢卒保车”里的“卒”。而在城中,阿里萨终于在乌尔比诺死后熬到了属于自己的时刻,75岁的他向72岁的费尔米纳写去了情书,在他的心目中,之前找那些女人都是为了这一刻所做的“热身”。
马尔克斯笔下的霍乱,由于他围绕“爱情”的叙事而显得很不起眼,总是被忽略,是为了衬出阿里萨不忘初心的“伟大”。作为对比,安分守己的(晚年有唯一一次出轨,但他马上向太太痛哭悔罪,显然很不适应情人这种身份)乌尔比诺医生多少是个消极的人物,内心没有激情,只相信现代科学与理性,相信霍乱发生了,就要消灭它,舍此之外并没有别的可做的事情。他对爱情不仅无感,而且轻蔑,他认为城里有太多的人感染了这种病,应该好好治一治。
但谈论《霍乱时期的爱情》又不能只谈爱情,或者激情。黑塞写黑死病,是为刺激主人公觉醒,这是他的关怀所在;而马尔克斯的更大的关怀,不在于被霍乱毁掉的社会或个体。他是以一种“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的态度来引入主题的,始终着意于把霍乱变成一种彻底的隐喻,不单隐喻爱情(其实是焚身欲火),更隐喻所有失控的、无节制的人的力量。马尔克斯对阿里萨的私德并无嘲讽,反而还颇肯定他,然而,当他着手描绘贪婪而逐利的人带给世界的后果时,霍乱就再也不是一个无足轻重的比喻了。《霍乱时期的爱情》以一个令人意外的讽刺结尾:阿里萨和费尔米纳登上爱之船,进行他们所谓的蜜月旅行的时候,看到了这样一番景象:大河已经随着五十年的滥伐森林而毁坏,阿里萨年轻时看到的参天大树都不见了,费尔米纳一直想看的原始森林里的动物也没有了,在河面上晒太阳的鳄鱼早就被猎人杀光了,鹦鹉的啼鸣,长尾猴的叫声,还有河滩上神奇的哺乳动物海牛,都销声匿迹,或者干脆灭绝了。死鱼在污水里翻着肚子,一路漂向了大海。两位新人看不下去了,让船长掉头返航,并宣布沿路不停,放出风声说,船上有两个霍乱病人。毁灭了河流生态的元凶,正是阿里萨所经营的内河航运公司。
萨拉马戈的《失明症漫记》
人是最大的病毒之源,倘若马尔克斯还不见得明说这点,那么若泽·萨拉马戈做到了。葡萄牙老作家在七旬高龄,用一本《失明症漫记》震慑了他的读者,和那些只喜欢冲着获奖作家名头而去的读书人。他写的并不是欧洲人熟悉的黑死病(鼠疫),而是一场莫名来由的“失明症”:患者眼前一片白,并且还能以目光传染给其他人。正因其莫名来由,所以更像是天谴。
《失明症漫记》里的重点词眼是,隔离。《鼠疫》中的里厄医生第一时间提出了要对已发现的病患实施隔离,并推行申报制,这是必需的措施,患者即便感到屈辱也只能默然忍下;而《失明症漫记》里,由于传染方式离奇,恐慌瞬间加剧,人们的心理防线一下子就被冲破了。在萨拉马戈笔下的这座无名城市里,被隔离的失明者第一时间感受到被监押的恐怖。他们失去了一切保护,甚至一有任何躁动,便会被紧张的看守人打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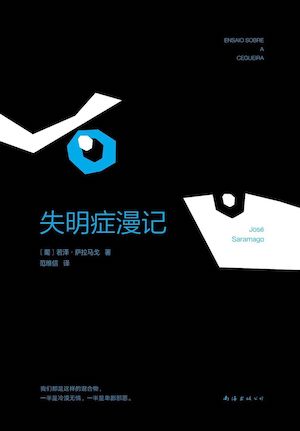
《失明症漫记》唯一让人感到安慰的地方在于,这是小说,并非事实,然而那些令人毛骨悚然的情节又像是预言。那座无名城市里的人朝朝暮暮等待好转,可等来的却是医院住不下人,新患者被责令留在家中,所有正常且必要的举措,在患者听来都仅仅是对健全人的安抚。隔离所里,有人借机对其他失明者释放心中的邪念,比如性骚扰,有人偷走公共食物,有人甚至凭着武器称王称霸,占领了所有的资源,支配其他盲人。后来,失明者冲破了他们的牢笼,闯到外边,在那些早已空无一人的公共场所里大举抢掠,并且肆意占领民宅。
然而灾难里也有一些温情的时刻,有一些希望的萌芽。比如两位失明者——一个老人和一个年轻女子相爱了;一个走投无路的老妇人在死前打开笼门,放走了她养的兔子;还有,小说的主人公,一个失明医生的太太,她冒充失明者进入隔离所,引着脱狱的众盲人来到自己家,让他们围在一起,给他们读书。文明在一个彻底垮掉的世界里艰难地、一步一步地回归。小说中有名盲人是作家,他说,即使自己看不见,他也要摸索着写下这段经历。
他能写下些什么?萨拉马戈一定读过《鼠疫》,他知道“人的身上,值得赞赏的东西总是多于应该蔑视的东西”。这是加缪的想法和态度。加缪值得热爱的理由,对我来说,就是他能在触及事物的本质与核心的同时,仍然持有一种在人的身上“察其正”的信念。而在萨拉马戈这里,在医生太太和作家的身上,我则发现了这一信念的一种较为微弱的版本。
当《鼠疫》从寓言的设定中脱出,无限逼近人们的真实体验时,我有了一种“见山仍是山,见水仍是水”的感觉。加缪式存在主义中最重要的就是人须以其行动,来赋予自己的存在以意义。意义,但愿我们在眼下也能找到些许。
(来源:界面新闻)
 简体中文
简体中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