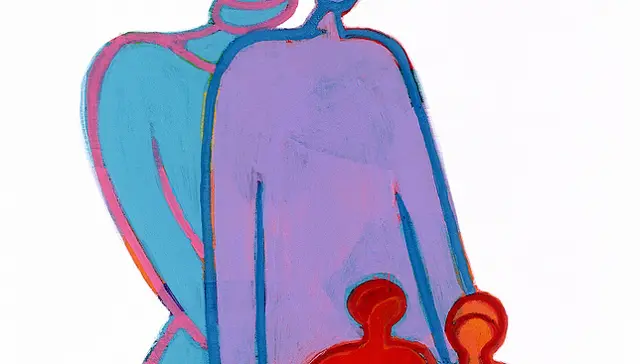进入21世纪,技术进步和城市化给人类带来更强大的生产力,但更精细的分工使个体在文化、情感上的距离越来越远,中国大都市的社会原子化倾向普遍存在。然而,家庭依然是人类生活中最重要的单元。即使人与人之间的界限愈发明晰,人们对于社区、组织的依附程度大大减少,但家庭成员仍然是最亲密的共同体。
中国人对于家庭的推崇,似乎是其几千年来传统的底色。但鲜为人知的是,在20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曾掀起一场针对家庭的“革命”,一时间,家庭成为先进中国人眼中愚昧、落后、不堪的代表,甚至成为民族进步的阻碍,亟需接受“改造”。随之而来的,就是读书人群体对于新家庭的种种设想,从不婚、公育再到恋爱自由,这些理念直到今日仍是社会讨论的焦点。赵妍杰的新著《家庭革命:清末民初读书人的憧憬》,全面呈现了20世纪初有关家庭理念的起源和实践,作者认为,这段家庭革命的表达,自有其贡献与局限,一方面是知识分子面对西方思潮的自我投射,其中又包含着某种乌托邦式构想;另一方面,家庭革命的观念,很多也并未导向美好的结果,同时给20世纪的中国人带来巨大影响。本书带领我们回到了那个特殊年代:激烈的社会变革之下,中国人怎么看待家庭?
告别传统家庭:国与家的矛盾
谈及家庭革命的起源,作者将其归结于清末甲午、庚子的战败,“救国”具有巨大迫切性。就历史背景而言,也的确如此。“民族国家”的概念正是在此时引入,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知识精英,不遗余力地建构“国家”、“国民”的观念。而家庭之所以受到批判,乃因家庭的背后,是传统中国的秩序基础。宗法制是从家庭出发,成为中国传统政治的依托。上层皇权的继承基于宗法规则,基层乡村社会的治理也依赖宗族社群。不论是皇权还是乡权,都与梁启超心中的“现代国家”相悖。
在政治层面外,传统家庭也联结着“礼教”,这构成了帝国的道德基础。礼教的核心是“三纲五伦”,抽象表达则为“道”。作者指出,当中国面对西方文明,成为“野蛮”象征时,“废礼”思潮也弥散开来。很显然,家庭作为中国人礼数纲常的日常实践环境,往往与“专制”捆绑在一起,自然也成为国家变革的绊脚石。既是担负着救亡使命,家庭革命也就被赋予了正当意义。废家以追求个体的人身、情感自由便不再显得自私而狭隘,因此才引起巨大的社会声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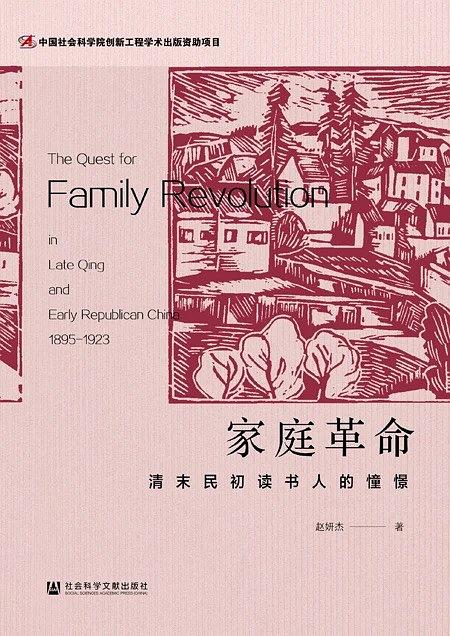
《家庭革命:清末民初读书人的憧憬》
赵妍杰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0-04
不过,国与家的冲突不仅仅停留在观念层面。仅从教育来看,传统家庭控制着教育资源,家长往往是知识的权威,同时也主导着知识的代际传递。而科举的废除和西方新学的兴起,使传统家庭失去对教育资源的掌控,下一代的知识更新足以挑战甚至颠覆家长的认知,这或许成为撼动家庭根基的重要因素。而书中所提到的自由恋爱、儿童公育甚至废婚等主张的倡导者,正是受民族国家话语熏陶下的新一代青年人,例如施存统、朱谦之、恽代英、罗家伦等人,早年皆入读新式学堂,之后或参与或创办种种思想性社团,同时在青年时代即已走出家乡,跨越省际界限参加异地政治活动,之后凭借学识和阅历进入政界、学界,至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成长为颇具社会影响力的政治人物或学者。我们或许可以从早期家庭革命倡导者的轨迹中,窥见社会思潮传播扩散的某种规律。经过一代人的演化,有关家庭的激烈批判与设想,已经落实为法条,并反作用于社会。
国与家走向对立,也表达着知识分子的政治诉求。所谓传统家庭之所以遭到批判,乃因其父权至上、漠视个性的基因与自由、民主的政治理想背道而驰。民国建立后,新的政体之下,社会革命亦刻不容缓,家庭作为旧国家的代表,更成为众矢之的。作者认为,这是近代中国思想激进的读书人“重置个人与家庭、国家与天下的一种尝试”。
然而,家庭不仅关乎政治,还关乎亲情、人伦,甚至反映着人类的某种天性。这些重要面向,在家庭被迅速政治化的时代,只得成为附带议题。舆论从国家出发,倾力批判家庭之丑恶,但每当谈及家庭中的血缘亲情如何处理时,便往往大而无当、随心所欲。国与家的对立,促使对家的讨论充满政治意味,这或许是家庭革命自出发就面临的困境。
设计新式家庭:从理想到空想
旧的家庭遭到批判,那么新式的家庭应该是什么样?作者指出,20世纪的读书人展开了无限遐想,有些近乎于乌托邦式的空想,但却反映了当时知识分子对西方思潮的认知与回应。
首先是“废家”,即无家庭的主张。“废家”的出发点,乃是对理想社会的重新构建,意在打破几千年来家、国、天下的链条,将个人从这一传统链条中解放出来。废家者针对家庭基本的养老育幼功能提出新的见解,希望打破孝道的束缚,从全社会的角度思考养老、育幼的责任;此外,针对家庭提供的居住空间,废家者主张建设新的空间,推动医院、养老院、化人院等公立化机构的建立。更进一步者,甚至要通过废婚达到废家的目的,甚至提出了“情人制”的新婚姻制度。正如作者所言,家庭革命者是以主义而不是以血缘或亲情凝聚社会。我们暂不评价早期家庭革命者主张的观点,整体来看,家庭革命的思潮之所以引起影响,乃是家庭革命者以“废家”为目的,针对婚姻、育儿、恋爱、孝道等子问题,设计出一整套方案,并源源不断地提供设想、讨论,以至在知识界形成一股风潮。
在婚姻方面,帝制时代的“早婚”与“纳妾”传统首先遭受批判,对婚姻制度的表述也展现了知识分子的某种理想。接受新观念洗礼的读书人,认为早婚之弊害主要在两方面,一是对下一代养育的不足,二是对父母家庭的进一步依赖。这两方面事实上都决定着个体无法脱离家庭,走向独立,从而陷入传统家庭网络的循环。而纳妾则根本上与新文化运动的立场完全相抵。国民党执政后,限定婚姻年龄和禁止纳妾都落实为法律条文。从另一角度来思考,禁止早婚的法律化代表着家庭父辈所能干预个体生活的领域收缩,也代表着国家对于个体生活的介入。
除旧式婚姻外,对父母的“孝道”也成为新青年的舆论靶子。作者提到,“孝”是中国传统社会的核心价值,也在儒家道德体系中占据核心地位。从梁启超认为孝道限于私德范围,再到国家主导的新式教育下父母权威的解体,孝道成为与自由平等观念冲突的陈旧思想。此外,古代中国对忠孝的捆绑,也因一直为帝制服务而遭受颠覆,反对父权与反对专制走上同路,更受到一代青年的追捧。但作者亦指出,对孝道的解构可能导向“自私自利”,毕竟有关家庭成员关系的论述,在舆论上往往流于随心所欲,无一定之规,甚至也有可能成为抛弃应有责任的借口。
在反对早婚、纳妾、孝道等旧秩序的基础上,青年知识分子对于新式家庭有着可行性的理想,即效仿“西洋式家庭”,实现从大家庭到小家庭的变革。这一方案在欧美社会有着活生生的比照,因此更成为年青一代效仿的样板。西方式的小家庭包含着对个人自由的追求,对家族权威的挑战,首当其冲的即是包办婚姻。此时,所谓的家庭革命已经渐渐剥开民族国家的帽子,为个体的幸福而服务了。另一个议题则是“儿童公育”,从本质来看,公育的意义在于将未走向独立的个体进一步从小家庭中剥离,增强其社会人格的属性。虽然公育的理念在当时存在争议,但走过近百年后,托儿所、幼儿园机构的普遍化,却一部分实现了公育倡导的职能,接替了父母的部分儿童教育职能。
然而,民国初年的舆论表达虽然多样,却也混杂着行云流水般的随意发挥和误解,书中提到最典型的案例就是关于“自由恋爱”的问题。知识分子反对包办婚姻,却对舶来的“自由恋爱”之概念充满着携带个人目的的曲解,自由的边界,从反对父母之命到反对婚姻仪式,甚至两性关系可以随时建立又随时解体,可见这种缺乏共识的讨论,只能流于空想。延伸来看,现代中国思想界的通病恐怕莫过于此:教育断裂后的新一代知识精英,在反传统和西方文明冲击的浪潮下,并未建立起完整的认知体系。更严重的是,其对概念的误读,往往又被政党操纵,成为谋求特定利益的工具,甚至进一步影响教育的内容。正如自由恋爱引发的误读一样,“自由”这一包含丰富语境的概念,至今仍被“无绝对自由”大而化之地消解,足见思想界的贫乏与无力。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家庭革命的激进化实践
当诸多新的家庭观被知识分子提上辩论场后,“五四”后的青年一代也开始了形形色色的实践活动。作者注意到,“工读互助团”即是青年人脱离家庭谋求新生活的重要方案。互助团从提出到实行可谓“一蹴而就”,加入的青年皆以“废除家庭”、“实行共产”、“改造社会”为目标,同时也受到蔡元培等新文化领袖的支持。然而,在无秩序束缚的状态下,在互助团同处一室的男女青年以“自由恋爱”之名卷入情感纠葛中,更由于恋爱引发的痛苦而使互助团解散。作者认为,雷厉风行的“家庭革命”看起来无效又无序。另一方面,作者也指出互助团的组织形式,与成员之后的政治轨迹密切相关,当年互助团的核心成员如施存统、赵世炎、张伯根等人先后参加马克思主义组织,构筑起早期中共党组织的基础。
通览全书,作者考察的时间下限以1900年前后为始,至1920年代为止,聚焦于知识分子对家庭的讨论与实践。然而,“家庭革命”并未就此划上休止符,反而在1920年代之后走上更加激烈的实践道路。正如本书引言的开头部分所陈述的,1930年国民政府制定《亲属法》时,我们可以从民国政府对婚姻、家庭的法律定义上来看到当时对家庭结构改变的实践,政治精英的讨论已大大超出常规的观念,许多新的思潮甚至已被纳入法律,走在时代前头。但由于民国政府的艰困执政环境,许多观念和法律并未得到贯彻。1949年后,家庭革命在某种程度上反而得到了最充分的实践。
谈及工读互助团的实践,作者亦提到几十年后实行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其影响和范围都远远超过1920年代所谓“读书人的憧憬”,而政治运动造成的普遍结果,也使中国社会面临对家庭和个人去向的反思。反家庭主义走向极端,造成的不仅仅是“公社化”试验。集体主义的召唤,使家庭在公共利益面前,成为可以被牺牲的对象,“舍小家为大家”上升为备受社会推崇的美德。在激烈的运动面前,“阶级”也可以在紧密联系的家庭成员之间画出界限。正如作者在结论中所言:“当我们把整个社会当成一个实验室,而每个个体自然丧失了主体性而沦为试验品。尝试废除家庭的实践便浮现除了对自我和他人生命与感情的轻率和不尊重。”
如果我们从20世纪后半叶家庭结构受到的冲击,来回顾20世纪初“废家”论说的起点,会发现所谓“家庭革命”一开始即建立在民族国家的话语之上。本来“家庭”是一个中立性的词汇,是一种生活的方式,但因中国古代的社会秩序立足于家庭,家庭因此背上了“封建”、“传统”的标签,成为受到批判和改造的对象。与此同时,中国现代政党政治的兴起,使个体在党、国、家三者之间处于更加脆弱的境地。1927年后,国民党垄断了国家构建的政治资源,其对家庭革命的支持,亦包含着政党对个体的渗透。在地方士绅的观感中,“家庭革命”与都市知识分子所构想的画面完全不同:乡村的宗族秩序被打破,换来的却是“党部横行”。作者亦有指出,本书聚焦于“读书人的憧憬”,其实多数论点都是知识分子群体的社会构想,与其社会大众的落实层面,还有很大距离。历史无法假设,但我们可以从家庭革命实践的演进逻辑中,看到其乌托邦式的悲剧一面,这与前文所述的思想界之弊病,似乎又互为因果,主导着20世纪中国的巨变。
 简体中文
简体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