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馆很有趣,也很有教育意义。它们是向市民开放的公共机构,是人们在学校旅行、第一次约会或是假期下雨天会去的地方。博物馆是安全的,颇有价值的,但有点无聊。这么说对吗?丹·希克斯对此有不同的看法。他的新作《野蛮的博物馆》( The Brutish Museums )文笔优美、论证严谨,在书中他认为,博物馆里充斥着无休止的暴力、无休止的创伤,以及每天早晨当长条灯点亮就再次犯下的殖民罪行。博物馆即战场。
这本书是一个重要的行动号召:部分是历史调查,部分是宣言,要求读者废除现存的“野蛮博物馆”,并为它们找到新的存在方式,不是作为暴力或创伤的场所,而是作为“良知的场所”。希克斯是牛津皮特·里弗斯博物馆(Pitt Rivers museum)的馆长,该博物馆网站称,馆内陈列着“来自世界各地的考古和人种学资料”。而他的研究专注于一个特定的地区——贝宁王国,位于现在的尼日利亚境内。
《野蛮的博物馆》首先介绍了1897年被英国军队掳走的贝宁青铜器、埃多人制作的牌匾和其他物品。然后,希克斯开始了一段关于博物馆和实物、殖民暴力和资本主义(以及它们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的理论之旅。有一节讲的是英国人偷走青铜器和其他物品的历史背景,希克斯明确表示,对贝宁王国的所谓“报复性”袭击实际上是早就计划好的,其动机并不是为了攻击帝国代表团,像博物馆信息板上经常说的那样。
在当时及之后,人们认为对贝宁的袭击是“人道主义”的,因为这个王国用活人献祭,但希克斯把这点放在了这样的大背景之下:大英帝国的种族优越感,以及——或许也是最重要的——在贝宁君主制掌控之下,英国人想要进行原材料贸易来获利的渴望遭到了挫败。因此,1897年的袭击事件加入到了一长串例子之中,帮助我们批判帝国人道主义这一概念本身。这本书细节丰富,态度激烈:希克斯将19世纪末所谓的“小规模战争”概括为一场持续到1914年的“零次世界大战”,在此期间,欧洲殖民列强为了掠夺和征服非洲人民,持续不断地发起残酷的战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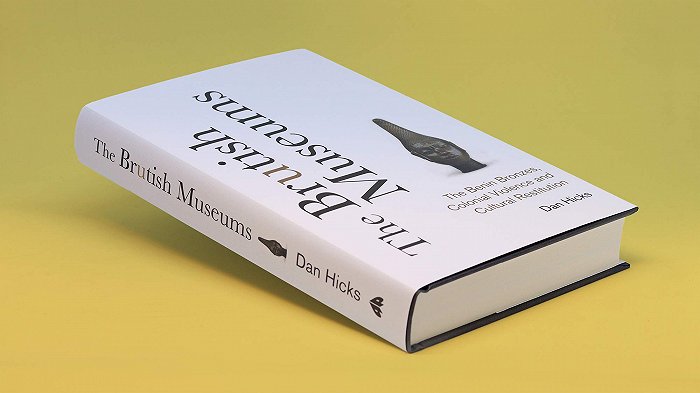
《野蛮的博物馆》
这本书的核心是“死亡史”或“死亡学”的概念:人类学博物馆里的知识是通过死亡和丧失来创造的。在博物馆这个空间里,过去一次又一次地重演,同时又陷入停滞——在一个玻璃盒子里,一个昏暗的角落里。正如希克斯所说,“博物馆不仅仅是一个放慢时间的装置,而且它本身就是一件武器。”
当人们谈到贝宁青铜器及同类文物的帝国背景时,往往把它们视为帝国的“副作用”,而且往往是积极的副作用,因为它们不仅有助于启发英国观众了解其他地方的文化,同时提供了审美上的愉悦。但正如希克斯明确指出的那样,博物馆的藏品跟石油和橡胶一样,都不是帝国的“副作用”。这些物品与帝国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们继续出现在英国的博物馆里就是这种暴力的延续。
希克斯停顿了一下,详细谈论了比佐组织(Bizot group,成员为各大博物馆的馆长)2002年发布的《关于世界博物馆的重要性和价值的宣言》,该宣言反对将文物归还原国的呼吁。他指出,这一支持博物馆殖民主义的声明是在伊拉克战争的酝酿阶段发表的,当时正值西方最清楚战争将要爆发的确定时刻。如果博物馆是建立在从世界各地偷来的文物的基础上,但为了北半球观众的利益而建在那里,那么它们如何才能成为世界性的博物馆呢?
博物馆馆长们认为,文物保存在伦敦、巴黎、纽约,在某种程度上要比保存在拉各斯、亚的斯亚贝巴、内罗毕或金沙萨更为安全。希克斯认为这纯属无稽之谈,他对殖民博物馆中文物的策展、保存和来源持无情的批判:“纯粹的虚伪始于这一事实,即在这些所谓的世界遗产安全储备中,今天的馆长们对馆藏文物的理解是如此之少。我们不知道那里有什么。我们不清楚它在哪里。我们无法确切地说它是如何到达那里的。”
他的呼吁很简单:归还所有一切。这有双重作用。首先,这是前殖民压迫者对曾经的殖民地国家进行文化归还的开端。当这些文物被归还给它们的来源地和被盗地的博物馆时,这些国家将得以庆祝和审视自己的文化遗产。但这也将迫使英国人接受自己的殖民过往——这真的不是过往,而是置放在玻璃后面的当下。
(翻译:刘溜)
 简体中文
简体中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