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城前的生活中,我最怀念的不是节日,甚至不是出国旅行,而是与女性朋友相处的时间。我相信,这种惆怅是普遍存在的。还有一些书,可以让你沉浸在复杂的、偶尔让你受伤却总是不可替代的女性情谊中。
在托妮·莫里森的小说《秀拉》中,内尔和秀拉是俄亥俄州贫穷的黑人社区里最好的朋友。秀拉拒绝扮演这里的女性扮演的种种角色,她不受社会和性的约束。所有人对她避之不及,就连内尔也不例外,内尔的婚姻在秀拉的诱惑下崩溃了。内尔难过了多年,但也像之前的秀拉一样,她逐渐明白,她缺少的不是丈夫,而是与好友的关系。莫里森说,她身边的女人都在挣扎,都陷于贫穷,她们是这本书的灵感来源。“那些我们拿来交易的东西!时间、食物、金钱、衣服、笑声、记忆——还有胆量。尤其是胆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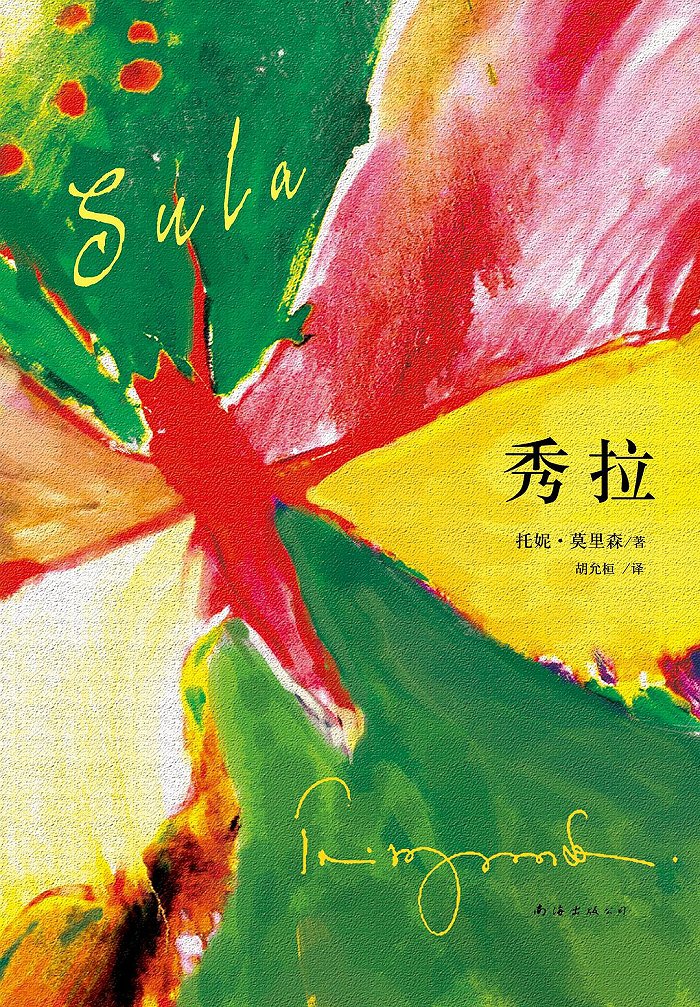
《秀拉》
[美]托妮·莫里森 著 胡允桓 译
南海出版公司 2014-7
埃琳娜·费兰特在她的“那不勒斯四部曲”中讲述了莉拉和埃莱娜20世纪50年代相识后在那不勒斯地区暴力、压抑的文化中所经历的爱恨起伏。埃莱娜说:“莉拉逼着我去做一些我自己都没有勇气去做的事情。”是她的朋友莉拉提供了勇气,让埃莱娜得以逃脱,成为一名作家。费兰特也并不避讳,她们具有强大催化剂效应的友谊亦有着破坏性一面。
维拉·布里顿的《友谊的证明》( Testament of Friendship )中也包含了宿敌关系的要素。乍一看,本书是她最好的朋友——37岁就去世的作家和活动家温尼弗雷德·霍尔特比的光辉写照。两人形影不离,甚至在布里顿结婚后两人还住在一起,在布里顿撰写《青春的证明》( Testament of Youth )的时候,霍尔特比甚至放下了自己的写作工作,帮忙做家务。在该书的结尾,布里顿承认,她利用霍尔特比宽宏大量的天性来追求自己的才华,这也是对一个事实的坦诚认识——女性创作往往需要牺牲其他女性的时间。深厚的友谊在被忽视或失衡的时候依然存在,但霍尔特比在布里顿还没来得及偿还这笔恩情债的时候就去世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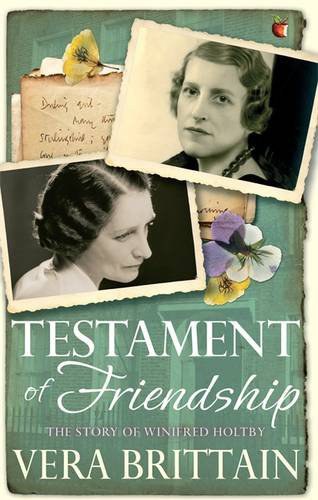
《友谊的证明》( Testament of Friendship )
塞巴斯蒂安·巴里的《安妮·邓恩》( Annie Dunne )亦描绘了这种相互依存的关系。1950年代,安妮和她的表妹莎拉在爱尔兰威克洛偏远地区的小农场里生活和工作。两人都是老处女,在被莎拉收留之前,安妮被其他所有亲戚拒绝或赶出家门。在这个夏天,安妮仍然害怕自己会再次被赶出家门。在此期间,两个女人意识到只有她们才能真正欣赏对方身上的品质。她们的友谊点亮了她们的生活,“我看到莎拉身上有一种无人能否定的东西,她的勇气未被赏识,她的灵魂相当美丽。”
女性如此擅长见证和承认彼此——这也是伯娜丁·埃瓦里斯托的诗篇小说(verse novel)《皇帝的宝贝》( The Emperor's Babe )的核心。祖莱卡是公园三世纪的伦蒂尼恩 (Londinium,公元约43年建于今伦敦城一带的居民地)的第一代移民,她11岁时在切普赛德浴场被一位年龄和身高都是她三倍的罗马贵族发现,并很快与之结婚。他常常不在祖莱卡身边,即使他在,祖莱卡也高兴不起来。这一切因为阿尔巴的出现而改观——她鼓励祖莱卡完成她的梦想,成为一名诗人,体验爱情。就像生活中和艺术中常常出现的情况一样,这种大胆的行为必须付出代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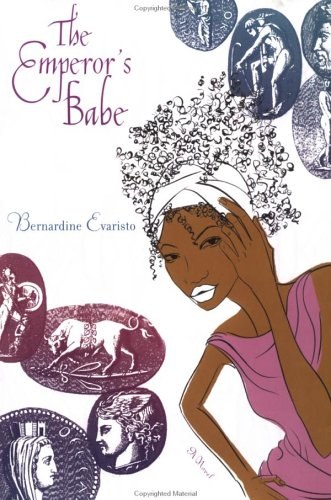
《皇帝的宝贝》( The Emperor's Babe )
在当下这些悲伤、迷茫的日子里,对女性友谊的探索为我们提供了智慧和营养,同时它们鼓励我们面对政治现实。用莫里森的话说,“剥夺自由这件事很有说服力——一些人仍能茁壮成长;另一些人则凋亡。我们所有人都尝到过这种滋味。”
(翻译:王宁远)
 简体中文
简体中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