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关于神秘疾病的新闻报道总是能让我兴致盎然,无法抗拒。例如“18名纽约青少年因何抽搐不止”“神秘的昏睡病在哈萨克村庄肆虐之谜”“200名哥伦比亚女孩离奇感染神秘疾病”“哈瓦那综合症之谜”等等。而在这类描述的疾病当中,有一种疾病的出现频率似乎更多,那就是:心身疾病(psychosomatic illness)。我们的身体就是思想的“代言人”,这一点不难理解,姿势、微笑、紧张时刻颤抖的双手等各种表现都显而易见。然而,有时候身体可能表达得太过了,也有时候精神太过强大甚至会导致身体出现疾病,人们对此却难以理解。当心身疾病影响到群体,像病毒一样在人与人之间传播开来时,这种困惑就会尤为明显,而这种现象通常被称为群体性癔症(mass hysteria)。
眼下,我们正处在新冠疫情大流行当中。我们被迫隔离起来,通过身体搜寻症状。如果有这么一个时机,心身疾病能够通过焦虑和暗示传播,那么必然就是现在了。病毒的危险会在多个方面影响健康。自2018年以来,我一直在走访疑似感染心身疾病的社区。我见识过恐惧可以对身体健康造成的影响,也看到过正确的疗效带给人的希望。
最开始我见了一个叫诺拉的10岁女孩。当时,她正躺在床上,闭着眼睛,浓密的黑发像光晕一样散落在枕头上。看上去她像是睡着了,但事实上,她只是动不了。当她的父亲试着让她坐起来时,她就会像个布娃娃一样柔软无力。算起来,诺拉已经18个月没有动过了,她甚至连眼睛都没有睁开过。她的父母用吸管给她喂流质食物以维持生命,还会帮助她活动关节,按摩皮肤,保证身体的基本机能完好。扫描和测试均表明诺拉的大脑是清醒的,这与她基本毫无反应的身体状态显然不符。
除了诺拉之外,还有数百名患病儿童处在长期昏迷状态。他们的体检结果往往都是正常的,也没有任何身体病变可以解释这种症状的发生,于是这种新发现的医学症状被称作放弃求生综合征(Resignation Syndrome)。更离奇的是,放弃求生综合征几乎只出现在瑞典。直到近期,患上这种综合征的孩子们仍然都是来自那些在瑞典寻求庇护的家庭。

神经学家苏珊娜·奥沙利文 图片来源:Gary Doak/Alamy
一开始,我希望通过诺拉了解到她陷入昏迷的原因,从而进一步了解放弃求生综合征这种疾病。然而,最终当我发现人们对于放弃求生综合征仍然知之甚少时,我感到非常沮丧。帮助我安排探视诺拉的医生,还寄希望于我能够提出一种大脑机制来解释为什么像诺拉这样的孩子会醒不过来。为了找到答案,瑞典科学家们在扫描和血液测试上投入了大量的时间。与此同时,媒体只是对这种看似不可能发生的“神秘疾病”感到惊讶。
的确,放弃求生综合征是一种极不寻常的疾病。像诺拉这种症状,大脑测试表现健康正常,但身体却处在深度持久昏迷状态,就非常罕见。但是,这种疾病真的有必要成为新闻头条吗?毕竟,我们其实都知道真正的病因,也清楚应该如何治疗。面对被驱逐出境、不获政府庇护时,像诺拉这样的儿童会被迫退出社会,变得越来越冷漠,直到最终停止与世界的互动。而治疗放弃求生综合征的办法,就是为他们提供庇护。
在我看来,放弃求生综合征实际上并非医学病症,而是社交障碍。当这些孩子们通过身体症状表现出他们的需求,而其他人通过神经递质和大脑连接将其概念化时,他们的遭遇就会被赋予不一样的意义。相较于心理疾病或是社会困境,身体的残疾更能引起人们的关注和帮助。世界各地都存在着寻求庇护的儿童,却只有那些被冲到海滩,或是因为不堪重负而陷入昏迷的难民儿童,获得了更多的关注和庇护。
见过诺拉之后,我很清楚,这些瑞典孩子们的困境并不是靠神经学家或是脑部扫描就能解决,放弃求生综合征所表达的其实是心理创伤。这不禁加深了我探索神秘疾病的欲望,让我更加想要去了解这些神秘疾病的成因以及背后的故事。我想知道,揭开了那层神秘的面纱之后,这些病症究竟是在表达什么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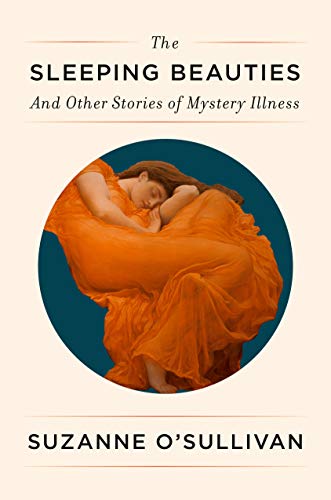
《睡美人》
2011年,有一群美国女学生开始无法控制地抽搐。神经学家将这种症状诊断为身心紊乱症(Psychosomatic Disorders)。然而这个诊断结果遭到了媒体的质疑,随后,这家为名人效应所驱动的媒体在这些女学生所在的社区展开了一场寻找环境毒素的行动,最后无果告终。2016年,20多名在古巴的美国外交官感染了一系列神经症状,包括头痛、发晕和不稳定症状。当时,也有人诊断这是群体性癔症的爆发,并引发了广泛的讨论。但是,这些外交官的医生却并不认可这个诊断。在医生看来,所谓群体性癔症就是装病,而他坚称他的外交官们绝对没有“假装”生病。最终,虽然缺乏证据,但医生还是将这些病症归咎于古巴声波武器的袭击。
对于群体性癔症的定义其实并不明确。它可以用来描述各种行为:兴奋,骚乱,蜂拥,抢购,大规模枪击事件等。作为一种被称为“群体性心理疾病(MPI)”的医学疾病,它是指恐惧和焦虑等紧张状态在密切接触的人群中相互影响和传播的传染性症状。
癔症在医学上有多种表现形式。癔症(hysteria)一词源于希腊语,意思是子宫。曾经人们认为癔症与生育和性行为相关,所以只会发生在女性身上。在弗洛伊德的理论中,癔症被定义为一种心理障碍,一种由被压抑的心理创伤转化而成的生理症状。近来,癔症又被当做是生物学问题,通过心理机制和大脑生理过程的相互作用而引发。
群体性癔症所引发的群体现象是医学上最常被曲解的疾病之一。一说起群体性癔症,不可避免就会与一些陈词滥调和刻板印象联系在一起。它时常被刻画为一种由于情绪过度紧张而引发的心理障碍,且往往发生在女性身上。在许多书籍和影视作品当中,群体性癔症都被归结为女性遭受性挫折后的产物。阿瑟·米勒在《萨勒姆的女巫》中所描绘的愚昧村庄似乎从未离我们远去。时至今日,在与群体性癔症爆发的相关新闻报道中,我们仍然能够读到对数百年前“追捕女巫行动”的影射。有一份报纸的标题就直接将这些抽搐的美国女学生称为“勒罗伊的女巫”。而据我所知,没有其他任何一种疾病会像群体性癔症这样,至今还依然遭受着17世纪信仰的影响。

1996年,电影版《萨勒姆的女巫》剧照。图片来源:20th Century Fox/Allstar
即便是那些接受过医疗培训的人,对群体性癔症的看法和认知也并没有好到哪里去。许多医生仍然误以为癔症就是在装病,就像上文中提到过的美国外交官的医生。他们认为,群体性癔症是脆弱的象征,只有女性才会得这种病,并因此拒绝对男性进行这种疾病的诊断。还有许多人仍然会借用弗洛伊德的理论来解释群体性癔症,而这些理论往往与性虐待相关。但是,受这种疾病影响的群体会竭尽全力地去远离它,这有什么奇怪的吗?
因为医生把群体性心理疾病(MPI)视作是装病,所以这些外交官们别无选择,只能从别处寻找答案。美国和古巴两国关系一向紧张,理由充足到足够使外交官们怀疑是古巴方面发动了袭击。然后,政客告诉使馆的工作人员他们有危险,并建议他们躲起来。另一方面,在纽约,医生明确地诊断那些抽搐的女孩子们是患了身心紊乱症。对此,媒体认为,这一诊断就意味着这些女孩子有麻烦了,并且迅速开始审视她们的社会问题,而作为优等生和拉拉队员,这些女孩子们的生活并非苍白寡淡。如果群体性癔症是由忧虑和压力引起的话,那么医生对这些女孩们做出的诊断就有待商榷了。
如果人们不重视甚至是忽视身心症的正确定义,那么这两个案例中的病患只会被推入无尽的医学测试,陷入死循环。那些女学生们或许后来都康复了,但是在古巴,五年时间过去了,还有一些人在寻找声波武器。这让人不禁发问,如果我们能单纯地正确地看待群体性癔症,把那些相关的隐喻抛到一边,或许就可以避免很多痛苦了。
“群体性心理疾病”又称“群体性社会性疾病”,或许这个名称才更加合适,因为直接表明了这种疾病是一种社会障碍,而不是心理或生理障碍。有时候,医生们总是只顾着观察人们的大脑,而忘记了考虑造成疾病的社会因素。或者说,更有可能的情况是,他们不敢太近距离地观察病人的社交世界,因为害怕外界会指责他们将病因归咎于病人本身、他们的家庭或是社区。于是,他们避免进行坦诚的对话。这也就是为什么群体性癔症不再是全球移民危机的产物,而是成为了一个所谓的谜。
距离上一次见到诺拉,已经过去两年了。我很高兴地告诉大家,她已经醒过来了。现在的诺拉可以自己吃东西,不再依赖进食管,有时候甚至还能去上学。但是她现在还是不能说话,离完全恢复正常还有一段路要走。她的家庭已经获得政府批准,可以留在瑞典,至少在可预见到的未来不会再面临被驱逐的困境。诺拉病情的好转并不是因为医生或心理学家的治疗,而是在于社会为她提供了一个具有安全感且充满希望的未来。
本文作者Suzanne O'Sullivan是神经科顾问医生,著有《睡美人》( The Sleeping Beauties: And Other Stories of Mystery Illness )和《脑海中的疾病》( It's All in Your Head: True Stories of Imaginary Illness )。
(翻译:刘桑)
 简体中文
简体中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