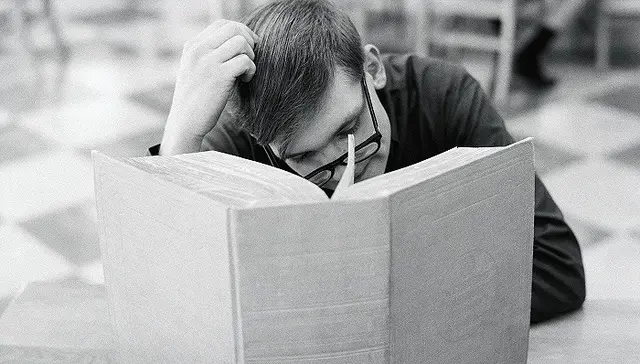“伊布拉姆·X·肯迪、罗宾·迪安杰洛、乔丹·彼得森、彼得·泰尔、尤瓦尔·赫拉利、斯蒂芬·平克、泰勒·科文、塔尼西斯·科玆、米歇尔·亚历山大、斯拉沃热·齐泽克、安德鲁·沙利文、理查德·道金斯和山姆·哈里斯、彼得·辛格、萨曼莎·鲍尔。”这是《纽约时报》专栏作家罗斯·杜塔特试图列出的新千年最具影响力,甚至是水平最高的思想家。
这是一份相当令人失望的(以美国为中心的)名单,而这正是他的观点。在这些人中,谁有可能在几个世纪后被认为是与陀思妥耶夫斯基或马克思一样的世界知名思想家?
根据杜塔特的说法,如今的知识分子几乎都是记者,无论是职业上还是精神上。的确,历史上许多伟大的作家都写过新闻作品。但是,例如卡尔·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52年),一篇关于1851年拿破仑三世政变的文章,是他作为记者的知识分子作品。而目前的情况是许多记者正在扮演知识分子的角色。事情发展到现在,我们甚至不再经常听到谈论“知识分子”这个独特的群体,反而只有“媒体”和“学者”。
在文学方面,这个领域也没有多肥沃。杜塔特认为,2019年去世的托尼·莫里森是“最后一位伟大的美国小说家”。在其他体裁(比如诗歌)衰落的时候,小说已经证明了自己独特的长寿,但它现在也已经走到了尽头。菲利普·罗斯和索尔·贝娄等美国作家的光辉岁月已经过去。有名望的作家仍然出现,但主要是在其他地方,比如意大利的埃莱娜·费兰特、法国的米歇尔·韦勒贝克和挪威的卡尔·奥夫·克瑙斯加尔。

杜塔特认为,2019年去世的托尼·莫里森是“最后一位伟大的美国小说家”。图为莫里森在《这个世界土崩瓦解了》出版50周年活动上发言。图片来源:Angela RadulescuCC BY-SA 2.0
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英语圈的这种文化萎靡?杜塔特认为是因为1960年代的激进主义已经枯竭,其他人可能会归因于1989年后的奇特停滞。但我们最缺乏的是先锋派。历史上的大动荡时期往往会出现一小群放肆叛逆的知识分子,他们往往处于文化生活的边缘,通过短命的“小”杂志对文学机构进行正面攻击。他们反对在当时的重大政治问题上被归类,常常激怒或疏远各方,有时他们并不公开发表政治观点。
在政治动荡时期,往往是在这些富有成效的知识分子小群体中产生了伟大的文学人才。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葡萄牙就是这样一个微小的现代主义场景,伟大的诗人费尔南多·佩索阿在此诞生。
如今依然有良好的美学反叛条件,也就是说,如今的条件在物质上是不稳定的。如果说当今的政治缺乏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利害关系,但却仍然存在着大量混乱和文化争论。从右翼民族主义到左翼民主社会主义的一系列政治立场,已经成为真正的可能,而关于正义和社会结构的基本问题则有待辩论。
但我们有什么类似于先锋派的事物呢?许多关注种族和性别问题的进步作家并不合格,因为他们远远没有达到“打击资产阶级”的目的(这也许会冲击体面的中产阶级舆论),相反,他们小心翼翼地调整自己的商品,以迎合这一群体的口味。例如,罗宾·迪安杰洛的反种族主义小册子《白人的脆弱》( White Fragility )不仅在《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上连续134周占据一席之地,作者还从各大名校以及亚马逊等公司获得了巨额演讲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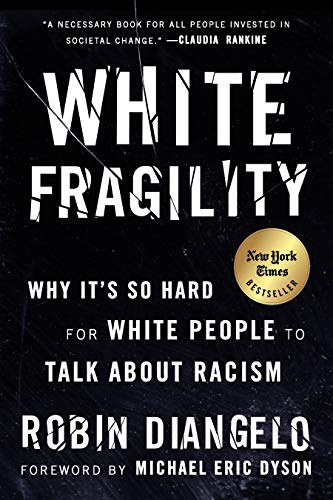
《白人的脆弱》
“文化战争”中的其他派别也没有孵化出有希望的文化反叛候选人。批评“取消文化”的中间派,如美国作家托马斯·查特顿·威廉姆斯或政治学家叶沙·蒙克,已经承担了反智主义者的角色。但他们太受人尊敬了,被称为先锋没法给他们带来任何好处。许多右派作家致力于捍卫传统的文化态度,也不太可能成为惊世骇俗的人。尽管美国右派一直坚持高雅文化的重要性,但如今已经很少有人对当代文学表现出兴趣,杜塔特是一个罕见的例外。
随着杰里米·科尔宾和伯尼·桑德斯的崛起,英美两国崛起的青年社会主义者还没有出现著名的文学人才,就已经被击败了。一个例外是小说家萨莉·鲁尼,她的辩论式幼稚马克思主义最好被理解为一种纯粹的审美手段,旨在丑化和区别于老一代的爱尔兰作家。
一个问题是,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主导知识生产的记者思维在政治上过于狭隘,不适合美学反叛。就杜塔特而言,他比美国中右翼的大多数人都更努力地阅读文学作品,但他关于文化话题的大部分文章仍然采取评论最新的好莱坞超级英雄电影的形式,也就是主要采用政治视角。
“文化战争”的无情要求,将美学压迫到政治文化的服务中,使事态更加艰难。或者因为我们的问题在于物质,在于我们的制度。通过艺术硕士课程将诗人和小说家纳入学院的僵化惯例,美国写作已经将沉闷和顺从制度化。随着英美的出版业更加统一,叛逆作家接触读者的可能性正在逐渐减少。
但是,一些新的出版物还有希望的迹象:伦敦的《围栏》杂志讽刺重要的文学和新闻人物,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纽约的《漂流》杂志则试图证明新一代有社会主义倾向的新闻工作者的能力。无论新的先锋派采取什么形式,我们都应该知道总有一天我们会对其失望。这证明先锋派正在做它该做的工作。
(翻译:李思璟)
 简体中文
简体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