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编写历史最古老的两种方法,是编年史与纪传体。前者以自然年代为断层,后者以人物的生涯为线索。彼得·沃森的《二十世纪思想史》的某些章节大致按照编年顺序将思想文化史上不同领域作共时排列,另一些章节则顺着时间的线索,刻画了某个人或某个学派或思潮的发展变迁。这种纵横交织的庞大经纬线,是为了尽可能选取彼此相关联的思想,将“二十世纪思想史”纳入一本书。然而这篇书评却要质疑这种写作方略,因为它必然会弱化另一条更根本的线索,即内在于思想的,由逻辑贯穿起来的线索。
沃森是一位出色的事件记录者,他若从事历史学的其他门类,例如军事-外交史或社会-经济史,他描绘庞大画卷的长处将更能得到彰显,且其短处也不会暴露得如此清楚。本书广博过度却缺乏重心,作者仿佛面对无限长的战线,其策略竟是把兵力分散打游击,其代价是对阵地战的全面放弃。这种比例失调首先在于对大思想家的忽视,例如狄尔泰的名字一次都未出现,胡塞尔的思想只占一页。马林诺夫斯基的大名只出现过一次,且对这位人类学方法奠基人的思想毫无介绍。相反,玛格丽特·米德、鲁思·本尼迪克特等人类学家反而颇费笔墨。沃森提到了弗里曼对米德的批判,遗憾的是未能意识到,该批判的标准(指责米德不懂萨摩亚语、未与当地人共同生活)正是马林诺夫斯基的遗产。对马氏的忽视和对狄尔泰的忽视其实相通:解释学在多大程度上必须以“体验的亲身性”为基础?意义的可译性的标准是什么?这些基础问题被忽视了,而马氏为人类学确立的标准,从哲学原理上说,恰是为了尽可能克服这些问题。
另一个例子是本书对库恩的介绍不足两页。沃森已经知道库恩对波普尔证伪主义的批判,然而正如沃森从未谈到狄尔泰解释学中的“前见”,他也未能说清库恩与波普尔之间的问题:库恩指出的那些“一切科学都要遵循的最基础范式”究竟是什么?科学追求确定性、普遍性与波普尔说的“可证伪性”之间有没有关系?同样,对维特根斯坦的思想介绍也忽略了游戏规则、生活形式、语法命题以及《论确定性》。以上几处忽略的其实是不同思想家在不同的领域对“前见”的分析。共同的问题意识本可将他们贯穿起来,作者却未看到这一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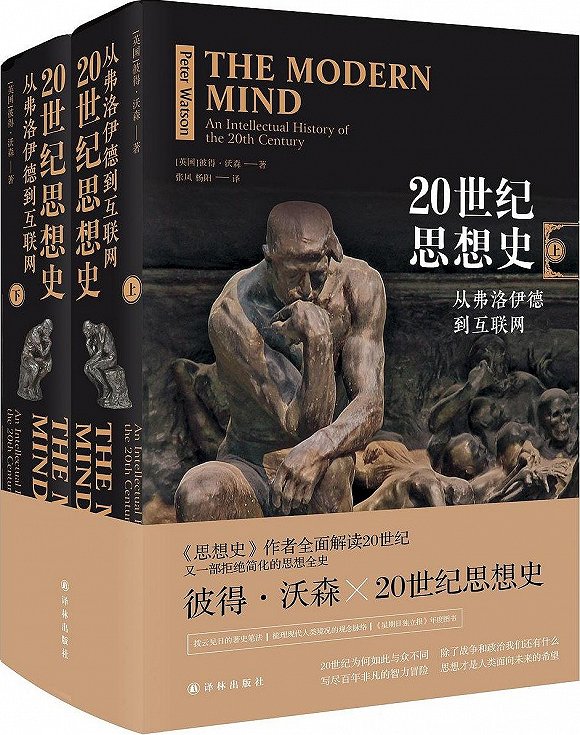
《20世纪思想史》
(英)彼得·沃森 著 张凤、杨阳 译
译林出版社2019年10月
除科学史外,政治思想史也是历史系的思想史专业极重视的部分。在该领域研究中,我们对某理论是否合逻辑,和其宣传力量是否影响了时代的判断,是相互分离的。换句话说,我们常将历史上的政治思想当作意识形态小册子。本书的一大优点,在于作者对一战前后的小册子的井喷时代认识广博,然而他在谈论到罗尔斯等学院派思想家时,就显得囫囵吞枣。
从历史的观点看:沃森将罗尔斯放在平权运动与福利国家的背景下讨论是完全正确的,历史学家当有此时代敏感性,这是许多哲学家欠缺的。但他对《正义论》的理论的解读比罗尔斯还要非历史化,因为沃森甚至未提到“良序社会”这个至关重要却又饱受争议的焦点。这也意味着沃森不熟悉罗尔斯的反对者们的批判。沃森还谈到过《历史的终结与最后之人》,然而冷战期间的美国人罗尔斯宣告“良序社会”,与冷战结束时美国人福山宣告“历史终结”,二者分别以怎样的意识形态强行粘合了理念与现实,其更广阔的政治史效应也并未提及。
从哲学的观点看:二十世纪道德哲学中最大的三个相互关联的变化,其一是德性论的出现,并与义务论、功利论鼎立;其二是道德越来越被视作政治经济学的前设,而不再是信仰的附庸,技术手段以更显见的方式影响、塑造着道德目的的可能性;其三是元伦理学(metaethics)的诞生,道德争论越来越多地诉诸语言分析。这三者都是现代世界的必然结果,是时代的真正巨变,远比一、两个思想家的主张更重要,作者却均未涉及。这些绝不仅是学院内的智力游戏,因为它们其实折射出了另一些广泛的心智史现象:例如现代人不再承认对“道德”的意义有统一的认识,抑或首次意识到了这个词其实没有一个统一的词义。
海德格尔是在阿伦特的一节中出现的,只占了一页篇幅,且另半页在说他是个纳粹。几乎所有海德格尔的思想传记都必须讨论其纳粹丑闻,但老生常谈的是:弗雷格也是个准纳粹,为何他没有被如此对待?因为弗雷格的政见与弗雷格哲学无关,而海德格尔的政见却与其思想有关。海德格尔的纳粹丑闻只有在联系到其哲学时才值得一谈,可是沃森既未曾谈及海氏谈论过的思想的“扎根性”,或海氏不把民主视作一种基于人类共性的抽象原理而视作“美国化”,也未谈及海氏对“真理(aletheia)”的特殊看法与同时代德国反对“(犹太)唯理智论”的思潮之间的联系。当然,海德格尔的重要性,更在于《存在与时间》中那些与政治无关的部分,本书也略过了。
同样的问题出现在对尼采的解释中,他把尼采放置在达尔文主义思潮中理解,强调主人道德与奴隶道德的区别。法西斯主义者和后现代嬉皮士、保守主义者和激进主义者、厌女者和女权主义者,都有各自的尼采,但这些都无关那个以查拉图斯特拉之名教我们“人是一个必须被超越的东西”的尼采。在研究伟大思想家时,常会遇到一个困境:他们的语境其实不是同时代提供的。尼采真正的对立面是基督,而不是瓦格纳,甚至不是康德,因为义务论的道德哲学不过是宗教的意识形态外壳。沃森为了将尼采“历史化”,将其放置在19世纪末的语境下,不惜隐没他超越时代的成就,将他矮化到同时代小册子作家的水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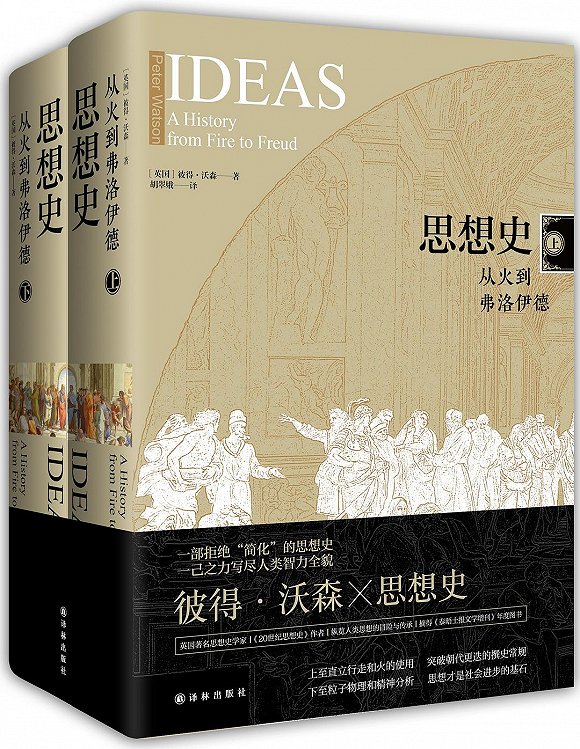
《思想史》
(英)彼得·沃森 著 胡翠娥 译
译林出版社2018年1月
以上批评绝非吹毛求疵。或许有人认为,尼采与海德格尔不过是众多哲学家中的两位而已。然而若要深入20世纪初欧洲精神中那惊心动魄的虚无,只有这两位思想家才能将其暴露,因为他们是“用锤子从事哲学”的人。这是一千个斯宾格勒、荣格或萨特都达不到的事情。思想史作者若仅将尼采和海德格尔视作两位哲学家,就错过了两扇窥视欧洲心灵的窗口。
类似的问题还出现在他对维特根斯坦的解读中。沃森很重视他,但他重视的更多是维氏与同时代人的关联,例如他对弗洛伊德的语言批判。然而维氏关于语言游戏是什么、遵守规则意味着什么的问题,例如《哲学研究》的开头对奥古斯丁的语言观的反驳,却被忽视了。这些部分,恰恰是他独一无二的成就。对精神分析学的隐喻的批判不一定要由维氏来完成,波普尔其实也能做到,但语言游戏及其规则的讨论却非他不可。
本书对于思想家的挑选相当现代派,这暴露于作者对新康德、新黑格尔等二十世纪初的运动只字不提。或许作者与我一样认为他们只是十九世纪的遗留。毕竟无论他们怎么谈论“认识论”或“美学”,在人文与科学割裂的现代,认识论的领域已被解释学-现象学和科学哲学瓜分,美学也被价值现象学、心理学与文化研究取代。既然此书英文书名为The Modern Mind,这种忽视就有理可循。略遗憾的是,科学与人文的割裂以及围绕它产生的众多争执本是二十世纪思想的一条明线,此书也未多涉及。如此重大的、可视作其他诸思想的总前提的问题,是不该忽视的。
本书作者大胆地将技术视作思想史的一部分,这或许不被较传统的学者认同,但我想为此辩护:技术改变着我们关于“自然”的观念,塑造着人的心理习惯,海德格尔的对技术之思的批判说明了这一点,而芒福德对印刷术和钟表的研究,更是阐明了现代世界中的语言和时间是如何被技术塑造。对于原子能、计算机等关乎世界观的技术,作者更不吝惜笔墨。然而遗憾的是,作者详细描写了核武器的发明过程,却没有说明核威慑平衡对国际关系学的改变,以及它如何改变了人们对“战争是什么”的想象。19世纪军事思想对强力且短促的战争的追求,是如何在世界大战的现实和核武恐怖面前破产的。技术、军事、伦理,三者的历史本可以联动起来,作者却没有做到这一点。
在处理史学史的问题时,沃森开宗明义指出,20世纪史学的趋势是从专注于精英的个人行为,转为关注更大范围的诸多结构性力量。这完全正确。他对年鉴学派、英国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人物和著作的概括也兼顾了扼要与准确。然而同样由于对解释学的忽视,他未能意识到历史学家们的兴趣从“个人”转向“结构”的哲学原因,未能抓住20世纪上半叶的传记学与史学之争,也未能由此引入历史学何以横跨“人文”与“社科”的讨论。
沃森明显意识到:撰写二十世纪的思想史无法绕开复杂精微的哲学理论。因为现代哲学不是彼岸的,用彼得·斯特劳森的话说,是“描述性”地关涉我们的存在的,是对日常生活中一些最基本的范畴的分析。例如心灵哲学中关于人工智能的讨论,其实就是围绕现代世界观中几种直觉之间的冲突。本书38、39两章集中讨论了美国新实用主义与心灵哲学。然而在当代分析哲学界,论文已经取代了大部头著述,实难概括出谁的“毕生观点”或“体系”。尤其是当介绍托马斯·内格尔这样在很多领域都有重要论文的哲学家时更是如此。所以这两章哪怕仅从篇幅上说已几乎注定要失败。但即便如此,沃森也未能将有限的篇幅作高效利用:在简介心灵哲学时,他未能澄清其中几种主流观点之间相互辩驳的思路、各自的长与短、对立学派之间的哪些观点不矛盾,哪些分歧是根本的、无法弥合的。整个一章甚至未出现过困难问题、泛心论、副现象论、随附性等术语。
或者说,这本书其实是以书写艺术史的方式写哲学史的。艺术史界有一句名言:“从来没有艺术这回事,有的只是艺术家们”,但类似命题不适用于哲学。沃森展示了二十世纪各个艺术流派的兴衰交替,描绘了众多艺术家生涯群像,提供了很多信息,例如波洛克曾经一度非常重视荣格的思想——这是我在看波洛克作品时完全不知道的,读到此处,立刻改变了我对波洛克的理解。艺术史就是艺术家、艺术圈的故事,但哲学史不是。当一个哲学概念第一次被提出时,它的命运与界限就已经注定,尽管它或许需要通过数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的辩论来澄清,概念的可能性和界限被澄清之前的争论构成了哲学史。生命之树长青,但理论是灰色的;情绪是柔软的和可塑的,概念却比钻石更坚硬。不是我说语言,而是语言说我;我不过是一个形式上的、偶然的器皿罢了。
然而在二十世纪艺术史的方面,沃森有另一个无法克服的难题:艺术史不能以西方中心的方式来写。西方中心的写法适用于哲学史、科学史甚至国际关系史,却不适用于艺术史。我可以承认中国的科学和哲学都不如西方,却不会认为齐白石不如毕加索。
沃森在艺术行业经验丰富,此书却对上世纪新生的艺术史学科只字不提,只略提了阿比·瓦尔堡。贡布里希的视觉心理学、沃尔夫林的风格要素、潘诺夫斯基的图像学均未涉及。也就是说他不打算阐述二十世纪艺术理论的发展如何改变了人们的艺术观念,或反映了这一改变。然而二十世纪的艺术是高度哲学化的,即便对此颇反感的人也承认这一点:亚瑟·丹托说,“艺术受到了哲学的压迫”,或者说正是在智性活动将感性活动塑造成今天的模样。所以本书既然有大量篇幅讨论这百年艺术圈,对同时代艺术史与艺术理论的忽视就是不明智的。沃森重视艺术与历史其他方面的联系,这无疑是正确的。例如他引用保罗·克利的话:“世界越可怕,艺术越抽象”,并提到了核弹的可怖,这确是奇妙的关联。然而他本可以借沃林格《抽象与移情》解释克利的这句话,或加入海德格尔对“比一千个太阳还亮”的核弹与现代技术是如何毁灭了世间“阴翳”的讨论。
沃森按照编年史的整体顺序,尽可能展示“共时”的诸领域的思想的某些隐约相通。然而,思想史的写法却既不该以年代顺序,也不该以思想家为中心,而应当循着概念的逻辑层次,以思想本身的发展为线索。道德哲学、科学哲学、语言哲学等哲学分支不应当被思想史家视作某些人的“观点”,而应当被用作揭示诸学科、诸领域的思想各自的前设,借以讨论、揭示其间的根本关联,甚至专门学科的研究者自身都未能察觉的前见。这要求思想史的写作者具备不亚于他笔下的对象的才智。这并非强人所难,而是后人既然占了旁观者的便利,就应当做得到。沃森还对思想的“起源”感兴趣,但这又是一个绝望的、不可能的任务。我们无法通过描绘时代环境来解释某个思想,甚至某个念头,是如何“砸中”某个人的。我们能做的仅是清晰地描述学术共同体内的相关讨论。而对时代的政治经济背景的描绘,则只能服务于解释某种思想为何在某个时代流行,不能用来说明思想的“起源”。
这虽然是一篇批判为主的书评,但我必须承认,这样一本书反而较适合我这样的读者:我对历史的认识止于一战,对哲学的研究却始于现代,这两部分知识是脱节的。这本书恰恰提供了大量我所不知道的细节,填补了我的知识空缺。然而考虑到这本书是面向普通读者的通识读物,不能仅以我一人之利弊度量,本文中的批评也就在所难免了。
 简体中文
简体中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