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完结的剧集《德雷尔一家》改编自英国自然作家杰拉尔德·德雷尔的《希腊三部曲》,讲的是丧偶的母亲带着四个孩子离开阴冷的英国伯恩茅斯,来到希腊小岛科孚居住的经历,这里“每天都有那种安详静谧、光阴止步的感觉”。今年开播的英剧《万物既伟大又渺小》则改编自同名小说,讲述了年轻兽医吉米·哈利在乡间行医生活的经历,观众在其中得见北英格兰约克郡乡间人与动物百态。
这两部作品有一些共通之处,比如都根据真人真事改编,故事都发生在一战结束后、二战开始前的欧洲,并且主人公都在战争阴影之下和现实生活的痛苦之外,营造了一片世外桃源。在今天,观众即便没有注意这些故事的时间和背景设定,也一样能够在当中得到治愈。
这种治愈来自于赏心悦目的自然环境——德雷尔一家俯瞰大海,周围是树林与果园,吉米·哈利目之所及都是无尽的碧绿草地。在这里,人与动物相处就像亲人朋友,人对所处的自然保持尊重和克制,人与人之间则相互依存、彼此关照。这些要素让现代都市的人们对某些缺失之物心生渴望,滋长出了某种浓烈的怀旧与思乡之情。
人与动物
在《德雷尔一家》当中,一家人对待动物的方式是和它们生活在一起,人们给予动物食物和照顾,并允许它们在家里走来走去、飞来飞去,没有过多收养,也没有让它们挤在笼子里。在真实生活当中,杰拉尔德一生与动物为伍,花了大半辈子时间经营动物园,不过他真正希望看到的是地球不再有濒临绝种的动物,也不再有动物园存在的必要。杰拉尔德到20世纪50年代已经收养了相当数量的小动物,他并没有赚取“展览费”而捕获表演物种。在当时的人们眼中,放弃这笔可观的收入是愚蠢的,不过,他即使陷于穷困也未曾动摇。

《德雷尔一家》第四季 剧照 图片来源:豆瓣
在《万物既伟大又渺小》里,从事兽医工作的吉米·哈利主要与乡村里的猪牛马羊打交道,也会关照村民养的宠物猫狗。在第一集里,他被马踢倒,弄得一身脏泥;被体形庞大的公牛吓得站到了墙上;他给难产的母牛接生,把手伸进产道,费尽全身力气把小牛拉出来……这些工作固然辛苦,但他所面对的乡间动物是真正悠然生活在田野的。很多时候,动物们有自己的名字,比如大公牛“克莱夫”和母牛“冰糖”,它们需要劳作却并非苦力,而更像农民的朋友、亲人或儿女。
兽医西格弗里德·法农和哈利在乡间有过这样的对话。法农给哈利介绍短角牛,他说,这种牛如今都要灭绝了,因为荷兰牛的产奶量要大得多。哈利回答说:“如果一个农民花同样的时间能够得到更多的奶,那我觉得是好事。”法农反问道:“但代价是什么呢?这个地方有自己独特的气息,短角牛就是其中的一部分。它们一旦消失,这个山谷就会又失去一点独特性。”
如今还有多少山谷拥有自己的独特性,乡间的动物又有多少仍自在生活?有多少人会像杰拉尔德一样,哪怕在巨大的利益驱动下,也不让动物处在拥挤的环境中,不让它们去展览、表演赚钱呢?现实生活中,很多动物已经不复自在自为,动物成为人牟利的工具,动物和人的关系变成了奴役和虐待的关系。

《万物既伟大又渺小》剧照 图片来源:豆瓣
人和动物的关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传统饲养动物在户外放养,吃的是蔬菜和种子,活蹦乱跳,如今工业化养殖之下,动物被集约化监禁饲养,饲养空间十分狭窄。伦理学家、《动物解放》一书作者彼得·辛格看到,动物的五项基本自由(转身、梳毛、站立、卧倒、伸腿)在这种情况下难以得到保障。鸡吃的是高能量食物,在笼子里几乎动弹不得;奶牛生活在不长草的牧场里;牛犊短暂的一生都在吃液体饲料,在75厘米宽的格栏里难以伸展四肢……这些动物不再拥有自己的名字,变成了养殖场的一个个数字。
人与自然
与《德雷尔一家》《万物既伟大又渺小》所展示的田园牧歌不同,现实中的人们一直心存把动物、土地转化为金钱的渴望。就在吉米·哈利开始在英格兰乡村当兽医的30年代,也正是德雷尔一家在希腊科孚的30年代,在大洋彼岸的美国,狂飙突进的美国西部大开发中,在利润的刺激之下,人们不计后果地翻耕大平原,剥光了那里千百年来固定土壤、抵御风蚀的植被。《肮脏的三十年代:沙尘暴中的美国人》讲述了大规模的土壤侵蚀和尘暴的到来,让人们生活的世界如同漫漫长夜,人们因为尘肺疾病而死去。那是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环境危机之一。
上个世纪60年代,人们开始反思征服自然的意识形态。美国历史学家、环境史学的创始人之一唐纳德·沃斯特在《尘暴:20世纪30年代美国南部大平原》里看到,问题的根源而在于一种文化——这些环境问题是由资本主义的精神引发的,拜金主义取代了人与土地的依存关系,对无限财富的追求取代了自给自足的乡村经济。农业生态失败和人们持有的价值观、对成功的看法和获得成功的方式密切相关。在广告宣传和物欲刺激之下,人的欲望被放大到远远超过自己的需求,乡村的人们紧盯城市社会的生活标准,“人们没有按照社区自身的节奏来生活,而是盯着远方的陀螺,这样的生活态度也成为了他们采取的高度商业化农业的重要部分。”

《尘暴:20世纪30年代美国南部大平原(25周年纪念版)》 [美]唐纳德·沃斯特 著侯文蕙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2020-7-1
在城市里,欲望的放大让人们变得越来越忙碌。波士顿学院社会学教授朱丽叶·斯格尔在《过度劳累的美国人》一书中提出了“工作-消费循环”,日本经济学家森冈孝二在《过劳时代》里也有过类似的论述。人们用物质消费的刺激取代空闲时间来消解自己的欲望,这样无异于饮鸩止渴,不仅不能持久,还会推动欲望不断升级,人们为此再增加劳动时间,进一步削减空闲。而没有进入工作-消费陷阱的人,不是不会落入,而是无力落入。如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指出的,被排除在消费之外的“新穷人”由于没有购买力,在物质与精神上都被抛弃。
在大城市,以消费为实现自我目的的浪费型生活方式成为大众化现象,攀比消费成为了过度劳动的重要诱因,人们为了永不餍足的消费欲望拼命加班、超负荷兼职、频繁跳槽……在农村,唯一的办法就是向自然索取,利用土地既不取决于土地本身的要求,也不取决于当地人自身产生的需求,而取决于来自于商人的无情的压力。沃斯特看到,一种对消费至上的无个性的认同树立起来——“钱,更多的钱,是参与那个世界所必须的。”
为什么《德雷尔一家》《万物既伟大又渺小》提供了治愈的效果?他们和我们所追求的“进步”、追求的拜金文化格格不入——德雷尔一家因为濒临破产才搬到了希腊科孚,住在破破烂烂的房子里,空无一物,油漆剥落,天花板随时可能掉下来。与碧海蓝天相对应的,是原始闭塞和物质匮乏。而《万物既伟大又渺小》里,兽医哈利早在上学的时候就被老教授警告过职业问题:如果决定将来做兽医,生活中会有无穷的趣味和丰富的经验,可是永远不会成为大富翁。这里绝对没有香奈儿不如爱马仕的太太圈竞赛,人们上街只是买点苹果洋葱,多煎一根香肠都算得上是美味餐点。
与现实中人们沉溺丰裕无法自拔的生活方式相比,剧集中的人物生活在上个世纪30年代,还没有体会到人与物关系的彻底转变,没有极大的丰盛,也没有戏剧性的浪费,普通的食品和物件都能够成为维系人与人感情的牵绊。他们的生活也符合今天经历过环境破坏之后人们的反思——那就是,不能漠视自然极限,保持尊重与克制。
人际关系
沃斯特指出,在种种抵抗消费文化的力量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个体对地方群体的认同。家庭也是一种对抗力量。德雷尔一家人密切关联,相互关照,不仅以此应对恶劣的环境和贫困,也消除了彼此的孤独感、不安全感和失落感。除了家庭,地方教会和一些团体也拥有这样的力量,德雷尔一家努力参与地方教会、理解科孚岛的风俗文化;对于兽医哈利来说,赛马场、舞会、酒吧也都是当地生活重要的组成部分。沃斯特说,这种地方感,也可以让人们在周围的经济文化转向工厂、城市和过度消费时,思考当地社区的需要和生态和谐,从而“在随风飘摇的文化里稳如泰山”。

《德雷尔一家》第一季 剧照 图片来源:豆瓣
今天,个体已经被释放到了都市的马路和人行道上,人人都成为了自己命运的主人。这些个体将如何共同生活?《后现代性下的生命与多重时间》作者、社会学家基思·特斯特看到,怀旧/恋乡提供了解决之道。社会学家斐迪南·滕尼斯认为,共同体是一种生命有机体,在规模较小、基本静态的乡村情境里,共同体是显著的。因此,当我们为德雷尔一家的生活所着迷时,我们想念的不是田园牧歌时代受到界线限制的家园,而是其中所蕴含的确定性。在怀旧/恋乡当中找到的解决之道,就是把个体维系在某些限定的特性、身份、认同之上,现代性经过怀旧/恋乡而变得可以居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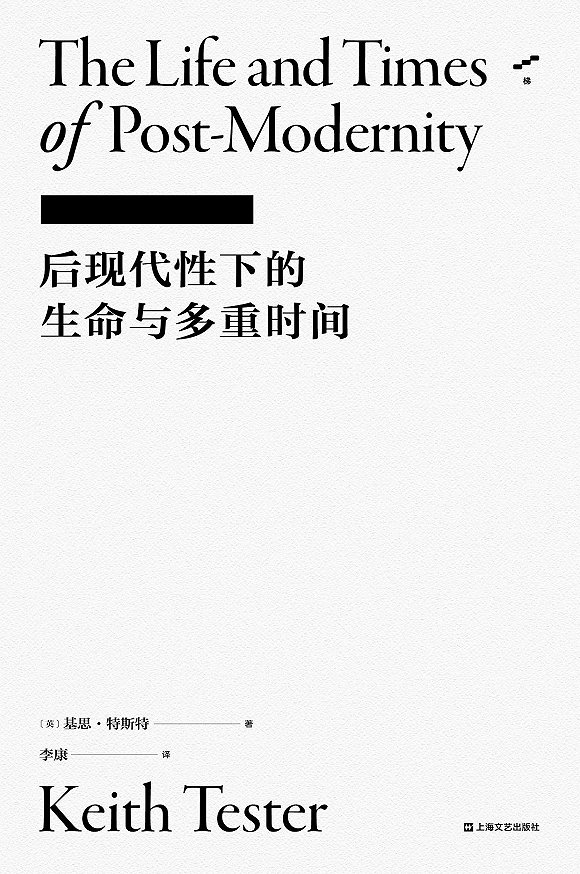
《后现代性下的生命与多重时间》 [英]基思·特斯特著 李康译 梯·上海文艺出版社 2020-5
我们对田园生活的欣赏中蕴含着对现代性的批判。《森林纪》作者胡平看到,虽说英国作为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代名词,但是英国人心里一直保持对乡村的热爱——哪怕他们一直居于城市,内心也始终向往着返归乡村。作者请求中国读者自问:“如果说英国人的灵魂在乡村,那么,我们的灵魂去哪里寻找呢?”
乡村不是绝对的世外桃源之地,不然“打土豪,分田地”的阶级斗争从哪里来?文化批评家雷蒙·威廉斯也在《乡村与城市》一书中谈到,对乡村的田园牧歌般的想象遮蔽了问题,简·奥斯汀笔下的村庄固然可爱,但主人公的邻居们并不是住得最近的人,而只是社会地位上可以交往的人,在她的故事中,大量的农民是隐形的。旧日农村的“自然经济”是一种剥削制度,人和土地一样都是财产,多数人沦为劳作动物,虽然农民也受到“保护”,但那只是为了让他们能够付出更多劳动。即使是在“自然经济”时期,乡村也孕育着后来的资本主义经济,地主阶级逐渐演变为资本家地主。随后的圈地运动和农业资本主义使得乡村和城市在本质上并没有什么不同。
即便如此,人们也对乡村依然怀抱一种美好的想象,正如在村居者的眼里城市充满了诱惑。我们也必须生活在城市,才能够想象乡村的快乐。德雷尔一家、兽医哈利给我们营造的治愈系的过去既不复存在,也无法再现,这其中的慰藉和失落却让人不由得意识到——我们正在对某些缺失的东西产生渴望。基思·特斯特说,或许,这种情结并不一定是拒斥当下,也可以是对于我们现在所处位置的一种积极的应对,让我们针对物化的斗争变得更加坚定,重新获得继续生活下去的信心和确定性。
(来源:界面新闻)
 简体中文
简体中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