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籍智利作家伊莎贝尔·阿连德(Isabel Allende)早在知道女权一词的含义之前,就已经是一名女权主义者了。三岁时,她见证了母亲潘奇塔被父亲抛弃,独自抚养三个小孩。潘奇塔搬回了父母在圣地亚哥的房子,她的父亲立即控制了她的财务。离婚后,她被逐出教会。年幼的伊莎贝尔观察到母亲的无能为力,并对男性权威进行了抨击。在她的新书《一个女人的灵魂》( The Soul of a Woman )中,她回忆起她的怨恨来源于“我家庭中的出现的问题,而这个家庭却自认为是知识分子和现代人,但按照今天的标准,坦率地说,它相当于是旧石器时代”。这样的愤怒让她的母亲不得不带她去看医生,怀疑是由肠绞痛或者绦虫引起的。
现年78岁的阿连德说,她为潘奇塔感到沮丧,也为她拒绝为自己站出来而感到沮丧。阿连德回忆说,“她认为自己无法改变上帝创造出来的东西,当她看到我愿意站出来抗争时,她很害怕,认为我会被排挤。她还担心我永远找不到丈夫。在智利,我们这一代人如果在23岁之前没有正式订婚,就是个老处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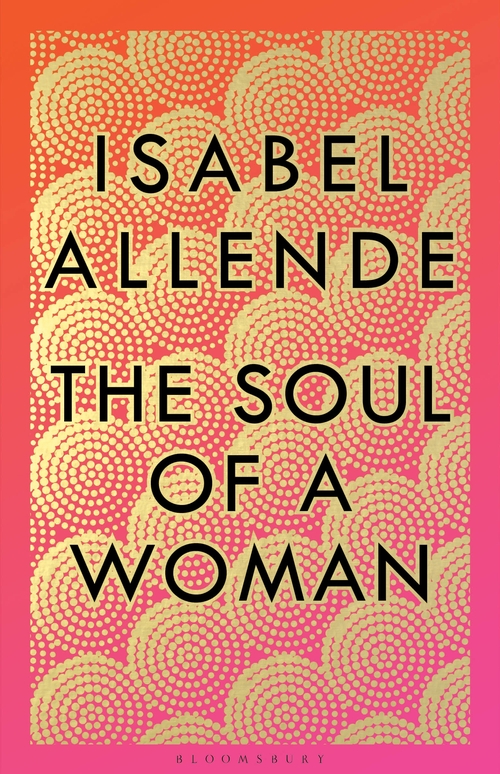
《一个女人的灵魂》
阿连德最终结了三次婚,也从未放弃过争取平等的斗争。1967年,她与别人一起创办了女权主义杂志《宝拉》(Paula),意识到自己“可以将愤怒转化为行动”,并撰写了一系列讽刺父权制的专栏文章,专栏名为“类人猿文明”。后来她转向小说创作,审视家庭、历史、流离失所和女性的生活。1982年,她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书——畅销著作《幽灵之家》,被誉为在男性主导的文学环境中发出了新的女性主义声音。随后她出版了《幸运之女》( Daughter of Fortune )、《我的灵魂伊奈斯》( Inés of My Soul )、《怪兽之城》(City of the Beasts)等几十本书,被翻译成40多种语言。2014年,奥巴马授予她美国最高平民荣誉——总统自由勋章。迄今她已经卖出了7500万本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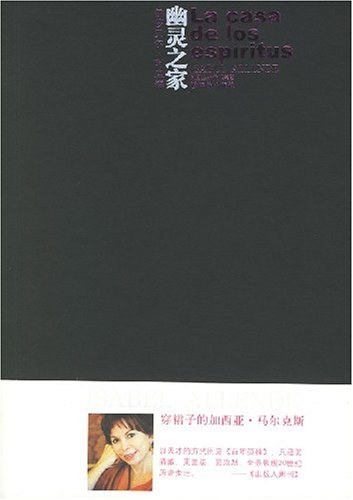
《幽灵之家》
[智利]伊莎贝尔·阿连德 著 刘习良 笋季英 译
译林出版社 2007-04
阿连德在她位于加州的家中接受了采访,她自1988年起就居住在那里(她于1993年成为美国公民),现在她和第三任丈夫罗杰·库克拉斯住在一起。在她身后可以看到一扇纯白色的百叶窗,阳光透过窗页照进来。她说,隔离并没有让她变得懒散——“我每天早上六点左右起床。先是喝杯咖啡,然后洗个澡,接着我会完整地化好妆,就像要出去看歌剧一样。我换好衣服,穿上高跟鞋,然后上楼到我工作的阁楼。我不会见任何人,甚至连快递员也不会见,我为自己打扮。”
阿连德两年前与库克拉斯结婚,自己甚至依然为这一事实感到甜蜜的惊讶。“简直是在开玩笑!我根本没想到我还会有性生活,更不用说结婚了! 我72岁的时候就和我的(上一任)丈夫分居了,大家都说‘你疯了吗? 你为什么70多岁还要离婚?’。我从来没有害怕过孤独,因为我自给自足。但后来罗杰出现在我的生活中,他是一个非常正派而善良的人,这样的人可不是在哪儿都能遇到的。”

写得非常纯真……改编自伊莎贝尔·阿连德的《幽灵之屋》电影,由梅丽尔·斯特里普和杰瑞米·艾恩斯出演。图片来源:TCD/Alamy TCD/Alamy
当她在墨西哥城的一次女性会议上发表演讲时,就埋下了《一个女人的灵魂》的种子。这是一部女性的反思,它既是回忆录,也是辩论。“我开始思考我作为一个女人和一个女权主义者的人生轨迹,”她说。除了记录她早年的家庭生活,书中还包含了对青春、衰老和物化(“女权主义并没有把我们从这种奴役中拯救出来”)的优雅而富有启发性的思考。她也审视了生殖权和性暴力,并阐述了她对女权主义的定义:“不是我们两腿之间的东西,而是我们双耳之间的东西。这是一种哲学姿态,也是对男性权威的起义。”
特别感人的是她对自己与孙辈关系的反思,她孙辈的身份认同是非二元性别。“当他们(they,非二元性别者常用的人称代词)把我介绍给朋友时,我会问每个人他们喜欢被称呼的人称代词。”我告诉她,这对她这一代人来说是罕见的。“确实如此,”她同意,“但你知道,事情会变,变化是有原因的,你必须适应。当年轻人质疑的时候,总是显得太过火,显得很极端。但在这种斗争中,总会发生美好的事情,新的想法,新的艺术,新的创造力。我们正在推动历史。”
回顾她在智利的童年,阿连德回忆其当时的父权社会“非常成功地将女权主义者描绘成不刮腋毛的愤怒婊子”。“很多年轻女性都吸收了这种想法。虽然她们不会放弃她们的母亲和祖母经过一番奋斗所获得的权利,但她们却不想被称为女权主义者。我当时常说现在仍然在说的是:‘你不喜欢这个词,就不要用它。改变它。都无所谓。只要为此斗争就好。’”
对她而言,这种斗争包括帮助他人,承认自己在教育、技术和医疗方面的特权,并了解这些东西是多么容易消失。阿连德说,“在疫情中,首先失去工作的人是女性,“她们被困在家里养育孩子,因为学校没有开放。有时,家庭里的施虐者就和她们住在一起,她们没有任何资源,因为一切都处在隔离中,她们将是最后恢复的人。女性必须非常警惕,提高警惕,因为我们可能会失去一切。”

1985年,阿连德在加拉加斯的家中。图片来源:Felipe Amilibia/AFP/Getty Images
毫无疑问,阿连德了解失去的滋味。1973年,她的表兄、社会主义总统萨尔瓦多·阿连德在一次暴力政变中被皮诺切特推翻并杀害。她被政府列入黑名单,与丈夫和两个孩子一起逃往委内瑞拉,他们在那里生活了13年。1991年,她的女儿宝拉·弗里亚斯因卟啉症陷入昏迷,一年后去世,享年29岁。她经受了更深的创伤。阿连德之后写了一本回忆录《宝拉》( Paula ),在出版后,她说自己“陷入了瓶颈——我无法写作,我什么也做不了,我感到内心空虚”。
为了分散她的悲伤,她的丈夫和一个朋友决定带她去印度。当他们开车经过拉贾斯坦时,车出了问题。等待修车的阿连德和一群当地女性聊了起来。虽然她们语言不通,但却能交流。离开之前,一个年轻女子递给她一个破布小包裹。“她坚持要我打开包裹,我看到里面是一个刚出生的婴儿,”她回忆说,“她一定只有一天大,脐带还是新鲜的。”司机出面干预,把婴儿交还给女人,并把阿连德赶进车里。“当时我问那女人为什么要把婴儿送人,她告诉我:‘那是个女孩。谁会想要一个女孩呢?’这让我心里有了些许触动。”
回家后,她成立了伊莎贝尔·阿连德基金会。“使命是帮助像她们这样的女孩,那个我无法伸出援手的小婴儿,还有像那位母亲一样的女性,她觉得自己的孩子活下去的唯一机会就是送给别人。”基金会专注于女性健康、教育、经济独立和免受暴力侵害。自2016年以来,它已经扩大到援助难民,特别是美国南部边境的难民。她把回忆录《宝拉》的所有利润都捐给了基金会,此后,她依然将图书收入的一部分注入基金会。
阿连德说,多年来她一直想写一部爱情小说,但每次都失败了,因为她不相信她所写的男性角色。“我开始写,没一会就会放声大笑,我不能用那种轻浮的风格写作。我必须得先相信,有着绿眼睛和大胸的处女会吸引来一个对爱情失望的富豪CEO。我一生中从未遇见过这种情况,所以我没法相信。”当她确实在书中引入一个带有浪漫色彩的男性角色时,她说:“我在第112页左右就把他杀了,因为我很快就发现我受不了这个家伙。如果你不希望这样的人出现在你的生活中,为什么要把他强加给你的主角呢?”
写《幽灵之家》时,她没有什么宏伟的计划。“我没有榜样,我也不知道我的书会不会有人读,更别说出版了。我是冲动之下写作的,非常纯真。”那时,她的第一段婚姻已经破裂,她在加拉加斯的一所学校里当管理员。她利用晚上、周末和假期写作。这本书一开始是写给她临终祖父的信,最后变成了关于家族的虚构故事。

2014年,美国总统奥巴马向阿连德颁发总统自由勋章。图片来源:ddp USA/REX Shutterstock
近40年来,在写了25本书后,阿连德学会了计划,但只是一点点。“我的计划是,如果1月8日我还活着,就开始写一本新书。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每年我都会开始写一本新书,因为也许我还没有写完前一本。”既然我们是在一月中旬进行的采访,这是否意味着她已经开始写新书了?“是的,”她点点头。能透露新书的内容吗?“当然不能,”她笑道。她能告诉我的是,在开始之写作前,她不一定会有一个想法。“一半的工作是坐在书桌前,”她说,“你坐在书桌前,打开你的思想和心灵,就会发生一些事情。在多年的写作中,我已经学会了必须要有耐心。除了政治和足球,我可以写任何东西,所以我知道如果给自己时间,放松下来,就能写出来点什么。如果我很紧张,拼命地呼唤缪斯,缪斯就不会来了。”
在《一个女人的灵魂》中,阿连德描绘了一幅她年过七旬的生活图景,“我正处在我命运的辉煌时刻。”她告诉我,她是一个天生的乐观主义者,在她的一生中,她看到了女性身上发生的巨大变化。她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男性和女性将拥有同等的权利。结束父权制“(需要)进化的飞跃”,她说,“那将会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文明,而我不会看到它。就像所有的革命一样,我们从巨大的愤怒和不公正感中起步,最终让事情走上正轨。我们像疯了一样地战斗,却不知道我们要去哪里。但只要继续为最后的目标而努力,它就会实现。我们会做到的,我相信。”
(翻译:李思璟)
 简体中文
简体中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