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曼塔·施维伯林(Samantha Schweblin)1978年出生于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著有三部短篇小说集,2010年被《格兰塔》杂志评选为35岁以下最佳西班牙语青年作家之一。2014年,施维伯林发表处女作《炙热梦魇》( Fever Dream ),荣获了雪莉·杰克逊奖最佳小说奖,并入围了国际布克文学奖。2020年,施维伯林发表了第二部小说《小眼睛》( Little Eyes ),再次入围了2020布克国际文学奖长名单。《小眼睛》虚构了另外一种现实——人人都佩带“kentuki”,一种动物形状的小型设备,动物的眼睛里都配有摄像头,而这些摄像头都被一个不为人知的神秘用户控制着。施维伯林目前定居在柏林。
过去这一年你过得怎么样?
莎曼塔·施维伯林: 总的来说感觉很奇怪。疫情最初爆发的那段时间,我正在阿根廷,哪儿也去不了让我很恼火。但是,那三个月其实还是挺不错的,我终于有时间可以坐下来调整自己的节奏,重新投入到我的工作当中。不过一开始真的挺难熬的,情况一天一天急转直下,全世界都受到了极大的冲击,甚至不敢相信这样极具杀伤力和传播力的疫情是真实发生的事情。我记得在第10天还是15天的时候,我还看到电视上有人相互拥抱,认为“这是不可能发生的”。或许这是我们有生以来第一次如此强烈的感受到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再也回不到原来的样子了。而在这种背景下再进行创作,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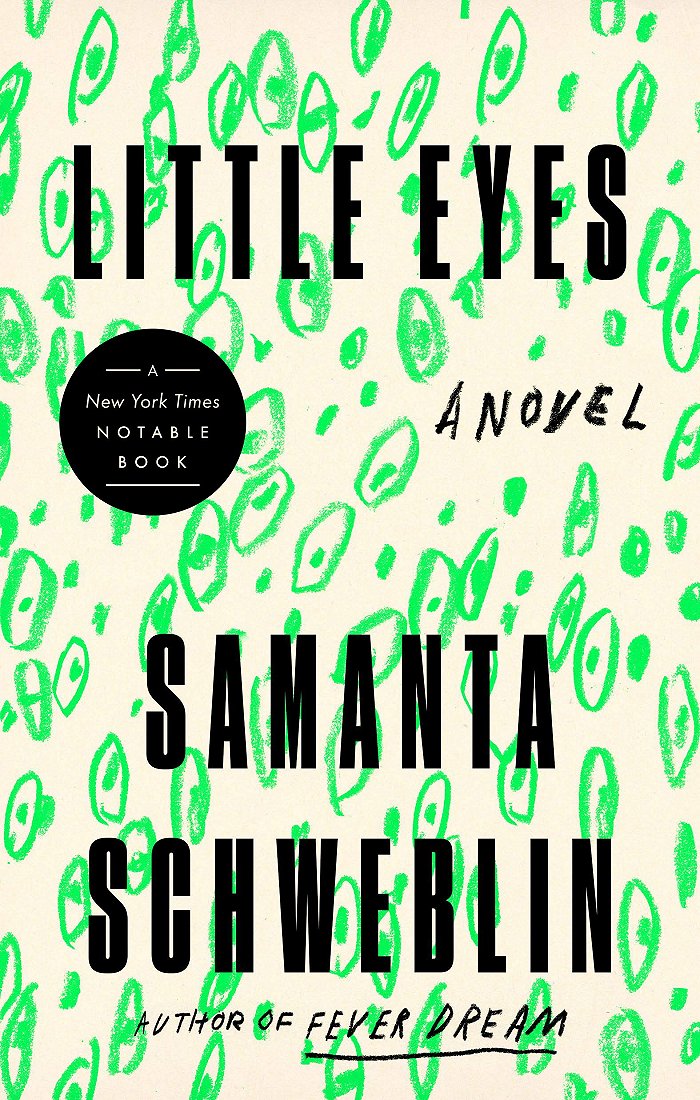
《小眼睛》
你在《小眼睛》中所构想的设备,是受到了某个特定设备的启发,还是说,只是表达了你对科学技术的担忧?
莎曼塔·施维伯林: 作为一个读者,我感觉文学和科技之间似乎存在某些问题。从我所读过的所有作品甚至是我自己的作品中,我发现,作者们都在竭尽全力避免为技术命名。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能够非常自然地接受科技的存在,但是在小说里,我们却极力避免谈论科技。而我想通过科技来谈谈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于是,关于“kentuki”的构想就出现了。“kentuki”其实是WhatsApp、Twitter、Facebook和手机的混合体,它可以代表一切,所以我也不需要命名任何东西。
为什么一定要展现科技积极和消极的两面性呢?这么做的重要性在哪里?
莎曼塔·施维伯林: 人们已经开始对科技有一种固化思维了,认为科技就是不好的东西,但是我个人认为,科技其实是中立的。科技所涵盖的范围很广,不仅仅只有电脑和WiFi,收音机、车轮、书籍等等也都是科技的产物。所有这些东西都具有两面性,至于它是好还是坏,更多其实是取决于我们自己。在某种程度上,其实“kentuki”就是这本小说中的麦高芬 (MacGuffin,电影中推动情节发展的事物、角色)。我就是想要创作一些非常人性化的角色,在同样的情况下,他们会做出和读者一模一样的反应和举动,然后再突然向他们揭示出,这些反应和举动可能是非常糟糕的。
你会不会暗地里希望某个在科技行业工作的人会真的开始创造“kentuki”?
莎曼塔·施维伯林: 这个我不能说太多,但是已经有人购买了电影版权,所以我想某一天真的会做出“kentuki”。不过我并不希望“kentuki”真的存在于现实生活中,那将会是一场灾难。我可不想成为这场可怕灾难的主谋。实际上,一开始“kentuki”的设想出现在我的脑海时,并不是小说创作的元素,我只是单纯构想了这么一个设备。如果像无人机这样复杂的东西都已经存在了,那么像“kentuki”这样的设备又有什么稀奇的呢?它肯定会是个物美价廉、标新立致的玩意儿,对市场来说肯定是双赢。我的父亲开玩笑地建议我给它申请版权,但我并不想这么做。他带着失望的语气说道:“如果你不想通过它挣钱的话,那就把它写进你的小说里吧。”
你自己平时使用科技和互联网的情况怎么样?
莎曼塔·施维伯林: 我自我感觉还比较正常。我有手机,也有Instagram账号,但是我不经常使用。 我没有Facebook,Twitter上只关注了几个优秀的记者,因为在很多拉美国家,如果一个公民相信主流媒体的报道,那真的是要了命了。当然,在疫情期间,少不了使用Zoom、Skype和WhatsApp与他人保持沟通。事实上,个人对这些技术的感受已经变得不那么重要了,更重要的是保持联系的功能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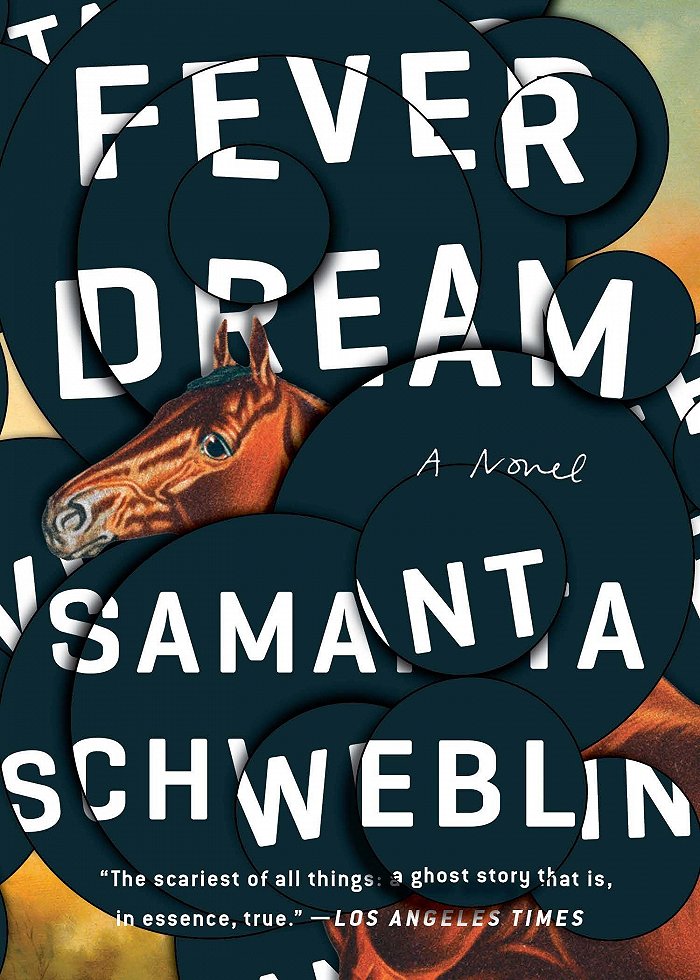
《炙热梦魇》
那你觉得,在过去的10年里,隐私的概念有什么变化吗?
莎曼塔·施维伯林: 变化是绝对有的。我们之前从未见过面,但是我已经对你了如指掌,我知道你沙发旁边放着什么书、你的书架是什么样子的、你公寓的采光等等。如果是在10年前,即便我们是朋友关系,或许也要花个好几年才能像这样了解到彼此日常生活中的点滴。现在的人们几乎无时无刻不在分享自己的空间,但要了解这种做法会对我们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还为时过早。
关于电影版《炙热梦魇》,有什么能和我们分享的吗?
莎曼塔·施维伯林: 网飞的计划是在10月份播出。在小说里,那种从始至终被叙事牵着走、被欺骗的恐惧感太过强烈了,也正是这一点让我对改编的作品感到担忧,因为把小说中非常关键的叙述转变成电影中的画外音可能就会很糟糕。观众可能会觉得画外音很无聊,有时候甚至会脱节,不知道画外音在说什么。所以写剧本真的是一个挑战。但是当我看到最终的剧本时,我非常高兴和满意。
最近你在读哪些书?
莎曼塔·施维伯林: 一般我会同时读很多书。这段时间,我正在读本杰明·拉巴图(Benjamín Labatut)的《何时停止了解世界》( When We Cease to Understand the World ),这是一部虚构小说,也是一部散文。我一直在重读唐纳德·巴塞尔姆(Donald Barthelme)的小说,还有马克西姆·毕勒 (Maxim Biller)的短篇小说集。恰克·帕拉尼克(Chuck Palahniuk)的新书《声音的发明》( The Invention of Sound )最近我也在读。
会不会有某种题材的书特别吸引你?
莎曼塔·施维伯林: 我特别喜欢短篇故事,这类故事往往非常精炼,表达准确而强烈。我觉得创作短篇小说的作者,主要就是希望读者能够全神贯注地花2、3个小时就把故事读完。
小时候你喜欢读什么书?
莎曼塔·施维伯林: 小时候我会看父母书架上的书,有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加西亚·马尔克斯和胡安·鲁尔福等。到16、17岁的时候,我偶然读到了一些英语著作,开始学着像这些作家一样写作,并开始了疯狂的创作。这些作家都非常清楚,小说一部分在于内容,还有一部分在于读者的想法,只不过读者的想法往往是经过作者精心计算诱导产生的。
莎曼塔·施维伯林: 当然有,我非常喜欢卡夫卡,经常重读他的作品。也有一些当代作家的作品读来令我着迷。我很喜欢伊丽莎白·斯特劳特(Elizabeth Strout)的作品,她可以仅用一句话就塑造出一个人物,鲜活地出现在读者面前。我也很欣赏凯利·林克(Kelly Link)、艾米·班德(Aimee Bender)、维维恩·戈尼克(Vivian Gornick)和艾米·亨普尔 (Amy Hempel),读她的书就好像我脑子里有个锤子在敲打,每个细节都要反复思考。
(翻译:刘桑)
 简体中文
简体中文






